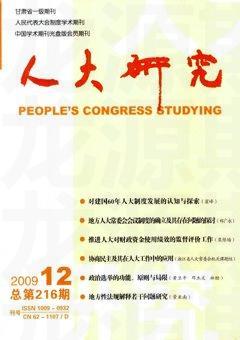地方人大常委會會議制度的確立及其存在問題的探討
鄭廣永
地方人大常委會會議是落實常委會各項權力的主要途徑,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鮮明的特點。地方人大常委會會議是常委會行使職權的主要方式。常委會會議的召開主要是行使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四項職權。立法權(縣級以上人大常委會)、監督權、人事任免權、重大事項決定權是憲法和法律賦予地方人大常委會的權力。這四項權力的行使必須通過會議。地方人大常委會會議綜合地反映了常委會的全部工作。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常委會的各項工作都是圍繞著常委會會議開展的。地方人大常委會會議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集中體現。
一、地方人大常委會會議制度的確立過程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而會議是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行使職權的基本方式,所以,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的會議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簡單地說,地方人大常委會會議制度就是指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為行使職權而依據憲法、法律和法規召開的各種會議的制度體系。
(一)地方人大常委會會議制度的探索
地方人大常委會會議制度不是伴隨著地方人大常委會的建立一蹴而就建立起來的,這個制度的完善是一個過程。地方人大常委會會議制度最初是1979年通過的地方組織法規定的。這個制度比較籠統,直到1986年修改過的地方組織法才在第二十九條中規定常務委員會會議由主任召集,每兩個月至少舉行一次。常務委員會的決議,由常務委員會以全體組成人員的過半數通過。常務委員會主任、副主任組成主任會議,處理常務委員會的重要日常工作。1987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頒布實施,各地比照這個常委會全體會議議事規則制定了本地人大常委會的議事規則后,地方人大常委會會議制度才逐步健全。當然,各地對地方人大常委會會議制度的探索從沒有停止過,這可以從各地不斷修正本地的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就能得到證明。
地方人大常委會首先比照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會議模式召開會議。比如1979年12月24日,北京市七屆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召開。據時任北京市人大常委會代表室副主任的李源富回憶說,當時,這個會到底怎么開法,主任們也不清楚。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賈庭三決定一切程序照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方式辦。李源富還專門到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秘書局要來一套會議工作程序文件[1]。黑龍江省人大常委會的同志也曾專門來到北京,向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請教。于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決定,請地方來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會議,并召開座談會。1980年4月8日,省級人大常委會負責人第一次列席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在這次座談會上,地方人大常委會如何行使職權,如何開展工作也成為議題之一。在1980年4月18日所作的《關于地方人大常委會的工作》報告中,彭真同志第一次把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的主要職權概括為四個方面:立法權、重大事項決定權、人事任免權、監督權。人們對于地方人大常委會的職權有了初步的認識。但是對于地方人大常委會如何行使這些職權,如何開展工作,許多人并不十分清楚。同時各地也開始了積極的探索。
1979年8月,我國成立了第一個地方人大常委會——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西藏自治區率先開始探索了主任會議制度。其實,就全國而言,主任會議的設置和發展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地方組織法,沒有規定地方人大常委會設立主任會議。1982年修改地方組織法時,從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出發,增設了主任會議。1986年修改地方組織法時,明確規定了主任會議的組成和職責。迄今,法律未對其性質、地位、具體職責以及行權方式作出明確規定。據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時任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第一副主任的熱地回憶說:“當時確實是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逐步探索、摸索經驗。”[2] “主任會議制度”是當時人大常委會工作的第一個規范。熱地回憶說,西藏自治區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一次主任會議是在自治區人大常委會成立10天之后召開的,會議由人大常委會主任阿沛?阿旺晉美主持。會上阿沛?阿旺晉美宣布,由于自己經常在北京,因此委托熱地全權負責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的日常工作。這次主任會議決定設立常委會辦公廳辦公室、秘書處等機構,還決定建立主任會議制度,從此每周一召開一次主任會議。
黑龍江省人大常委會探索了常委會的列席制度。1980年4月28日,黑龍江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通過《黑龍江省人大常委會同委員和人民代表的聯系制度(試行稿)》,明確規定:“省人大常委會召開的會議,按照會議內容,可邀請部分有這方面工作經驗或專門知識的代表列席。”這是地方人大關于代表列席常委會會議制度的最早規定。這一開創性做法,使常委會會議既了解實情又增加專業性。
山東省濰坊市人大常委會探索了公民旁聽人大常委會會議制度。1985年8月,山東濰坊市人大常委會邀請公民旁聽常委會會議[3]。這是最早的公民旁聽實踐。目前,全國已有20多個省級人大常委會實行了這項制度,實行公民旁聽制度的市、縣級人大常委會更加普遍。
比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會議模式,各地人大常委會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開始以召開會議的方式履行自己的職責。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從1979年12月成立至2009年5月共召開了238次會議[4]。
(二)各地通過制定本級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完善地方人大常委會會議制度
1982年通過的地方組織法對地方人大常委會如何行使職權,如何開展工作有一些籠統的規定,但是,地方組織法是一部實體法,對于地方人大如何召開會議這樣一些程序性的問題,不可能作出詳細的規定。2004年最新修訂的地方組織法也只是在第四十五條、四十六條和四十八條中規定:常務委員會會議由主任召集,每兩個月至少舉行一次;常務委員會的決議,由常務委員會以全體組成人員的過半數通過;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會議可以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屬于常務委員會職權范圍內的議案,由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可以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屬于常務委員會職權范圍內的議案,由主任會議決定提請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或者先交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提出報告,再提請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省、自治區、直轄市、自治州、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和秘書長組成主任會議;縣、自治縣、不設區的市、市轄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副主任組成主任會議。主任會議處理常務委員會的重要日常工作。也就是說,地方組織法對地方人大常委會的會期、發言、表決、列席、旁聽等內容均未作出明確的規定。
這就需要一部程序性的法規。于是,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就應運而生。1987年11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議事規則》由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的頒布和實施,不僅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制度完善的一個根本性標志,它還對地方人大常委會會議制度的完善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因為在這之前,地方人大常委會的會議制度基本上是復制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會議模式。無論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會議程序模式,還是地方人大常委會的會議程序模式,都不是在法律和法規層次上,基本上是一個時期以來的慣例。正是因為有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議事規則,各地紛紛結合本地實際制定了本地人大常委會的議事規則,從而使地方人大常委會的會議制度開始逐步完善起來。
各地在實踐中都對地方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進行了多次修訂和完善,就會議的召集和主持、聽取和審議工作報告、列席、質詢、發言、表決和旁聽等程序問題作出了比較詳細的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轄區的市、縣(縣級市)制定的議事規則雖各有特色,但規定的基本內容大體是一致的。與會議有關的內容具體是:常委會會議每兩個月至少舉行一次,會議由主任召集并主持;舉行會議時,常委會組成人員除請假外,必須出席,并建立簽到制度;必須有全體成員過半數以上出席,會議才能舉行;會議舉行15日前由主任會議決定將開會日期、建議會議審議的議程通知常委會組成人員及列席人員;政府、法院、檢察院的負責人,常委會副秘書長,各工作委員會的負責人、有關委員,設區的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或副主任1人列席會議,邀請有關的人大代表列席會議;常委會小組或聯組審議議案和工作報告時,應通知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到會,聽取意見,回答詢問;政府及5名以上的常委會組成人員均有權提出議案,是否提交會議審議由主任會議做出決定;常委會委員5人以上可聯名以書面形式向常委會提出對政府、法院、檢察院的質詢案,對答復不滿意的,可繼續質詢并要求再作答復;常委會全體組成人員過半數贊成方能通過;等等。可以講,以議事規則為主要標志,地方人大常委會會議的制度建設有了明顯的進步,法制化、規范化、程序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發揚民主、科學決策、提高效率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
許多地方的人大常委會還制定了主任會議議事規則。比如江西省新余市人大常委會制定的主任會議議事規則就與會議有關的內容作了如下規定: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副主任、秘書長組成主任會議;主任會議由常務委員會主任召集并主持。常務委員會主任可以委托1位副主任召集并主持主任會議;主任會議每月至少舉行1次;主任會議必須有全體組成人員的過半數出席始得舉行;主任會議討論決定問題,實行民主集中制。主任會議的決定,必須由全體組成人員的過半數同意;主任會議決定常務委員會會議舉行的日期,擬定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草案和日程草案,決定常務委員會會議列席人員;主任會議的議題,由秘書長征求常務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和市人民代表大會專門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的意見后提出,常務委員會主任或者受其委托的副主任確定;在主任會議舉行之前,常務委員會辦公室應將會議議題、開會日期和地點通知主任會議組成人員。
現在,人們對地方人大常委會會議制度重要性的認識越來越深刻了。經過30年的努力,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的會議制度已經基本形成,會議的程序已經法定化了。需要指出的是,人們除了自覺遵守常委會會議程序外,對于圍繞常委會會議進行的會前調研和會后監督反饋也都認真展開。會前充分而認真的調研是正確確定常委會會議議題的保證。在地方人大常委會成立之初,常委會會議議題的確定往往是根據黨委和政府的工作隨機確定的。關于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問題,彭真同志根據人大工作的特點,十分強調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會、人大專門委員會組成人員做好調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彭真同志認為,人大代表、常委會委員還要加強同選舉單位、與群眾的聯系。與群眾的聯系緊密了,了解的情況就會比較客觀、全面,決定問題就會比較正確。對于常委會會議決定的執行情況進行反饋和監督也是非常重要的。監督權本來就是地方人大常委會的一項重要職權。如果常委會只作決定,而不管決定的執行情況,那就是失職。毋庸諱言,不僅是地方人大常委會成立之初,就是時至今日,地方人大常委會的監督權行使也是不夠充分和有效的。好在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地方人大常委會日益重視常委會的監督權,并努力實施,監督不再是走過場。
總之,縣級以上地方人大常委會自1979年設立以來,常委會會議制度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逐步完善的過程。這個過程始終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因此,黨關于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工作的方針政策就是我國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工作的最高政治準則。具體說來,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會議制度的政治原則就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盡管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的論述不是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來的,而是江澤民在十六大的政治報告中首先提出的,但是,這個思想在鄧小平、彭真等老同志那里已經有了,并且貫穿了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建設的整個過程。
二、地方人大常委會會議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建議
目前,地方人大常委會會議制度雖然基本成型,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將會影響常委會功能的發揮,從而影響人民群眾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力。
(一)地方人大常委會需要進一步提高會議質量。目前,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影響了地方人大常委會的會議質量。第一,地方人大常委會會議次數少、會期短、議題多,對議題的審議不充分,從而影響會議效果。很顯然,在很短的會期里,要審議眾多的議題,審議的效果肯定不會太好。第二,會前準備不足和會后對決定、決議落實不夠也影響了會議效果。一般來說,在確定了會議議題后應該針對議題進行充分調研,但是,目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很難做到對議題的充分調研。許多地方對常委會會議的決定和決議落實得不夠有力,缺乏必要的反饋和監督,從而使得一些人對常委會會議的審議質量并不重視。經過充分審議后形成的決定和決議同未經充分審議后形成的決定和決議,其落實情況是一樣的。因此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的會期制度,以及與其相關的問題絕不是無關緊要的,而是關乎人大常委會能否依法履行職權的大問題。
全國人大組織法、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規定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每年開會的次數相對嚴格一點,每兩個月召開一次。而地方組織法規定的地方人大常委會開會的次數相對靈活一點。所謂每兩個月至少召開一次,就是可以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和工作需要,多召開會議。一律每兩個月召開一次會議,缺乏靈活性,并不完全符合地方組織法的立法原意。
另外,除召開人代會前后的個別常委會開會的時間較短,只開一天外,有些市州、縣(市、區)人大常委會正常例會的會期也太短,僅開一天,甚至僅開半天。在短暫的時間內,要審議許多議題,結果只能是走過場。這使組成人員很難充分發表意見,人大常委會也很難真正發揮作用。
地方組織法的出發點是:我國幅員過于遼闊,各地的實際情況差別很大,因此,法律給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實事求是地安排會議次數和會期留下了空間。所以,需要根據地方組織法的立法原意,提倡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從當地的實際情況和充分發揮人大常委會的作用出發,安排會議的次數、議題、會期和議程。
(二)地方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的權力要規范化。目前,一些地方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的權力有實體化的傾向,主任的權力有行政化的傾向。從主任會議、主任的職權可以看出,主任會議、主任只有程序權力,沒有實體權力;它們最大的權力就是召集和主持會議,在會議期間處理與會議程序有關的一些問題,并沒有決定立法、監督、任免和其他與人代會、人大常委會職權有關的重大事項的權力。這同人大及其常委會集體行使職權、集體討論和決定問題的根本特點是一致的。但是,我們也看到個別規定有使主任會議的權力實體化的傾向。這牽涉國家機構之間的關系,已經不是程序權力,而是實體權力了,是應該由地方人大常委會行使的權力。當然,地方人大常委會授權主任會議行使某項職權,不是不可以,但是,應該注意符合人大及其常委會集體行使職權、集體討論和決定問題的根本特點,符合法理。
目前,有些地方性法規,還授權給地方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一些實體權力。例如,主任會議可以就人民群眾對“一府兩院”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重要申訴和意見,聽取“一府兩院”的專題工作匯報,提出處理意見;可以聽取人民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專題工作匯報,提出處理意見。立法法規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產生、組織和職權,只能由法律規定。這種授權,一不符合人大及其常委會集體行使職權、集體討論和決定問題的根本特點,二不符合立法法確定的立法原則。
現在,有些地方的人大常委會主任甚至工作人員的工作出現行政化傾向。例如,按法律規定,召集會議是人大常委會主任的權力,處理人大常委會的日常工作則是主任會議的權力,有些地方是人大常委會主任說了算;有些地方的人大常委會主任,自己就面對“一府兩院”的負責人,“代表常委會”聽取匯報,“發號施令”;有些地方在處理來信來訪時,多頭對“一府兩院”,甚至把個人意見當成常委會意見批給“一府兩院”等。這也是不符合人大及其常委會集體行使職權、集體討論和決定問題的根本特點的。
面對上述情況,必須貫徹憲法及法律的意圖和規定,使包括常委會主任在內的所有常委會人員清楚地知道,人大常委會是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集體行使職權,主任會議和主任個人均不能代替常委會行使職權。
(三)地方人大常委會會議內容應該進一步向社會公開。地方人大常委會召開會議,行使各種法定的權力,就是代表人民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力,因此,地方人大常委會會議的內容應該向全社會公開。監督法對此也有相應的規定。目前,許多地方僅僅是公開會議的議程和議題,對于會議內容公開不夠。現在媒體技術發達,完全可以完整、準確、及時地公開會議內容。
(四)地方人大常委會的旁聽和列席制度需進一步健全。程序性、規范性、法律性是人大及其常委會工作的基本特點。就旁聽而言,它是人大及其常委會十分重要的議事程序,但是,到目前為止,卻沒有法律、地方性法規或其他規范性文件來規范。由于無章可循,在實際工作中,存在很大的隨意性、不確定性,無法依法操作;而各地已有的規定也很不一致,造成法制的不統一。所以,建立和完善旁聽制度是完善人大常委會會議制度、工作程序和議事規則的重要內容,應該引起重視。
目前,地方人大常委會的旁聽制度多數是公民旁聽人大常委會會議的辦法。對地方人大常委會的旁聽絕不僅僅是公民旁聽,旁聽主體還有很多,應該把地方人大常委會現在比較成熟的可行的做法,規定在旁聽辦法里。
(五)地方人大常委會列席制度要嚴格執行。為了擴大常委會會議的參與面,確保常委會職權的行使,除了法定列席之外,一些地區還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邀請了一些人員列席常委會會議。但是,一些被邀請的代表、公民對議題不了解,或者被邀請的代表、公民不具有代表性。另外,法定的“一府兩院”的列席人員把列席常委會會議當作是參加一般性會議,甚至當成一種負擔。有的法定列席人員讓副手參加,甚至讓秘書代替。有的遲到,有的早退,致使會議失去了嚴肅性,使建議、意見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和解決,挫傷了常委會組成人員審議發言的積極性。
為此,必須嚴格執行法定列席制度,尤其是要把旁聽和列席從制度上明確區分開來。首先制定旁聽和列席辦法,然后統一制定旁聽法和列席法。
經過30年的建設,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基本上建立起了比較規范的會議制度。但是隨著實踐的發展變化,地方人大常委會的會議制度仍然需要不斷完善。只有不斷完善地方人大常委會會議制度,才能更好地落實黨的領導,落實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才能實現真正地依法治國,而完善地方人大常委會會議制度的標準就是法制化、程序化。以法律法規的形式規定地方人大常委會的會議制度,使會議具有清楚的操作程序,任何人都要依據這些程序來召開會議,違背了這些程序就是違法,就要受到追究。這樣,憲法和法律賦予地方人大常委會的各項權力才能得以落實,從而也就保障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
注釋:
[1]《地方人大常委會誕生記:彭真寫報告 鄧小平作批示》,載《人民日報》2009年6月3日。
[2]http://tibet.news.cn/gdbb/2009-07/07/content_7016938.htm.
[3]吳兢:《盤點三十年地方人大常委會》,見http://www.npc.gov.cn/npc/zt/qt/dfrd30year/2009-07/02/content_1509033_2.htm http://www.npc.gov.cn/npc/zt/qt/dfrd30year/2009-07/02/content_1509033_2.htm.
[4]中國人大網2009年6月17日。
(作者系北京市政治文明建設研究中心博士、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