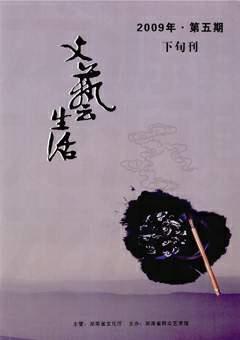以“傳統(tǒng)”的名義
羅麗娟
摘要:由2006年始于于丹的“國學(xué)熱”在2007年前后幾乎形成了一場“國學(xué)”奇觀。創(chuàng)同類電視節(jié)目歷史新高的收視率、近千萬冊演講錄的發(fā)行和“人民的孔子”、“女孔子”的呼聲,以及由網(wǎng)絡(luò)到報刊雜志、電視媒體,由“民間”到“學(xué)術(shù)”對于丹及其釋典方式爭論和關(guān)注,一場真正由“民眾”把握經(jīng)典、“普及”經(jīng)典的時代似乎在各媒體的喧囂中來臨。然而,在消費社會和商品經(jīng)濟的前提下,在這場“平民盛宴”中無疑遮蔽了許多內(nèi)在的關(guān)聯(lián)。本文從這場熱潮中不斷被提及的“個體”、“俗化”、“感悟”等集體狂歡與言說出發(fā),從中探析以“國學(xué)”名義下被遮蔽的中產(chǎn)階級消費趣味的實質(zhì)。
關(guān)鍵詞:國學(xué) 挪用 遮蔽 消費
中圖分類號:G206.3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09)15-
一、緣起:“人民的孔子”與經(jīng)典狂歡
以“奇觀”形容由于丹始于2006年《百家家講壇》的“國學(xué)熱”并不為過。2006年“十一”期間,時北京師范大學(xué)傳媒學(xué)教授于丹應(yīng)中央電視十套《百家講壇》欄目之邀,從幕后走向臺前,以“心得”的方式再一次觸及“國學(xué)”的關(guān)鍵——《論語》。
節(jié)目開播后,與節(jié)節(jié)攀升的收視率相呼應(yīng)的是經(jīng)整理的講演錄書籍所創(chuàng)造的各種圖書銷售神話:2006年11月26日,于丹的演講錄《于丹〈論語〉心得》在北京中關(guān)村圖書大廈簽售,創(chuàng)下了單場12600的記錄(據(jù)統(tǒng)計,這本書1個月的銷量即突破百萬);而隨后的《于丹〈莊子〉心得》則創(chuàng)下10個半小時簽售15260本的記錄,首月銷量達(dá)到200萬冊;截至到2008年3月,這兩本書在全國的銷售量將近1000萬冊(2004年中國大陸年度最暢銷書籍《狼圖騰》的發(fā)行量是100多萬冊;而2005年的兩部主要暢銷書《達(dá)?芬奇密碼》和《兄弟》的發(fā)行量分別是60多萬冊和80多萬冊)。因此有人說,其受大眾關(guān)注的程度只有當(dāng)年毛澤東的“紅寶書”可與之媲美①。
與驚人的圖書銷售神話和可觀的電視收視率同步的是于丹不斷被符號化的過程。在“于丹《論語》心得”不斷為央視重播的同時,于丹繼續(xù)沿襲“心得”的方式說《莊子》、講昆曲,甚至再一次以“感悟”的角度重新述《論語》。在現(xiàn)代傳媒的講壇上,于丹無疑成功構(gòu)建了“人民孔子”、“女孔子”的“師者于丹”身份。而在擁有公眾人物的符號功能之時,于丹也就同時從“國學(xué)講壇”走向了一個公眾人物所能覆蓋的話語場:作為一個具有“與時俱進(jìn)”性的“國學(xué)大師”對現(xiàn)代企業(yè)的“企業(yè)文化”策略演講、作為一個具有“心靈修復(fù)能力”的智者對災(zāi)區(qū)的慰問、作為一個優(yōu)秀的國民代表參與奧運火炬?zhèn)鬟f、作為一個具有“知性之美”的女性為時尚界所關(guān)注、作為一個具有民族文化身份(儒學(xué))的高端知識分子而出席高端企業(yè)峰會、會見他國元首……
同時,來自網(wǎng)民、學(xué)者在各網(wǎng)絡(luò)、雜志報刊之“挺”或“倒”于的喧鬧同樣參與了這場“國學(xué)”之熱:“挺于”一方,以活躍在網(wǎng)絡(luò)貼吧、論壇為代表的“魚丸”們認(rèn)為,于丹“為大眾找回了孔子”,其解讀方式“把古老高深的道理,淺顯地娓娓道來”,是“激活經(jīng)典”的創(chuàng)舉;以“學(xué)院”為代表的學(xué)者如李澤厚、任繼愈等,從經(jīng)典/文化“布道者”的角度予于丹以肯定,認(rèn)同其對“喚醒經(jīng)典記憶”的功勞。而“反于”一方,則主要集中在以馬千里等的“硬傷”、“軟肋”、“死穴”式的針對“原典”的邏輯性、準(zhǔn)確性方面的批評,以及以“十博士”針對“元典”的權(quán)威性、嚴(yán)肅性、神圣性方面的責(zé)難。同任何一次熱點問題一樣,激烈而紛繁的論爭無疑越發(fā)擴大和加強了問題的影響力和敏感度。
二、于丹的“國學(xué)”方式
于丹以前的“國學(xué)熱”,可以說幾乎都以“學(xué)校”特別是“高校”這樣的“象牙塔”為言說前提、以“精英”的界域出現(xiàn)在“大眾”視野之中。對于學(xué)院(高校)的“大眾”來說,無論是“讀經(jīng)運動”,還是“《儒藏》工程”,抑或是“孔子學(xué)院”、“國學(xué)院”的熱鬧成立——這些經(jīng)由媒體進(jìn)入社會群體視野的“國學(xué)”,或多或少地與官方、精英印記聯(lián)系在一起。對他們來說,那始終是在另一條(高端)軌道內(nèi)運作的文化資源和文化話題。
作為一種不同于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規(guī)范的釋典方式,“個體”“感悟”無疑是這場熱潮中的關(guān)鍵切入點。在這場“國學(xué)”盛宴中,于丹以一個可信的權(quán)威(異于“他者”的精英身份)不斷地承諾“個體感悟”的合理性。而這種承諾方式的完成,便是通過對自身視角的普遍化、庸俗化來獲取與受眾“同等”的想象,同時再以其身為大學(xué)教授、才華出眾者的身份予“同等”視角上的“大眾”以“精英”權(quán)威的共享。正如其一直所強調(diào)的,她所做的,只不過是“一個非專業(yè)的、普普通通的、也不算老的……中國女人,可以以她的這種方式把經(jīng)典讀了,而且心有所得。”那么,“所有的老百姓、普通人……都可以都能以她的這種方式讀,沒有多難。而且她讀完以后,會覺得挺快樂的。”所以,“至于這個女人是誰,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可以是于丹,也可以是別人,所以忘了于丹,記住這么一種感受 夠了。”在這里,于丹以“心得”的方式給儒家經(jīng)典以一個可以逃逸學(xué)術(shù)規(guī)范、學(xué)術(shù)邏輯和學(xué)術(shù)嚴(yán)謹(jǐn)性的切入點,從而消解了難以逾矩的“敬畏”之心,進(jìn)而,他們“把握”了“經(jīng)典”的釋義方式。“魚丸”中對“十博士”等的最大聲討理由,就是于丹所給出的經(jīng)典“庸俗化解讀”的可能。而這次突破“精英”隔閡的一個邏輯內(nèi)化方式,便是于丹所一直強調(diào)的“道不遠(yuǎn)人”:“經(jīng)典的價值或許并不在于令人敬畏到頂禮膜拜,而恰恰在于它的包容與流動,可以讓千古人群溫暖地浸潤其中,在每一個生命個體中,以不同的感悟延展了殊途同歸的價值。”②
于是,在“個體”、“體驗”的邏輯之下,一切“感悟”/“心得”式的闡釋都得到合理化的可能。在“魚丸”們看來,于丹“把圣人的言行從令人敬而遠(yuǎn)之的神圣殿堂請回充滿煙火氣的民間,把高深的天地人之道師友之道君子之道作出深入淺出的切合生活感悟的獨家解讀,讓你聽了有原來如此的恍然,有怦然心動的感激。”他們進(jìn)而指出于丹的“淺與俗自然與專家們的高頭講章道學(xué)氣息不可比擬,但專家的令人生厭,千冊起印的專著被打入冷宮,也是不爭的事實。”同時認(rèn)為“十博士”等“對于丹的批評,似乎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平等交流討論的范圍,而處處充盈了學(xué)閥的霸道,那種視國學(xué)精典為自家后花園,不誰他人偷窺,不容別人染指的蠻橫……”不難看出,基于“國學(xué)”一向以來的運作方式,“普通民眾”慣性地將之冠以“他者”的標(biāo)簽——一個難以觸及的文化資源,身為“國民”而未能共享“偉大”“民族文化”的距離感和抗拒感便在所難免。而于丹的“意義”,也是這場“國學(xué)熱”能夠引起如此關(guān)注的重要原因,便是對經(jīng)典釋義的“他者”——精英群體——傳統(tǒng)的突破,她把“雅”變“俗”,把“遠(yuǎn)”拉“近”,把“難”化“易”,由此獲得了廣泛認(rèn)可。
然而,“大眾”對于經(jīng)典“俗化”歡迎無非還是出于對經(jīng)典“精英化”的記憶。相對于經(jīng)典的原義來說,一種新鮮的把握方式更能吸引游離在“高墻”之外的“普通大眾”。他們樂于認(rèn)同并接受這種“個體性”、“感悟式”的釋典方式,一個潛在的前提便是保證“經(jīng)典”的所承諾的文化身份,這跟“精英”想象、“雅”趣味標(biāo)志無疑是同質(zhì)的。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于丹講經(jīng)典的內(nèi)容“俗化”,還不如說是于丹將釋典的方式“俗化”,而“普通大眾”樂于在自己手中實踐對傳統(tǒng)/經(jīng)典中所沉淀下來的文化優(yōu)越感的把握。與他們所認(rèn)同的“俗化”釋典方式構(gòu)成悖論的是,所追求的目的是出于對“精英”想象的“共享”,吸引并使他們?yōu)橹疇帄Z的,正是“精英”所制定的文化趣味分層。作為一個對這種“俗化”、“個體化”把握方式合理性的承諾者,于丹本身就以一個“精英”的身份提供了此“釋典自由”合理性的基礎(chǔ):高校(且是某種程度上的“名校”)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系主任、副院長。也即,一個“俗化”的方式,同樣是一個“精英”的方式。
三、遮蔽與挪用
正如戴錦華教授所指出的,自90年代以來,在“全球化”、“商業(yè)化”進(jìn)程中,中國的媒體的演變/轉(zhuǎn)型過程摻雜了權(quán)力、資本的重組和共享,其“大眾媒體”角色實為“新的權(quán)力”身份所置換。換句話而言,“經(jīng)典權(quán)力”已經(jīng)在某種程度上內(nèi)化為“媒介自身的權(quán)力”③。在此情境之下,以“直擊”的“現(xiàn)場性”異于傳統(tǒng)敘述方式的“另類新聞”(《焦點訪談》、《東方時空》)所能展現(xiàn)的“公正”是有限的,以“自由性”“自主性”為旗幟的地方娛樂/選秀節(jié)目(《超級女生》、《加油好男兒》、《夢想中國》)所實現(xiàn)的“民主”是“娛樂化”的④,而以“通俗化”解讀為特色的《百家講壇》,其所承諾的“個性化解讀”是有條件的——在“媒介的權(quán)利”下,它們同樣無法規(guī)避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 “捆綁輸出”。
在商品經(jīng)濟和消費社會的語境之中,作為具有歷史沉淀和傳統(tǒng)印記的“經(jīng)典”及傳統(tǒng)文化,被消費者有所甑選地記憶:樂于分享其“雅”而“優(yōu)”的價值想象,同時排除其繁雜的學(xué)識積累要求。于是,借“國學(xué)”之名,以外延所能指之趣味來換取某種價值立場及其快感,是為消費之實。公眾所需要的,并不是來自傳統(tǒng)文化的一種實踐方式和把握,“而是一種充斥著符號和參考、對學(xué)校知識的模糊回憶和時尚知識標(biāo)記的奇怪主體”⑤。這次由于丹所論《論語》、《莊子》及昆曲所引發(fā)的“國學(xué)”熱潮,就是以“國學(xué)”之名所行的消費之實。在這里,“國學(xué)”的外延被挪用,而“深度”的意義被置換,“大眾”/“消費者”在這場熱潮中所關(guān)注的,是由一個異于傳統(tǒng)經(jīng)學(xué)釋義者的“精英”所承諾的“釋典”權(quán),是一場與束閣高墻共享“雅趣”的消費快感。與其說“大眾”在這次熱潮中“受到了經(jīng)典的洗滌”,還不如說他們需要獲得“消費社會公民資格而必須擁有的最小一套同等物品”⑥。同被資本和階層以及官方本土文化策略所架空的“國學(xué)”意義一樣,這次遍及各個年齡、階層的“國學(xué)熱”,真正的“國學(xué)”內(nèi)核同樣缺席;而作為這場熱潮的“主導(dǎo)者”,于丹同樣為大眾所“塑造”,她不斷以“大眾”“普通百姓”中的成員反指自身,以社會傳統(tǒng)和主流意識所認(rèn)同的角色身份不斷構(gòu)建知性“女性”、“人妻”及“人母”的形象。在其不斷“隱匿”強勢身份的策略中,于丹以這種“退場”強化了其內(nèi)在邏輯的合理性和權(quán)威的可信度,在這場人們都可以“忘了于丹”的“國學(xué)盛宴”中,于丹始終以一中潛在的方式把握現(xiàn)場;而在“媒介”與“權(quán)利”有著深遠(yuǎn)牽連的語境中,作為營銷策略的“個體”、“感悟”釋典方式,在行使一種市場策略之時,也同樣受制于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規(guī)范。在這個意義上,“個體”性的話語狂歡實為意識形態(tài)框架內(nèi)的另類表現(xiàn)方式,它最終不能僭越官方的主流敘事。終其而言,正如2007年前后的極度喧囂及隨后的沉寂一樣,摻雜在于丹“國學(xué)熱”話語中的,只是一種以“國學(xué)”為名義的文化消費行為,一場由“個體”、“俗化”、“感悟”遮蔽的又一場主流意識形態(tài)修辭。
注釋:
①貝淡寧.《論語》的去政治化——于丹《論語》心得簡評.讀書.2007(8).
②于丹.于丹《論語》心得.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6年1版.
③戴錦華.隱形書寫.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1版.第23—41頁.
④滕威.尋找自我與想象民主——解讀2005年的“超級女生”奇觀.話題.2005(5).
⑤⑥【法】讓?波德里亞,張一兵編.消費社會.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1版.第105—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