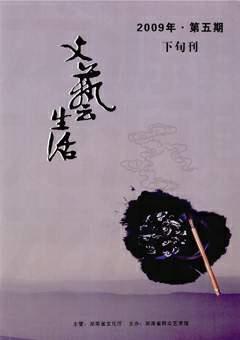略論聽證報告的效力
閔祥龍
摘要:正式聽證的法律文件的效力應實行嚴格的“案卷排他原則”,成為立法的唯一依據,而不能僅僅作為一種參考資料。在非正式聽證中,不一定要實行嚴格的“案卷排他原則”,只規定聽證的法律文件對立法主體有一定約束力,立法主體必須斟酌聽證筆錄作出決定即可。
關鍵詞:聽證報告 官方認知 案卷排他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09)15-
一、國外立法聽證程序中案卷材料的效力
在西方,立法聽證是一種咨詢性機制,其既無決策權力,議會也無遵從其意見的義務,因而,聽證的法律文件對立法主體的決定僅有一定的約束力。然而,與聽證有關的很多章程均希望加強議會對聽證會的善后工作,讓法案的審核過程更加透明化,使參與聽證會的證人感覺更受重視,在聽證會上投入的資源能更有效地得以利用。其中,在美國,行政立法聽證的案卷材料具有完全的拘束力,實行 “案卷排他原則”。行政機關的立法行為必須根據案卷作出,不能以在案卷之外以當事人不知道或沒有論證的事實作為根據,否則其行為即屬無效。“案卷排他原則”的目的在于維護聽證的公正性,如果行政機關可以根據聽證以外的證據作出決定那么聽證權的行使就毫無意義了。當然,“案卷排他原則”亦非絕對,其例外是“官方認知原則”,依據這一原則,行政機關可在聽證記錄、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之外認定案件事實,并以之作為裁決的依據。“官方認知原則”的限制是:(1)案件中有關核心問題的司法性事實不能認知;(2)所認知的事實必須是顯著而周知的;(3)所認知的事實及根據必須明白指出;(4)當事人對官方認知具有反駁權。由此看來,美國的“案卷排他”是原則性規定,而“官方認知”又部分地保障了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其并非完全不能采用聽證法律文件之外的其他材料。
二、我國地方立法的相關規定
我國地方立法的實踐中,一般是將聽證報告作為是否立法和修改法規的依據之一或重要參考。各地有關聽證報告效力的規定,一般都是原則性的,沒有硬性的強制性的規定。事實上,作為一種立法機關主導下的、自上而下的促進立法民主化的制度,立法聽證的效力也是有限的。立法活動中,立法機關是決策主體,通過一部什么樣的法律,最終取決于立法機關組成人員的態度,而非聽證會的意見。如《青海省人大常委會立法聽證試行規則》第23條規定:“聽證報告應當印發常務委員會會議,并印送聽證陳述人。省人大法制委員會在審議法規時,應當對聽證會提出的意見進行審議,并在審議結果報告中對聽證會提出的意見采納情況予以說明。”《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立法聽證條例》第25條規定 “常委會主任會議和常委會會議應當重視聽證報告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將報告內容作為審查、修改地方性法規草案的重要依據。法制委員會在審議結果報告中,應當對立法聽證會上公眾提出的主要意見的采納情況予以說明。”
三、“聽而不證”與媒體公開
實踐中,對那些大張旗鼓開聽證會,虎頭蛇尾,不采納或很少采納聽證會意見的情況,人們形象地稱為“聽而不證”,這種聽而不證的現象自然不利于聽證會功能的發揮,甚至可能使人們失去對聽證的信任和興趣,破壞立法聽證的制度化建設。對此,除了在相關的立法中作上述原則性規定外,加強聽證的公開化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辦法。
目前,媒體對聽證會的關注主要集中在現場報道等一些公開化的環節,事實上,如聽證會結束后,聽證報告被采納的程度等情況也應當得到相當的關注和報道。這種情況的公開更有利于公民了解聽證會的實效,也更有利于聽證制度的宣傳和發展。在這一方面,聽證組織機構應當主動、盡量公開可公開的信息,如會議的事前公告和宣傳、現場記錄、事后簡報等,也應當鼓勵媒體進行采訪報道、轉載報道,充分運用電子媒體,如電視、電臺,傳統文字媒體,如報章、雜志,和新興的網絡媒體進行廣泛、全面、深入地報道,增加公眾可接收到的信息量,用媒體這種“第四種權力”的力量加強對立法聽證的監督和保護,使其更好地發揮這種程序制度的功效。
四、不同的聽證程序中聽證報告的不同效力
正式聽證中,耗費了大量的立法成本,按照完備的聽證程序進行了嚴格的論證,其結果的科學性和公正性應得到充分的尊重,因此,正式聽證的法律文件的效力應實行嚴格的“案卷排他原則”,成為立法的唯一依據,而不能僅僅作為一種參考資料。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Van Devanter曾說:“制定法所規定的對于沒有列入聽證筆錄的證據一律不得加以考慮的原則必須得到遵守,否則聽證的權利變得毫無意義,如果決定者在作出處分時隨意背離記錄,或咨詢他人作出的事實認定和法律見解,則在正式聽證中提出的證據和辯論,沒有任何價值。”而在非正式聽證中,不一定要實行嚴格的“案卷排他原則”,只規定聽證的法律文件對立法主體有一定約束力,立法主體必須斟酌聽證筆錄作出決定即可。而當其不采用代表的意見時,則須說明理由。
無論正式聽證還是非正式聽證,均應建立、完善代表意見的回應機制。這一回應機制首先要求聽證機構必須對聽證會上的意見進行認真的整理、分析,其工作包括:聽證會提出了哪些意見,立法主體在立法中采用了哪些,沒有采用哪些,理由是什么等;另外,意見回應還應當以公眾易于知曉的方式加以公布,對于聽證代表,則應采用書面的方式正式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