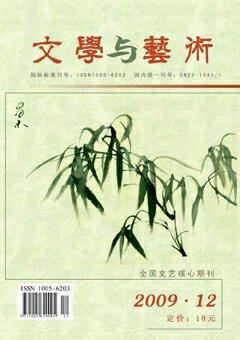對《喜福會》中男性形象的解讀
李 力 曾麗香
【摘要】在譚恩美的代表作《喜福會》中,都是以女性為其描寫對象,本文通過對文本中移民前中國父親形象,移民后的華裔男性形象及美國白人男性的解讀,闡明作者的女性主義立場。
【關鍵詞】男性形象;女性主義
譚恩美作為當今美國華裔女性作家中的佼佼者,以其嫻熟的寫作技巧,靈活的時空跳躍性,以及對華裔女性的生存狀態的深切關注,成為了繼湯亭亭之后,美國少數族裔作家群中一顆璀璨的明星。其處女作《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 》,一經出版就引起了美國主流社會讀者以及美國華裔的極大興趣,位列全美最暢銷小說達9個月之久,并被華裔導演王穎改編成同名電影,使得譚恩美迅速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作家之一。細讀譚恩美的《喜福會》,筆者發現,文本中16個相互交織的小故事中無一例外都是以女性為其描寫對象,而男性形象基本上處于一種缺失形態或僅僅作為陪襯。男性的缺席及陪襯成為解讀譚恩美小說的一把鑰匙,讓我們更深入的了解到作者極力為女性爭取發言權的立場。
1 移民前的中國父親形象——封建父權,夫權的代表
當人類社會從母系社會過渡到父系社會,女性在人類歷史中的優越地位便蕩然無存,成為男權社會的附庸品,誠如波伏娃所言:“女性并不是生就的,而寧可說是逐漸形成的”。長久以來,在傳統的中國家庭中,男性擁有至高無上的父權和夫權,女性則始終處于一種受壓迫,無權利的從屬地位。這種傳統思想已經滲透到中國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女性從小就被灌輸“重男輕女” “男尊女卑”“妻憑夫貴 ”等父權社會封建思想。文本中的母親恭琳達從小就被家人許給黃家做童養媳,受盡了折磨,過著非人的生活,“受的傷害太多了,也就麻木了”從踏入黃家的第一天起,她的婆婆就教導她凡事都要以丈夫為中心。而琳達也漸漸將這種思想融入自己的血液中,.然而她的乖巧,懂事也并沒有改變她在黃家的地位,無法生育的事實使她無法在家族中立足,最終她依靠自己的機智才得以從封建牢籠中逃脫出來。而另一個華裔母親顧映映,在16歲的時候按照家人的安排,嫁給了姑父的一個朋友,并愛上了他 ,處處取悅于他。然而她的癡情換來的卻是丈夫情感上的背叛,最終她殺死了腹中的胎兒以此報復丈夫的無情。
文本中刻畫的幾位移民前的父親,無論是恭琳達性無能的丈夫,安梅母親所遭遇的那個封建集權式的天津商人吳青,還是映映那始亂終棄,尋花問柳的丈夫無一不是封建夫權,父權的典型代表。
譚恩美正是通過對移民前父親的描寫,譴責了封建社會的童養媳,一夫多妻制度,及父母包辦婚姻,給女性的肉體及精神帶來了無盡的痛苦。深刻地鞭撻了男權中心主義所造成的女性的悲慘命運。
2移民后的中國父親形象——沉默的弱者
文本中,“沉默的父親”這個意象反復出現,而父親這一角色也形同虛設,被作者有意地忽略了。華裔男性作家趙健秀曾經指責譚恩美的作品是對華裔男性形象的歪曲,其創作僅僅是為了迎合美國主流文化及讀者的口味,屬于美國主流文化輻射下“東方話語”的反映。這種評述有失偏頗,追溯華裔的歷史,文本中對華裔男性的描述及其刻畫是有一定歷史事實依據的。隨著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第一個排華法案,以及1902年和1904年類似法案的頒布,華人的處境日益艱難,大量的勞動力的涌入給白人的就業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因此早期華人移民在勞動力市場上常常因種族歧視而受到白人男子的排擠,在勞動力市場上失去競爭力。為了生存,他們又不得不轉而從事白人男子所不屑的飲食業,洗衣業,這些只有女性才會從事的行業。加之語言溝通上的障礙,使得華裔男性的活動范圍僅僅局限于唐人街,在面對白人男性的時候,常常顯得膽小和懦弱。于是華人男子常被賦予“缺乏男子氣”的刻板印象,在美國主流社會中的形象也一直無法擺脫被閹割和女性化的命運。作品中對移民父親的刻畫正反映了這一現實。身處異國他鄉,華人男性在傳統社會中的支配地位也漸漸消失,而在故國家庭中原有的至高無上的父權,夫權也隨之消隱。為了生計,女性和男性共同成為家庭收入的提供者,而女性還額外承擔了撫養和教育孩子的責任,失去了原有生產方式和社會組織結構依托,華人男性在家庭中顯得脆弱而且無力。在女兒們的眼中,他們成為“無聲的一族”,
而在文本中華裔女性每周一聚的喜福會中,盡管也有父親的參與,但父親總是游離于女兒與母親心靈的外圍而無法進入。在她們的世界里,男性是令人不滿和可以忽略不計的。華裔女性對父親的“拒斥”就是要表明她們的世界是一個父親缺席的世界,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參與卻依然絢麗的世界。
3白人男性——華裔女性的“救世主”
久經磨難的華人婦女在離開家園,遠涉重洋之際,對于即將抵達的異域國度充滿了美好的向往,將其想象成消除性別壓迫,性別歧視的人間天堂。
然而,現實卻是如此殘酷,在美國這樣一個標榜自由,平等,民主的國家里,華裔女性爭取平等的斗爭卻是如此步履維艱。在這樣一個充滿敵意和種族歧視的異域國度,語言上的障礙加上白人男性的種族優越感不僅僅阻礙了夫妻間平等交流的機會,也使得白人男性順理成章的剝奪了華裔女性言說自我的權利而成為華裔女性的代言人。
而對于從小喝著可口可樂長大的美國第二代華裔女性,她們從小接受西方的現代教育。對本族文化的不滿及本族男性的失望,加之在種族社會中被排斥的經驗促使她們渴望獲得主流社會的認可。因此, 《喜福會》中的女兒們大多選擇白人男性作為丈夫或同居伴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與白人男性的結合正是華裔女性融入主流社會的證明,然而,跨越種族,和文化界限的婚姻卻并非美好愛情的開始。他們的黑眼睛,黃皮膚的亞裔特征成為了她們融入主流社會的最大障礙。 作品中白人男性的形象也是通過幾位女兒的描述呈現出來的。文本中,白人男性儼然成為了華裔女性眼中的英雄,成為將華裔女性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的救世主。
白人男性的高高在上恰恰與華裔女性的卑微、低下形成鮮明對比。 作品中對幾位白人男性的刻畫,正凸顯了華裔女性的弱勢地位以及在婚姻中的不平等關系。華裔女兒麗娜,與丈夫共同創立了公司并付出了同等的努力,然而丈夫的收入卻是他的七倍。在家庭中,她除了要和丈夫共同承擔家里的一切開支,有時還不得不承擔丈夫的開銷,最終是母親一語點醒夢中人,讓她重新思考與丈夫這種不平等的關系,挽救了自己的婚姻。
對于生活在美國的華裔女性,長期以來她們不僅承受來自族內男性的性別歧視,更遭受著來自以西方意識形態為代表的白人種族,文化以及白人男性等諸多方面的多重壓迫和排擠,處于邊緣化的地位。在這樣一個以男性話語作為絕對權威的環境中,女性的話語權被無情地褫奪,長期以來處于一種失語狀態。譚恩美正是從女性主義的立場出發,以其敏感的女性意識和獨特的族裔身份將長期以來身處東西文化夾縫中的生存經驗作為其創作的來源,利用手中的筆作為武器,書寫了逐漸覺醒的,具有主體意識的女性形象,徹底顛覆了男權中心神話的統治地位,使女性告別了“空洞的能指”,最終發出屬于自己的聲音。
【參考文獻】
[1]Amy Tan. The Joy Luck Club [M] New York: Ivy Books, 1989
[2]倪大析. 華裔美國文學一瞥[J] 世界文化,1996(3)
[3]柏隸,西方女性主義文學理論[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