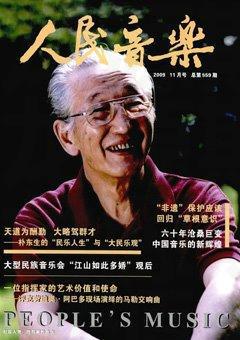天道為酬勤 大略駕群才



一
今年以來,樸東生先生為回顧、總結自己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音樂生涯,一連出版了《民樂?人生——樸東生藝術生涯六十年》(紀念專版)、《民樂紀事60年》(中國文聯出版社)和《指揮藝術概論》(上海音樂出版社)等三部著述。前著亦圖亦文,“回放”了他六十年的“民樂”①之旅;“紀事”以600余頁的巨制,縱論六十年來民樂之創作、表演、教育、樂改、樂隊、樂事、樂人等,無論長、短、繁、簡,無論評、述、議、敘,讀者皆可以從中切摸到當代民樂歷史的“脈動”;后者則是他數十年來專攻一業的心血之作,有切身體味,有理論提煉,散發著濃濃的學術氣息。認真細致地讀完它們,我們不僅能見到一個個體生命為追求人生大目標所遭遇的曲折和苦澀,還能見到一位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在“民樂”之海中拼搏者的執著和歡悅,更能通過他個人的成長史窺見當代民樂藝術“舉手投足”的身影!作為當代民樂界的一個有代表性的人物,個人與時代,歷史與文化,藝術與人生,在這位“民樂老人”娓娓道來的“文化敘事”中,交相重合、時隱時顯,讓讀者生發出許多感慨!
如果以1919年5月正式成立的“大同樂會”作為“民樂”正式登上現代中國文化舞臺計算,則今年正好是“民樂”的九十華誕。而這九十年又恰好可以分成三個三十年,即1919—1949;1949—1979;1979至今。第一個三十年間,民樂曾稱作“國樂”。在九十年的“民樂”史上,它是一個“改舊迎新”、開拓建設的“起步”時代。鄭覲文、劉天華二位前輩先后在合奏、獨奏藝術上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進、創新、試驗,鄭覲文于1924年組織的“女子古樂團”,以弦、管、簧、械的編制,為現代“民族管弦樂”闖開一條新路。1926年,他還將柳堯章根據琵琶古曲《潯陽月夜》改編的樂隊合奏,親自定名為《春江花月夜》,遂成為現代民樂合奏的開山之作。同一時間,劉天華創作的二胡、琵琶獨奏曲,則樹立了民樂獨奏藝術的新風尚。古人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鄭覲文、劉天華所處的時代,乃現代民樂的“拓荒”期,他們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氣,讓現代民樂有如此的高起點、新曙光,堪稱中國民樂的元老、巨擘!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民樂也隨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史學界稱之為民樂的“推展期”。盡管因為1966年“文革”驟發而停滯一時,但民樂在此階段的樂隊規模、專業院團,合奏、獨奏作品的數量、體裁形式以及社會認知度等,與第一個三十年迥然有別。“民樂”,成為與其他專業音樂品種并足而立的代表性體裁。后來的事實證明,暫時的停頓為第三個三十年積蓄了巨大的內在力量。因此,我們把1979年以后稱為“民樂的春天”。站在歷史的立場上看,這三十年可以歸結為現代民樂的“逐步成熟期”。樸東生先生恰好在1949年投入“民樂”領域,此后六十年間,無論是演奏、指揮,還是創作、理論研究,無論是作為普通的“民樂人”,還是近二十年來作為本領域的引領者,他都與“民樂”緣分難解、廝守不離,以至“民樂”成為他的人生主旨,他的“人生”則也浸透了“民樂”。事業與生命的這種交融重合,不僅存乎于上述三著的字里行間和不同年代的照片中,也顯露在他幾十年來為“民樂”而奔波于海內外的行跡中。其言、其德、其功,無一不與“民樂”相關。這是我反復拜讀上述三著的深刻印象,也是近十余年間與樸先生一來二往的直接感受。
那么,在長達一個甲子的歲月中,樸先生如何與民樂結緣?如何在自己的實踐中去領悟民樂的真諦?又如何在“民樂”旅程中建立起自己的“民樂觀”?這種“民樂觀”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經歷了怎樣的變化?或者說,他如何從“微觀”的民樂(我稱之為“小民樂觀”)步入“宏觀”的民樂(我稱之為“大民樂觀”)?他究竟有著怎樣的與一般民樂人不同的“民樂情懷”?要全部回答這些問題,可能需要一篇長文甚至一本專書。本文所論,僅想談樸先生六十年的民樂情緣和他在兩個三十年中“民樂觀”的變化。
二
舉凡一個在事業上有所作為的人,都因為他們有明確清晰的“行業觀”,而這個“行業觀”又常常與他們的人生觀緊緊聯系在一起。大概因為這個緣故,樸先生才在《民樂?人生》的封面上,寫下這樣一段感言 :“每個人或長或短都有一生,不同的職業、不同的境遇又構成了不同的人生。民樂則構成了我六十年的藝術人生。”②可見,他是把“人生”與“事業”視為一體,認為“民樂”與他的“人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 這不僅是他全部著述的總“提要”,簡直可以看成他的人生“提要”。不僅如此,他一向自詡為“民樂人”,稱學習民族樂器的孩子為“民樂兒童”,把“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稱為“民樂之家”。由此看出他的“民樂緣”是何等的深!“民樂情結”又是何等的重!而長期支配這種民樂“情”和“緣”的,則是他的“民樂觀”。這是我們解讀20世紀初葉以來所有“民樂人”的思想、追求、事業心、使命感的關鍵詞匯。在時代因素影響下,不僅不同年代的民樂人有不同的“民樂觀”,而且,具體到一個人,他的民樂觀也會因客觀因素及主觀處境的不同而發生變化。這一點,我在樸先生本人的閱歷中也很明顯地感受到了。
樸先生前三十年的民樂生活,主要是在演奏、創作、指揮等實踐性很強的活動中度過的。起先,他學習笙、揚琴、板胡、二胡、琵琶以及小號、雙簧管、單簧管、薩克斯等許多中外樂器的演奏;幾乎在同時,他又嘗試民樂合奏、獨奏的創作。未久,他又擔任了樂隊指揮。在五十年代,出于需要而一人兼學幾件樂器的“多面手”頗為多見。但像他這樣“跨度”很大的“三棲”民樂人,卻未必很多。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每個專業領域都有所成,特別是創作和指揮。音樂創作從早期的《苗族見太陽》(合奏)、《在草原上》(二胡)、《東湖之春》(揚琴)、《歡慶勝利》(配器)、《馬蘭花》(童話劇配樂)③等到近期的《牡丹仙女的傳說》(民族交響詩,1986)、《中華頌》(交響合唱,1994)、《漢俳》(聲樂組曲,2000),前后持續五十余年。指揮自五十年代至今從未停歇,長達近六十年,并在下放當木工期間撰寫、出版了國內少見的指揮專著。④如果這些長期廣泛多樣的實踐活動是在安定、平靜的環境中堅持下來的,似乎還可以理解。實際的情況是,三十年間,他四進四出北京,又多次支農、支老(區)、務工,輾轉漂泊于沈陽—北京—延安—沈陽—盤錦—沈陽—北京—沈陽—北京之間,生活的艱辛、奔波的勞累、心境的苦澀可想而知。然而,所有這一切,都未能改變他對民樂持續不斷的鉆研和發自心底的摯愛。更可貴的,是他通過這樣的實踐,逐步建立起與其他同行不盡相同的“民樂觀”。
如前所述,同樣在民樂界,作為從業者,人們的事業觀及其價值判斷未必一樣。由于專業不同、實踐層面不同,人的專業視野乃至文化情懷也都會有差異。如果是一位某件民族樂器的演奏家,或者僅僅從事民樂創作或指揮,他自然會高度關注這門專業的方方面面,而無余力顧及其他。建立在這一專業視野上的民樂觀念,可能會是較為單一甚而是偏于狹窄的。我們不是苛求,更不是責難這些同行,而只是指出這樣的民樂觀念是“微觀”的或者屬于“小民樂”的。
與上述同行不同,樸先生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同時以作曲、指揮從事民樂活動,且在個人境遇上又比別人多了一些坎坷,他的民樂觀念顯然有別于他人。其中,曲折的歷程磨礪了他對這份事業的執著追求,多專業的實踐加深了他的民樂情懷,著書立說提升了他的民樂素養,頻繁調動擴展了他的文化視野,由此而積淀起來的,就是他那時已經超越某類專業的“民樂觀”。這種觀念,一定程度上擺脫了長期存在于民樂界單一專業的某些較為狹隘、封閉的思維方式和門派、行幫作風,而能以一種較為開放、達觀、兼容、宏闊的心態對待本領域的現狀、人事及各類專業之間優長劣短等關系。我同時注意到,幾乎從進入“民樂”領域那一天起,樸先生就養成了善于思考、勤于歸納、有了心得就“舉一反三”的良好習慣。例如,收在“紀事”中的五十、六十年代的幾篇早期論文,既涉獵“樂改”、“樂曲編配”,也論及“業余民樂隊組織”和專業團體表演,顯出他思想的活躍和關注面的寬泛。就連在“文革”期間偶然讀到一則有關日籍指揮家小澤征爾獲大獎的報道,都會在他內心深處“引發”出“強烈的震撼”:“同生于沈陽的同齡人,同一指揮專業,反差之大,天壤之別。經過一段痛苦的思考,我有了新的認識與抉擇……我將小澤征爾的輝煌業績,轉化為我要刻苦奮進的動力。”⑤正因為有這樣自我激勵的思考與動力,他才堅持了十年,一邊干繁重的木工活,一邊寫作《樂隊指揮法》。所以,我認為,樸先生在前一個三十年所遵循的是一種“實踐的民樂觀”,其特點則是在廣度和深度上都超越了一般單一的、較為狹窄的“微觀”民樂觀念,而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我們稱之為“中觀”的民樂觀念或“實踐的民樂觀”。這一民樂觀,帶有前三十年鮮明的時代特征,同時也與樸先生本人暢達的民樂情懷、特殊的人生經歷有密切的關系。
三
中國自七十年代末起,可謂驟然而變:天變、地變,人更變!
政治、經濟、文化、學術、藝術……每一個領域都意氣盎然,每一個領域都把“建設性”視為重中之重!
“民樂界”若何?
它當然不例外。所有的民樂人、所有的專業領域:創作、教育、表演、理論,無一不充滿了創造、建設的熱情。以歡欣鼓舞之情,迎接又一個三十年——一個將闊步邁進的、具有嶄新風貌的民樂三十年!
樸東生先生呢?
他當然也和大家一樣。1977年,他以“民樂”指揮家的身份回到了闊別十八年的北京,也是他四進四出最后一次“進”北京。北京是成就了他民樂事業的向往之地。所以,這次“進”來,顯然是一個幸運的預兆:他的民樂人生第二個三十年的幸運的預兆。
1979年春,中國音協在成都召開全國工作會議。會議的主題:迎接中國文藝的春天。會上,他與彭修文、秦鵬章二位同行、摯友相遇。他們不約而同地議論起一件所有民樂人都關心的大事:成立“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以推動今后民族管弦樂事業。盡管這件事因種種原因推遲了六年,但成都會議上三個民樂中堅發起的動議,卻成為未來三十年民樂進入“逐步成熟期”的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⑥。也是樸先生從他的“實踐的民樂觀”踏入“宏觀民樂”的“大民樂觀”的關鍵之舉。
也許有人要問,回到北京以后樸先生的創作活動、演出活動極為頻繁,先后完成了幾部大型作品,還多次出國,赴港臺指揮、當評委,中間還有幾年出任文化部中國錄音錄像出版總社老總⑦等,而“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不過是一個聯絡民樂界同行的民間社團,為什么它反而在樸先生第二個民樂三十年具有如此巨大的意義呢?
是的,誠如樸先生自己所言,這是他“收獲”的年代、成熟的年代。他“收獲”了什么呢?就個人而言,確實成績驕人,獲譽多多。但在他生命的深層,他最看重的,他所要“收獲”的,或者說他數十年如一日所追求的,卻是“民樂”這件天大的事。無論在生活“慘烈”的年代,還是事業紅火如日中天之際,民樂對他而言,幾近“宿命”。所以,在1986年8月8日“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在北京正式成立后,他作為三大創會者之一,即以副會長兼秘書長的身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前十年,在彭修文先生的主持下,“民族管弦樂學會”的所作所為,多以組織演出、比賽為主。特別是1987年首屆中國藝術節上的千人“中華大樂”,亙古未有,影響深遠,是“民族管弦樂學會”在公眾面前第一次漂亮的登臺。1996年,畢生為“民族管弦樂”事業奮進的彭修文先生不幸辭世,樸先生剛好在那一年從“中錄”社長的位置上退下來,天遂人愿地擔當起學會會長,他的“民樂人生”因此又踏上新的旅程——所謂“勞碌的晚年”。“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從此也邁入它意氣縱橫、闊步向前的新時期。
自1996年至今,整整有十三年了。十三年,無論是對于一個不完全適宜于民間社團生存的社會,還是對于一個從“花甲”進入“古稀”之年的老者來講,都不能說短。而恰恰在這十余年間,不畏勞碌的樸先生把“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做”得紅紅火火,“做”得很“大”。
所謂“大”,自然包括學會本身的辦公房間、辦公人員、聯絡空間、“家業資產”這些物質因素。但對于樸先生來說,他更想要的是學會整體架構、發展思路、人文內涵、參與相關活動的“大”,是“大氣度”的“大”,是民樂一定要告別“小家碧玉”,走向“大民樂”新時代的“大”!
可以說,他在十三年的風雨行程中所期盼的,就是以“學會”的全方位運作為契機,實現自己的大民樂構想和“大民樂觀”。
那么,現在的狀況如何?結果又如何呢?準確、完滿的回答應該由學會數千名會員來完成。本人僅以一個20年來一直關注學會進展的普通成員所了解的事實在這里給出自己的答案。
我認為,學會自從1997年由樸先生引領以來,在他本人追求的“大民樂架構”思想的驅動下,學會的運作是良性而健康的。這里僅舉數例:
1.自2001年起,學會內分別成立了古箏、揚琴、笙、笛、胡琴、打擊樂、三弦、嗩吶、琵琶等16個專業委員會,利用每個專業的“條塊”關聯,擴大學會的內在結構。依照“結構決定功能”的規則,學會的專業功能由此大大延伸。
2.依照國家政策,協助、推進各省、區、市成立相應級別的“民族管弦樂學會”,目前已有八十七家,學會與之建立了緊密而友好的關系。各專業委員會有如“小網”,各省區“學會”有如“大網”,大、小網相連,不僅大陸,就連港、臺、澳,連新加坡、日本、馬來西亞的“民樂人”都在學會的“大家”里了。
3.自1997年獲準參與全國民樂考級,已堅持十二年。這是學會參與社會音樂教育的重大舉措。當國民素質教育成為政府主動倡導、民間積極響應的文化傳承熱點之際,民樂考級肩負大普及的歷史重任。樸先生主管學會未久,即敏感意識到學會參與民樂大普及的機遇,積極申辦,從而極大地延伸了學會的社會功能。
4.與政府文化宣傳主管部門合作,參與重大賽事,促進專業民樂水準的提高和宣傳。學會十余年來主辦、參與各類民樂大賽無數,其中特別有意義的是參與了某些政府文化宣傳部門主辦的專業比賽。三次民族器樂“文華藝術院校獎”和兩次CCTV民族器樂電視大賽,樸先生也都參與了策劃、評審工作。這對于民樂專業表演水準的提升、擴大民樂在千萬觀眾中的認知度、對民族器樂作為傳統文化遺產進入國民生活并促進保護傳承都起到難以估量的作用。特別是電視器樂大賽的舉辦,成千百倍地增加了民樂的觀眾數量,為民樂藝術進行了一次空前規模的大普及。在數千年中國樂器歷史上,在九十年的民樂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機遇是歷史賦予這個時代的,而學會與樸先生進入策劃層,既是全體民樂人多年努力奮斗的成果,也是樸先生帶領學會這個團隊為實現“大民樂”架構付出艱辛勞動后主動爭取來的!應該說,到民樂的第三個三十年臨近結束的時候,從上個世紀初的“起步”,到上個世紀中葉的“推展”,再到七十年代末的“逐步成熟”,無論我們意識到與否,我們都在為實現這個“大民樂”架構而不懈地拼搏、奮進!
現在,它的曙光終于出現在我們眼前了!
四
最后,我們來專門解讀“小民樂觀”與“大民樂觀”的內涵與外延以及樸東生先生“民樂人生”給我們的啟示。
所謂“小民樂觀”者,主要是指人們從一件樂器或一個民樂的專業看待中國民樂文化這種觀念而言。以往,受到歷史條件和專業視野的局限,某些從事民樂演奏的同行,常常只看重自己的技藝,到了一定水準之后,便要“開宗立派”, 進而漸漸排斥、低視其他同行,并進一步形成一種保守、封閉的門派思想和“行幫作風”。等到諸多樂器成為一門專業而進入音樂院校后,門派思想又與“本位主義”(也可以稱之為“單位主義”)相結合,最終,這種“小民樂觀”漸漸蔓延滋長,給專業民樂界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并在某種程度上制約了民族器樂演奏藝術的發展。
當然,不是說凡以一件樂器從事專業演奏的同行都會先天地具有這種偏于保守的“小民樂觀”。以劉天華先生為例,他雖然終生以二胡、琵琶“改進”傳統民族器樂藝術為旨趣,但讀他的《我對于本社的計劃》和他起草的《“國樂改進社”緣起》中關于改進“國樂”的一系列務實而又遠大的設想,再看他在短短的生命歷程中的所作所為,誰會說他的“民樂觀”是“小”而狹窄的呢?我們也可以討論樸東生先生民樂思想的形成過程。應該說,他也是從學習某件樂器進入民樂藝術的,但他卻能夠與時俱進。凡進入一個專業領域,他都能下一番苦功夫,學習、思考,不斷擴展視野,努力提升鑒別力,逐步從微觀的民樂(小民樂觀)進入“實踐的民樂觀”,再進一步形成“大民樂觀念”。反觀我們的一些民樂朋友,雖然在某個專業領域已經是教授、導師,甚至被尊為“大師”了,但一進到專業交流的環境,或某些比賽場合,則“門派思想”、“宗(流)派”傾向畢現,永遠視自己和自己的學生為最高,甚至把學生視為私有財產、不惜犧牲學生的榮譽而保全自己的所謂“臉面”。此種狀況,我們在近年來的各種大賽上每每有所見,其根源實際上就是前文所說的“小民樂觀”在繼續作祟。對此,我們如果視而不見,則民樂要在它的第四個三十年繁榮進步,我看難矣!
所謂“大民樂觀”,是建立在如下基礎之上的一種民樂觀念:1.民樂是數千年中華優秀文化遺產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2.民樂是在中國傳統器樂藝術基礎上,適應20世紀新文化、新聽眾的要求而成長起來的一門器樂藝術;3.民樂是當代中國文化大家庭的一個重要成員,它既是一門表演藝術,也是一種民族文化;4.當代民樂必須不斷克服傳統民樂傳承、交流中存在的封閉、保守、門派思想,以民樂的整體進步、繁盛為榮,讓某一類器樂成為“大民樂架構”中的有機組成部分,讓每個民樂人都樹立起“民樂家族”的自豪感,相互團結、自尊自重、相互交流,共同進步。唯此,民樂才會有燦爛的明天,才會在當代文化大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才會受到廣大民眾的關愛。
當前,大、小民樂觀都在民樂界存在,有時處于相持狀態,有時不免發生沖撞。這就常常讓正在強勁發展勢頭上的民樂不免出現尷尬、無奈的場面。也不免讓所有希望民樂事業興旺的朋友略略傷感。此種情形下,我倒是覺得我們的民樂人應該多想想我們許多民樂前輩如鄭覲文、劉天華、彭修文等所走過的艱辛道路,想想本文重點解讀的樸東生這位“老民樂人”或“民樂老人”以及他主持“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以來強化“大民樂結構”的種種舉措……。讀他的書,想他不易的人生,回顧六十年來民族器樂發生的巨大變化,我有一個最大的感悟,就是“民樂”在他和我們尊敬的許多前輩們心中的分量,以及在他們人生旅途上的分量,從來都很重很重。這里不妨用“神圣”和“崇高”四個字概括。我想,什么時候全體民樂人都把“民樂”視為“神圣”、視為“崇高”,都為當前民樂來之不易的大格局而欣慰,那么,曾經長期存在于本領域的那些舊習慣、舊思維、舊觀念,也許會漸漸消退。代之而豎起的,則是那具有符合現代人文精神并可以不斷推進民族器樂藝術的“大民樂觀”。
本人堅信,從民樂的大局出發,樹立“大民樂觀”的新思維、新作風,將是中國“民樂”邁入它更加成熟的新時代的重要動力!
①“民樂”一詞,乃20世紀上半葉廣泛使用的“國樂”的沿用,也是不同時代背景下針對同一對象發生的稱謂變異。在實際使用過程中,有廣、狹二義:狹義指民族樂器及其演奏的音樂而言。廣義指“民族音樂”,如“民樂界”,可以指民族器樂界,也可以指民族音樂界。又如“民樂事業”,亦同。本文中的“民樂”,多為狹義。
②樸東生《民樂?人生》封面題記(紀念專版2009,北京)。
③所列諸作,都是作者在兒童劇院、中央歌舞團期間完成的,寫作時間約在1952—1956年。
④該著前后出過六種版本:《樂隊指揮法》,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年;《樂隊指揮法》,人民音樂出版社,修訂版,1997;《指揮入門》,中國文聯出版社,1998;《民樂指揮概論》,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5;《合奏與指揮》,上海音樂出版社、人民音樂出版社,2007;《指揮藝術概論》,上海音樂出版社 2009年版。
⑤引自樸東生:《民樂﹒人生》“第二篇﹒苦澀的中年”第40頁(紀念專版,2009)。
⑥樸東生《民樂?人生》,第53頁。
⑦1989—1993年為中國錄音錄像出版總社副社長,主持工作;1993—1996年為社長。
喬建中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上海音樂學院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 于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