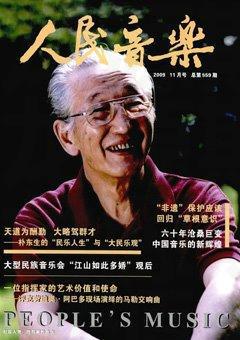20世紀(jì)西方音樂(lè)的輕松解讀
陳 輝
一年前,田藝苗博士贈(zèng)我一本她的新著《時(shí)間與靜默的歌——20世紀(jì)西方作曲家的孤獨(dú)吟唱》。在2002年至2005年間,她一邊在上海音樂(lè)學(xué)院作曲系攻讀作曲技術(shù)理論博士學(xué)位,一邊為《音樂(lè)愛(ài)好者》雜志撰寫(xiě)關(guān)于20世紀(jì)西方音樂(lè)與電影音樂(lè)的專(zhuān)題文章,這本《時(shí)間與靜默的歌——20世紀(jì)西方作曲家的孤獨(dú)吟唱》(上海音樂(lè)學(xué)院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就是這一類(lèi)文章的專(zhuān)集。這已是她寫(xiě)于求學(xué)期間的第二本專(zhuān)著了。此前,上海文匯出版社于2006年7月出版了她的《流影留聲——全球電影音樂(lè)經(jīng)典鑒賞》。近幾年,她還在《音樂(lè)研究》、《人民音樂(lè)》、《音樂(lè)藝術(shù)》等核心刊物,及“2003香港·華人作曲家藝術(shù)節(jié)”、“2008世界女音樂(lè)家大會(huì)”等國(guó)際會(huì)議上陸續(xù)發(fā)表了不少論文和作品。年輕的她在教學(xué)、科研、創(chuàng)作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績(jī)。
《時(shí)間與靜默的歌——20世紀(jì)西方作曲家的孤獨(dú)吟唱》是以作曲家為主線(xiàn),采用隨筆的形式對(duì)20世紀(jì)西方現(xiàn)代音樂(lè)進(jìn)行全面的解讀。田藝苗以學(xué)者的理性,樂(lè)人的熱情,文人的優(yōu)雅,女人的敏感,教師的勤勉與細(xì)致,鞭辟入里地向讀者娓娓解說(shuō)她對(duì)20世紀(jì)西方音樂(lè)的獨(dú)特理解。德彪西、拉威爾、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勛伯格、欣德米特、施尼特凱、布列茲、里蓋蒂、約翰·凱奇、喬治·克拉姆、梅西安、潘德列茨基……幾乎所有的20世紀(jì)西方現(xiàn)代音樂(lè)代表人物都在她的筆下重現(xiàn)。但這不是音樂(lè)家人物傳記,也不是系統(tǒng)的音樂(lè)學(xué)教科書(shū),更不是高深莫測(cè)的現(xiàn)代音樂(lè)作曲技術(shù)分析。在我看來(lái),它更像是一位愛(ài)樂(lè)人的音樂(lè)隨筆或讀書(shū)人的讀書(shū)筆記。這種輕松的文體是我所喜歡的,它可以讓業(yè)外人士和普通愛(ài)好者減少一些閱讀專(zhuān)業(yè)論文帶來(lái)的技術(shù)障礙。但作者在寫(xiě)作時(shí)又始終不負(fù)樂(lè)人的使命,她似乎在不經(jīng)意間將音樂(lè)家與作品、風(fēng)格流派、創(chuàng)作技法、時(shí)代背景,乃至美學(xué)追求、藝術(shù)趣味、人文素養(yǎng)、心理狀態(tài)、個(gè)性特征等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以散文化的筆觸、漫談式的口吻一一向讀者娓娓道來(lái)。她的筆法輕松隨意,不板著面孔說(shuō)教,不生搬前人的研究成果,不只為音樂(lè)而談音樂(lè)。她更注重多元文化的滲透,與讀者作心靈上的交流,談自己的聆樂(lè)體會(huì)與對(duì)音樂(lè)的感悟。這樣,在她的筆下,西方現(xiàn)代音樂(lè)家那一張張冷峻的面孔就變得感性起來(lái),西方現(xiàn)代音樂(lè)那些艱澀詭秘的音符就變得和藹起來(lái),讀者接受起來(lái)也就輕松愉悅,少一些隔閡。
一般來(lái)說(shuō),作家寫(xiě)的音樂(lè)隨筆往往游離于音樂(lè)之外,門(mén)外談樂(lè),說(shuō)不到點(diǎn)子上。音樂(lè)家寫(xiě)的專(zhuān)業(yè)論文又往往滿(mǎn)口的專(zhuān)業(yè)術(shù)語(yǔ),將音樂(lè)作外科手術(shù)式的解剖分析,讀起來(lái)枯燥乏味。田藝苗的文章恰恰是將兩者中和了,嚼起來(lái)有味道,消化了又有營(yíng)養(yǎng)。《時(shí)間與靜默的歌》一書(shū),是構(gòu)建在豐厚的人文底蘊(yùn)和廣博的音樂(lè)文化基礎(chǔ)上的,尤其是田藝苗的專(zhuān)業(yè)方向促使她對(duì)西方現(xiàn)代作曲技術(shù)理論進(jìn)行深入的研究,她對(duì)20世紀(jì)西方音樂(lè)作品的廣泛涉獵和精心搜集、潛心聆聽(tīng)、孜孜求索,是寫(xiě)作這一系列文章的前提,也使她在這一領(lǐng)域具有得天獨(dú)厚的優(yōu)勢(shì)。她對(duì)20世紀(jì)西方音樂(lè)名作如數(shù)家珍,專(zhuān)業(yè)上的駕輕就熟致使她在寫(xiě)作上顯得游刃有余。
我相信當(dāng)下許多人對(duì)于西方現(xiàn)代音樂(lè)的態(tài)度是:“想說(shuō)愛(ài)你不容易”,無(wú)論是觀念上還是語(yǔ)言上,多多少少還有隔閡。讀了田藝苗的文章或許可以幫助音樂(lè)愛(ài)好者消除一些隔閡,提高一些修養(yǎng)。《時(shí)間與靜默的歌》一書(shū)是由若干短篇組成的隨筆集,語(yǔ)言精練,言簡(jiǎn)意賅,重點(diǎn)突出,主旨鮮明,作者在寫(xiě)作時(shí)抓住了三個(gè)重心,即20世紀(jì)西方作曲家寫(xiě)了什么?怎樣寫(xiě)?為什么這樣寫(xiě)?一般來(lái)說(shuō),第一個(gè)問(wèn)題應(yīng)由音樂(lè)史學(xué)家來(lái)回答,第二個(gè)問(wèn)題應(yīng)由作曲理論家來(lái)回答,第三個(gè)問(wèn)題應(yīng)由音樂(lè)美學(xué)家來(lái)回答。田藝苗在寫(xiě)作《時(shí)間與靜默的歌》一書(shū)中,無(wú)意中扮演了三重角色,這是難能可貴的。當(dāng)然,由于是寫(xiě)給一般音樂(lè)愛(ài)好者閱讀的隨筆,而非長(zhǎng)篇論文,其學(xué)術(shù)深度也就略顯遜色了。
讀田藝苗的文章,在輕松休閑中長(zhǎng)了見(jiàn)識(shí),開(kāi)闊了視野。如《誰(shuí)是古拜杜麗娜》一文中,談到女作曲家時(shí),她分析了音樂(lè)史上為什么鮮見(jiàn)大師級(jí)的女作曲家的原因。在《夜鶯在它自己的國(guó)度》一文中,寫(xiě)布里頓引出了“英國(guó)為什么幾百年間遲遲沒(méi)有出現(xiàn)一個(gè)音樂(lè)大師”的話(huà)題。寫(xiě)巴托克時(shí)談到兩次世界大戰(zhàn)給作曲家?guī)?lái)的心靈創(chuàng)傷。在《砍柴打水都是道》一文中,寫(xiě)約翰·凱奇引出了中國(guó)的道家思想和東方的禪宗。在《接近創(chuàng)造的核心》一文中,評(píng)介勛伯格時(shí)談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xué)說(shuō)……她是把音樂(lè)置于廣博的文化背景上解讀的。因此,我更愿意將田藝苗的文章定位為“音樂(lè)文化散文”。
其實(shí),研究20世紀(jì)西方音樂(lè)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尤其是在這個(gè)浮躁的年代。正如作者在她的后記里寫(xiě)道:“很多現(xiàn)當(dāng)代音樂(lè)作品效果駭人,連最資深的音樂(lè)愛(ài)好者也對(duì)它滿(mǎn)懷質(zhì)疑。可是當(dāng)代音樂(lè)不可或缺。那些100多年前的音樂(lè),即使被這個(gè)世紀(jì)的天才演奏家們完美詮釋,重新塑造,它們所表達(dá)的也是從前的情感,與當(dāng)下的生活經(jīng)驗(yàn)相去甚遠(yuǎn)。……即使前面有巴赫的大海與貝多芬的高峰,20世紀(jì)的作曲家也要挺身前行,尋覓這個(gè)世紀(jì)的音樂(lè)語(yǔ)言與表達(dá)方式。……除了職業(yè)音樂(lè)家,大部分人是以?shī)蕵?lè)的態(tài)度來(lái)聽(tīng)音樂(lè)的,而作曲家們是以學(xué)術(shù)的嚴(yán)謹(jǐn)態(tài)度看待自己的這份音樂(lè)事業(yè)的,聽(tīng)與寫(xiě)矛盾重重,難以調(diào)和……在娛樂(lè)時(shí)代,藝術(shù)家也不肯低下驕傲的頭顱來(lái)娛樂(lè)大眾……即使找不到聽(tīng)眾,這些天賦秉異的人,也要專(zhuān)注一生寫(xiě)作這種晦澀難懂的音符,勇于突破他人的法則,也從不墨守自己的陳規(guī),為它翻山越嶺,一意孤行。只因心里始終有一束信仰的光芒照耀。”
現(xiàn)代派作曲家為什么要?jiǎng)?chuàng)作效果駭人、晦澀難懂的音樂(lè)?或許他們心里始終有一束信仰的光芒照耀。他們的信仰是什么?我想應(yīng)該是不斷創(chuàng)新,超越自我,哪怕把自己當(dāng)成一次實(shí)驗(yàn)。誰(shuí)能通過(guò)音樂(lè)解讀他們的心靈?或許這正是田藝苗寫(xiě)作《時(shí)間與靜默的歌》一書(shū)的初衷。
陳輝 浙江臺(tái)州學(xué)院藝術(shù)學(xué)院教師
(責(zé)任編輯 金兆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