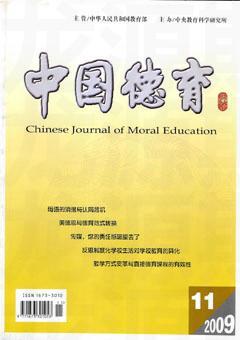反思制度化學校生活對學校教育的異化
杜 潔 屈 陸
一、制度化教育與制度化學校生活
(一)科學教育與工具理性文化催生制度化教育
在人類教育發展史上,十九世紀以前的教育基本上是人文教育或人文教育占主導地位。但在近代工業文明產生以后,在科學技術和大工業生產的沖擊下,科學教育走進學校并成為主導,工具理性文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成為主流文化,高效率、技術化和實用化等日益成為現代社會的追求。作為社會系統重要組成部分的教育也在這片面追求效率、追求秩序化的過程中被結構化為其中的重要一環,有目的、有計劃、有系統、有組織的制度化教育因人才培養的高效特征和對知識傳承的極大促進作用而備受推崇,其目的性、計劃性、系統性和組織性更被認為是教育在人的發展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根本保證。不可否認,教育制度在完成教育的社會職能,促進個體社會化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人類教育進步與發展的每一次飛躍也無不與教育制度的日漸完善和教育效率水平的不斷提高緊密相連,但對單一科學理性和實證理性的過度追求卻使其走向了反面。馬克思?韋伯指出,在理性化的世界中,知識賦予人這樣的信心:只要人們想知道,他在任何時候都能夠知道。從原則上說,再也沒有什么神秘莫測、無法計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們可以通過計算掌握一切,而技術和計算導致理性化,這就意味著世界失去魅力。[1]工具理性主客對立的思維方式使教育被規約在某個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簡單控制的模型里,教育過程中技術主義盛行,教育活動被簡化為“技術性”問題,成為事先籌劃好的、科學或藝術地控制人們心智的技術,成為一種人們必須服從的機制。[2]31一切有利于秩序的技術、制度規范都得到推崇,教育行為最大限度的可計算性、可控制性和預測性成為教育的根本追求。對知識大量、快速的獲取成為教育最直接的目的,而教育過程中價值和意義的創造則被忽視了。這使教育成為被抽去了人文內涵的自我封閉系統,成為傳授科學知識,教授技術與技能,發展人類理性能力的“唯理性教育”,充滿技術與計算的循規蹈矩的“祛魅的世界”取代了豐富多彩而充滿人文氣息的學校生活世界。
(二)制度化教育帶來了學校教育生活的制度化
從近代學校的興起到學校教育系統的形成,制度化教育逐漸成熟,教育活動、教育過程也按標準和規則、規范操作,形成規范的制度體系。隨著制度化教育對教育制度的過度追求,學校教育生活也由“自在”走向“組織規范”,最終走向以“強制”與“約束”為特征的制度化學校生活,過多地強調了制度性、規范性和一致性,過多地強調個體對制度規范的遵從。“各種顯性的規章制度、管理條例、行為規范把學校中的日常生活規定得疏而不漏,各種隱性的倫理規則和約束機制也界定了學校生活的邊界和內容。各種行政命令、儀式、規劃充斥于校園中,促成一派和諧的氣象。”[3]強大而膨脹的制度幾乎塞滿了學校生活的所有空間,制度規范自身的合理性與合道德性則被忽視了。在崇尚科學與實證理性思維的制度化教育的壓力下,學校教育生活已經成為對人進行加工、使其適應于早計劃好的世界的有計劃過程,成為一個以統一的標準、一致的群體活動、制造統一的標準教育成品的可預測、可控制的過程,具有非人性的“精確性、速度、清晰性、持續性……統一性、嚴格的服從、減少摩擦、降低物力和人力消耗等等”特點[4],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成為其最基本的特征,“守時、順從、機械地重復作業”成為其最崇尚的德性[5],表現在從管理方式到師生交往,從教育價值取向到教育生活的基本形態等學校教育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制度化學校生活的具體表現
(一)制度化學校生活表現為效率至上、多層次結構的科層制管理方式
學校組織是具有多層次結構的組織,這種多層次性某種程度上強化了科層化的管理傾向,使作為現代社會管理范式制度的科層制的一些特征明顯地滲入學校生活中。科層制的管理是按權力等級和嚴格的紀律理性建立起來的,這種管理方式以權力的垂直領導和信息的單向傳遞為特征,以效率至上為原則。制度化學校生活傾向于追求這樣一種效率理性(工具理性),從學校權力系統中的等級關系到學校所制定的明確的規章制度,無不顯示出較為鮮明的科層制特征。這種管理方式以高效地“生產”出盡可能多的社會化個體為目的,全力灌輸社會化價值的一套制度和規范體系。這使個體被不同程度地忽視,真實的人讓位于抽象的人,“有著種種欲念與悲喜的活生生的個人逐漸喪失其在制度中的地位,不僅居于邊緣,進而逐漸抽象化、匿名化,抽象的人格凸現出來,具體的、鮮活的、有殊異個性的人格隱匿了”[6]。
(二)制度化學校生活表現為一種集體主義(整體主義)至上的生活
制度化學校生活的價值取向是集體主義或稱整體主義,教師認定集體對個體的發展具有極大的價值,在教育活動中顯示出對集體建設的高度重視:特別強調個人服從于集體、社會和國家,強調一致性和規范化,強調秩序化與整體性,追求一種整體的利益。建立在這種整體主義基礎上的學校生活所維護的是“沒有個體獨立性的、存在于人對人的依賴關系中的整體性,維護體現這種整體主義的社會制度、社會秩序與一切行為規范,它所要反對和抑制的是個人對這種整體主義的反叛與破壞”[7]。在這種制度化的集體(整體)主義至上的生活中,個體“不可避免地產生某種程度的敵意與反叛,……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消除這種敵意的反應。所使用的方法多種多樣,從威脅、懲罰(這是硬的一手)到哄騙、‘耐心說服(這是軟的一手)無所不用”[8] 。在這樣的生活中,作為主體的個人在道德發展中的多種可能性與偶然性被必然性的要求所取代,其結果只能是個體道德主體性的淹沒。在這種狀態下生活的個體所形成的也只能是一種以服從、馴服、恪守為特征的整體主義人格。
(三)制度化學校生活表現為“強價值介入”立場支配下的生活
制度化學校生活是以個體的不成熟為基本價值預設的,學校試圖通過一套嚴密的制度與嚴格的紀律要求來掌握住生活在其中的個體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任何細節都不能逃脫制度的規訓。在制度化的生活中,教育者制訂了各種制度和規則規約個體的行為,以“塑造”心態為受教育者預設了既定的生活方式、價值選擇和發展方向,以一種不容置疑的強令態度要求個體執行,并借助各種強制性懲罰措施矯治個體的失范行為和態度,表現出一種“強價值介入”的立場。在這種生活中,“服從高于自主,聽話高于思想,接受高于創造,一致高于獨立”[2]13,各種制度、規則充斥于其中,“不準”“必須”“嚴禁”以及各種形式的干預與制止、批評與懲罰構成個體的學校生活環境,個體被要求“規規矩矩”地服從管理,控制自己的情緒沖動和自發的情感。個體的“自由”則被限定在制度與規則所“允許”的時空內,而這種“自由”卻被教育者認為是最正確、最有價值、最值得追求的,是培養合格的人所必需的。
三、制度化學校生活合理性的反思
生活是一個復雜的概念,人的生活過程是個體人生價值和人生意義得以發展、完善與實現的過程。人的生活按是否具有“自在性”可以分為日常生活和制度生活。[9]制度生活是指人在特定的制度體系中展開的生活。在制度體系中,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的觀念受到制度和社會給定規范的約束,生活的價值和意義往往是通過與社會制度和規范相符的程度來判斷,具有模式化和穩定性的特點。日常生活則是人的一種自在性生活,以人的習慣為基礎,具有明顯的自生性、習慣性和情感性等基本特征。制度生活和日常生活是人的整體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兩個部分,不可互相替代。對學校教育生活而言,制度生活和日常生活同樣不可或缺,學校教育生活作為完整生活,同時包括“制度生活”和“日常生活”兩大部分,只有兩方面相互協調,才能為個體的道德發展創造和諧的環境。
學校教育的重要職能之一是完成個體的社會化。學校要通過專門的教育活動給生活在其中的個體不斷賦予社會角色意義,使其養成相應的組織意識與規范意識。這使學校教育作為一種制度性規定具有一定的強制性,這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如果讓每個人自由自在而不受任何壓抑或約束地生活,讓每個人充分張揚自我而沒有遵守規范和制度的顧慮,學校教育只會陷入混亂、無序的失控狀態。對個人來說,學校教育生活的開始,也是其生活多樣化、復雜化,受群體生活制度約束的開始。學校教育生活作為個體成長過程中完整生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蘊含著豐富的德育價值,是影響其德性發展極其重要的方面,在個體的成長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在傳統的教育觀念看來,學校教育中的制度生活不僅能夠實現集體的統一性、穩定感和秩序感,而且可以教會個體在集體中有規律地生活,遵守規范并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與意識,與群體生活要求的社會角色保持一致,對于學校教育和個體成長是必要且有積極意義的。
但這種必要性決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無限制地突出學校組織的規范性與強制性,決不意味著學校教育生活是一種制度化的生活。制度化生活過多地強調了規范性、約束性與制度化,某種程度上取消了個人生活的自主性。在制度化學校生活中,制度表現為一種強制性的權力,用福柯的話說,這種權力無所不在,如毛細血管一樣布滿任何角落,是一種小心謹慎、細致入微的管理生命的權力,即權力的“毛細化”。“假如生活是被安排和決定的,或者說個人的生活不是自主的,那么,根本無所謂什么生活目的,……因為一旦生活受制于或者隸屬于某種目的或體系,……那種生活已不是生活,而只是順從強迫約束的生存,已失去生活主體精神價值的內涵,也失去了生活的原則性。”[10]可以說,學校在努力構建井然有序的制度化學校生活的同時,也加強了對人異化的可能。
制度化生活構筑了一個“和諧”與“秩序”的氛圍,掩蓋了學校內部存在著的各種沖突和不確定性。生活中的沖突和不確定性對于個體道德的形成與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是學校德育重要的資源。正是在這種沖突中,個體能夠超越已有道德規范的狹隘與局限,實現對社會、他人和自我的理解、認同與移情體驗,生成主體性的價值判斷標準,促進個體道德的形成與發展。而個體也只有面對道德沖突時,道德選擇才是真實而有意義的。
制度化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指向的是有效的管理。在制度化生活的集體主義價值取向下,教育者顯在或潛在的表現出其對集體在個體發展中極大價值的高度認定,過分強調個體適應集體,過分要求整體性與一致性。這種生活以“目的—工具”合理性為目的,只關注達到目的手段的有效性,忽視其價值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隱含著管理的便利目的。而為達到管理的目的,教育者往往以控制和要求代替溝通和理解,更多考慮的不是個體的需要,而是制度及規則的不容侵犯。被動接受取代了主動探求,服從與依賴取代了真誠的理解和有效的溝通,統一與和諧的背后很可能造成個人真實情感的隱藏與個性的埋沒。這使個體鮮活的個性、能動性和創造性被極大地壓抑和忽視,帶來主體精神成長的缺失。
事實上,“制度”與“制度化”是不同的概念,嚴格意義上的“制度生活”與“制度化生活”也有不同的內涵。“制度”作為人類社會生活的必要條件,由一定標準及相應的規則、規范構成,學校教育必然需要制度,學校教育系統展開的過程也與制度的安排和保障密切相關。而“制度化”則是“為了杜絕失范,只要有可能,總傾向于使制度中所包含的規則、規范更加密集,并使制度配套”[11]的一種傾向。在“化”的過程中,事物性質和狀態發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學校教育生活需要制度的“保障”,也相應地存在著“制度生活”,但學校教育生活作為完整生活,既有“制度生活”的一面,更有“日常生活”的一面。“制度化生活”則以異化的“制度生活”取代“日常生活”成為學校教育生活的全部。學校教育需要制度保障,但不必然走向“制度化教育”。學校教育生活是制度保障下的生活,也不必然就一定走向“制度化生活”。
生活是個人的,每個人自己才是生活的主體,才是生活的真實存在。制度化學校生活將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簡單對立起來,力圖以社會為本位營造生活、對待生活。在這種“模式化”的生活中,一切都被嚴格規定,這使個體缺少對生命自覺的觀念和認識,喪失獨立思考精神培育的可能,來源于生活的道德也演變為單純地規范與約束人的教條和工具。應該看到,制度生活崇尚的是制度和理性,而日常生活則是以道德和情感為人與人之間主導的、直接的調節因素,制度生活不可能也不應替代日常生活成為學校教育生活的全部。而“當前基礎教育的各種弊端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學校教育生活的完全制度化,或曰制度化生活成為教育生活的唯一,即對日常生活的制度化,或者說是學校制度生活向日常生活的延續,制度生活充滿和霸占了日常生活的時空。”[12]相比較而言,制度生活中對人的制度要求應是對人要求的最基本方面,德性涵養更多是在人的真實可感的日常生活中發生的。學校教育中這兩方面相互協調才能為人的道德發展創造和諧的環境。學校教育生活要實現其培養受教育者鮮活個性的教育目標,必須要打破鐵板一塊的制度化學校生活現狀,以道德的制度創建優良的學校生活,以優良的學校生活成就個體道德性的生成。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韋伯.學術與政治[M].馮克利,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29.
[2] 金生鈜.規訓與教化[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
[3] 李廣.學校制度化生活中的德育探析[D].廣州:華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10.
[4] 蘇國勛.理性化及其限制——韋伯思想引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14.
[5] 阿爾溫?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朱志焱,潘琪,張炎,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74.
[6] 劉云杉.學校生活社會學[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49.
[7] 魯潔.關系中的人:當代道德教育的一種人學探尋[J].教育研究,2002,(1):3—9.
[8] 黃頌杰.弗洛姆著作精選——人性?社會?拯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83—84.
[9] 郭元祥.生活與教育[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101—102.
[10] 金生鈜.個人自主性和公民的德性教育[J].教育研究與實驗,2001,(1):8—12.
[11] 陳桂生.教育管理實話[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153.
[12] 郭元祥.生活與教育[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102.
【杜潔,成都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書記、副教授,主要從事學習型組織、教育領導學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屈陸,成都大學經濟政法學院講師,主要從事德育、思想政治教育和高等教育研究。四川成都,610106】
責任編輯/趙?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