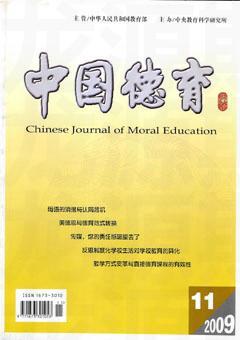也談“無痕德育”
陳桂生
最近剛從張思明老師訪談記錄中,知道“無痕德育”一說,又從《中國德育》雜志2009年第8期刊載的樓江紅君的《讓無痕德育走進課堂》一文中,知道一個“無痕德育”的案例。盡管不知“無痕教育”出自何典,單從不同地區出現同一教育趨向的提法,就感到異常興奮。仿佛從風蕭蕭、霧茫茫中發現了一縷霞光。因為我們在鮮有實效的“德育”中消磨的時間與精力太多,在教育炒作的迷亂中困惑得實在太久了。
何謂“無痕教育”?實施“無痕教育”是否可能?提出這個問題和進行這種嘗試的意義何在?且從樓君介紹的案例談起。
一
據介紹,金華外國語學校的邵紅老師,在講授《思想品德》教科書中《享受學習》課文時,從一個小游戲導入。即先出示兩塊巧克力,請兩個學生進行品嘗巧克力比賽。比賽規則是,誰先把巧克力吃完,老師就把自己手中另外一塊巧克力獎給誰。比賽結束,要兩個參賽者回答巧克力味道如何。接著又請兩個學生進行同樣的比賽。比賽規則改為,誰先嘗出它的真正味道,就把老師手中的巧克力獎給誰。同樣,在比賽結束后,要他們回答巧克力味道如何。由于前后兩次比賽規則不同,學生對巧克力味道的體驗自然不同(如以學生難得吃到的食品代替巧克力,兩種吃法的對比可能更加鮮明)。接著要學生回答,兩組同學對巧克力味道的感受為什么不同?老師又以學生都體會得到的兒時游戲為例,說明游戲主要是享受游戲過程中的樂趣。經過如此鋪墊,這才進入正題:學習不是為了考試,而是為了“享受學習”。盡管就連這篇課文本身,也不過是哄哄學生。因為為考試而學習,又何嘗是出于學生的本意。如此繁重而又復雜的課文,又能給學生多少“享受學習”的機會?只是“享受學習”倒也是學生應當懂得的道理。
樓君的大作,妙在于介紹邵老師的案例之前,先提到一個哲學家上課的故事,作為對“無痕德育”的鋪墊。故事是:一位哲學家,選在雜草叢生的荒地給其弟子上最后一課。他要弟子回答:如何鏟除這些雜草?四個弟子作了不同的回答,或鏟除,或火燒,或撒石灰,或挖根。老師未置可否,只是約弟子一年后仍在此地相聚。一年后,老師未到。弟子發現此地已經成為一片莊稼地。學生由此領悟到,鏟除雜草的根本辦法是種莊稼,進而引申為:要讓靈魂無紛擾,唯一的辦法是讓美德占領靈魂。這個故事類似于我國禪者“論道不滯于跡象”,不依教義教學,唯求以心傳心,訴諸體驗,屬“不傳之傳”。
套用如今習俗說法,這個哲學家上課的故事和邵老師的案例,都堪稱“經典案例”。這兩者的區別,在于后者為“道是無痕實有痕”。虎頭無痕,蛇尾有跡是也。自然,故事出于假設,案例不免受實踐條件限制。故能達到邵老師那樣的水平,也就非常難得了。
二
所謂“無痕教育”,原是狹義“教育”題中應有之義。在我國,早就有另一種說法,叫做“以不教為教”。前一個“教”字,專指說教。后一個“教”字,是指“教育”(狹義)。這種說法,可以遠溯到先秦時期。據莊子稱,和孔子同時代的另一位設學授徒的“圣人”,叫做王駘。他“立不教,坐不議”,而弟子“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邪”。(《莊子?德充符》)意思是,他不言而教,居然使弟子頭腦空空而來,思想充實而去。這或許出于莊子的杜撰。由于這個故事貶抑孔子的意圖非常明顯,故一般只把它當作寓言看待。而這畢竟是兩千多年以前的一種見識。不過,通常認為“以不教為教”是葉圣陶的說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般情況下,狹義“教育”的含義,中西有別。西方著名教育家所謂的“教育”,是指有價值的影響,即善的影響。我國通常把“教育”作為一種影響人的“活動”。兩者之別,猶如耕耘與收獲的不同。前者重在強調沒有收獲的耕耘是無效的勞作,后者重在強調沒有耕作何來收獲。只是這個比喻并不完全恰當。因為耕耘與收獲都有跡可循,而教育影響不見得都立竿見影。然而,是不是“教育”,當以學生是不是受到影響衡量,也才是合情合理的判斷。
為什么要通過無痕跡的活動,即不擺出教育人的姿態,才更能發生有價值的影響呢?這是由于“教育”(狹義)有別于“教學”。教學旨在使學生掌握一定的基礎知識技能。知識、技能之于學生成長的意義,學生或多或少是能夠了解的。因為沒有一個未成年人沒有求知欲。至于簡單灌輸、機械訓練和不堪承載的課業負擔,因無視甚至扼殺學生的求知欲而引起厭學,那是另外一回事。教育涉及對學生價值觀念的影響,學生是否受到某種“教育活動”的影響,既同他們的生活體驗相關,又可能同他們原有的價值傾向發生沖突。如同他們的價值傾向沖突,就可能發生逆反心理的抗阻。學生即使認同“道德教育”中的種種道理,要使懂得的道理見諸行動,又可能同學生原先的行為習慣發生抵觸。即使是成年人往往也不免如此。所以有效的教育活動,應避免灌輸和強制,而成為“無痕教育”。
嚴格說來,“紀律”屬于行為管理的范疇。在行為管理中,強制性、紀律與個人自由的適度平衡是必要的,而超越紀律與管理的“教育”,重在對學生的價值觀念發生影響。
三
以上談到的,還只是“無痕教育”的個案。至于普適性的“無痕教育”的設計,按理,凡是學過教育學的人,都該懂得。因為這是教育原理中核心的價值觀念。連這種核心價值觀念都似懂非懂,還讀什么教育學或教育原理?只是在這里,不適合細讀這種似乎高深的道理,只得簡單地提示一下。
1.在西方理論界,“美德可教嗎”,從蘇格拉底到杜威,一直是爭議不休的問題,一直到現在都是。不過,在近代以前,盡管頗多分歧,而對于美德并非經由傳授客觀知識的教師去教,并無爭議。這就預先排除了說教的必要性,并已成為教育的傳統。其中就包含“無痕教育”意識。
2.隨著近代學校的興起,作為“公共教育機構”的學校,既承擔教學的職責,又承擔教育(狹義)的職責,教師也就相應地承擔這雙重職責。只是并不把它們作為互不相關的兩件事情,而是致力于探究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這便是赫爾巴特提出的“教育性教學”和“通過教學進行教育”的構想。意思是:教師的基本任務就是教學,而教學本身必須具有教育性。那么,教學為什么具有教育性呢?因為通過教學可以培養學生多方面的興趣,使學生系統地掌握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成為有文化教養的人。也就是基于理性判斷力而成為具有獨立個性的人。這種教養,便成為學生德性的基礎。按照這種學說,“教育”仍然是無痕的。
3.在西方社會文化中,教育原先與宗教融于一體。到了近代,隨著崇尚個性與理性成為風尚,宗教本身趨于道德化,進而實行教育與宗教分離,客觀上需要建構與弘揚世俗道德。學校中的“道德課”以及“公民課”遂應運而生。“道德課”意味著從“無痕教育”變成“有痕教育”。不過,它只不過是課程體系中微不足道的補充。即使如此,由于西方素有“無痕教育”的傳統,故“道德課”的有效性,經常受到質疑。其中最為突出的,便是杜威針對“直接的道德教學”,提出“間接的道德教育”新命題。所謂“間接的道德教育”,也就是“無痕教育”。至于“間接的道德教育”的總體構想,它同歐洲大陸“教育性教學”之間的聯系與區別,它本身存在什么問題,也就不必講下去了。
在中國,雖然早有“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一說,早有“不言之教”(《莊子?德充符》)、“以善先人者謂之教”(《荀子?修身》)之類觀念萌生,后來更有禪者“不立文字”“不傳之傳”“教外別傳”之類大量語錄和公案,但并未形成“無痕教育”的傳統。與此相反,到了現代,卻越來越追求“教育”的可見效果和附加在“教育活動”上的外在效果。個中緣由,在這里也無須贅言。
惟其如此,這才對新近發生的所謂“無痕教育”新芽,油然而生喜悅。倒是這種未必植根于教育理論中的新芽,恰恰證明,不管教育的道路何等曲折,只要具有探索精神,尊重事實,講求實效,不為外在誘力所動,即使從教訓中,也能重新回歸教育的常理。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系,上海,200062】
責任編輯/趙?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