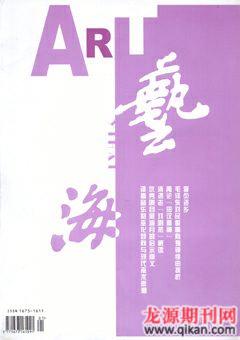清遺老“戲劇熱”解讀
邱 睿
民國初,在清遺老中掀起一股“戲劇熱”。遺老們狂熱地看戲捧伶,并由此創作了大量“捧伶詩”,其中尤以易順鼎為最。
易順鼎,字實甫,亦作碩甫、實父、石甫;又字中實,亦作仲碩。少年時自號眉伽,中年后號哭盦,亦作哭庵、哭廠。湖南龍陽(今漢壽)人。咸豐八年戊午(1858)生,中華民國九年庚申(1920)卒。其人歷咸、同、光、宣,目睹清末黑暗的現實,又經歷民國初混亂動蕩的時局。易順鼎在辛亥之后,有混跡遺老圈自保之時;有側身北上與袁世凱及諸子交游之時;有在袁世凱帝制期間任職之時;而其浪跡梨園,看戲捧伶則始終如一。
評易順鼎詩歌,稱道者多稱其《四魂集》、《廬山詩錄》,貶抑者多訾議其壬子以后作的“捧伶詩”。然而這些“捧伶詩”,可作為易實甫的“詩史”觀,見其辛亥以后的行跡與心史;可作為梨園“詩史”觀,以備清末民初的梨園掌故;可作為民國初社會“詩史”觀,那些唱酬贈答的作品中有一份翔實的遺老名單,記錄下他們在戲園求寄托的群像。然而這些詩卻因為貶抑遺老們頹放的生活方式而長期遭到貶抑,豈非有“因人廢詩”的遺憾?
一稱詩都學杜陵老,豈期全類元遺山
身經亂世,而以如椽巨筆記錄風雨如晦的現實,“以詩為史”,是杜甫以來詩人們的某種自覺與自我期許。清遺老們也認識到時代賦予的某種“文化使命”,便是做一個寫詩史的杜陵老,屢屢在詩歌中流露以這種身份自擬。
但是易順鼎們并沒有像杜甫一樣,在顛沛流離中目擊社會瘡痍,接觸到民眾真實的血淚。而是在京滬的遺老圈中構建自己充滿“黍離之悲”的小天地。因此,他們缺乏“詩史”所有的廣闊視野,看見的只是自己和別的遺老的痛苦;他們很難寫出杜甫《三吏》、《三別》這樣生活化的篇章,只能反復咀嚼杜甫江南逢李龜年般的“天寶遺恨”。
辛亥之后,易順鼎時常往來于京滬,交接兩地遺老圈。“清亡遺臣之隱居者,大抵視夷場為安樂窩,北之京郊,南之淞滬,殊多遺老之跡。”(陳灨一,《睇睇向齋逞意談》,收錄于《晚清民初政壇百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284)所謂的“夷場”是指租界。租界“為那些既不愿以身殉國、也無法逃往國外、又不擁護革命共和的清廷士大夫,提供了另外一種存在的空間:到租界做遺老。”(熊月之,《辛亥鼎革與租界遺老》,發表于《學術月刊》2001年第9期)清遺老聚集在這個圈子里,努力建構自己的文化天地。遺老們通過諸如詩酒唱和、聲色怡情之類的活動“以共同制造一個想象的社群來強化遺民的歸屬感”(王標《空間的想像和經驗——民初上海租界的遜清遺民》,發表于《杭州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
易順鼎的詩中也彌漫著遺老之悲,在其“捧伶詩”中,甚而有一種“悲感結構”。其詩喜在結尾以個人的悲感收束。“還傾桑海千行淚,來寫優云一朵花。”(易順鼎著,王飚點校《琴志樓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本文所引詩文,除特別標注外,均出于此,不另注)“我來看花忽揾淚,天荒地老聊參禪。”“應是公孫傳弟子,杜陵觀罷黯傷神。”每每在饒有興味地評花觀戲之后,卻做杜陵野老吞聲之哭。
在捧伶詩中,易順鼎常常在追述伶人世家時,回顧與伶人的世誼,從而陷入對清末光緒以來梨園盛況的追憶。如寫朱幼芬,講述他是光緒初年名伶霞郎之子;寫梅蘭芳,更是上溯至梅蘭芳之祖梅巧玲,曾有“內廷供奉留芳馨”,“天子親呼胖巧玲”的輝煌。易順鼎的父親易佩綸又曾與梅巧玲之師羅景福交好。易順鼎當時“年甫過二九歲”,“不知當時蘭芳之父墮地業已十幾齡,豈料今日乃與蘭芳論交兩三世”。在一種人世代變的滄桑中再次重味“記殘淚于金臺,錄夢華于東京”;看小叫天譚鑫培的表演,感慨“先帝伶官今亦老,傷心猶唱百年歌。”在一種均將被舞臺邊緣化的隱憂中,咀嚼著落寞。
這也可知,遺老們流連戲園的深層文化動因,不徒是一種自我放縱麻醉,更帶有一種文化的依戀感。舞臺帶給他們的是一種熟悉的文化。這是從他們祖輩父輩就開始的生活方式,徜徉其中,他們可以找到歸屬感。
易順鼎的“奇談怪論”中含有他對“舊文化”的執著態度。所謂“請君勿談開國偉人之勛位,吾恐建設璀璨之新國者,不在彼類在此類。請君勿談先朝遺老之國粹,吾恐保存清淑靈秀之留遺者,不在彼社會在此社會。”“何況并世之佳人,又能化為古來無數之佳人,玉環、飛燕、明妃、洛神,一一可辨為誰某。令我哀窈窕、思賢才,令我發古思,抒舊懷。令我闡潛德之幽光,誅奸諛于既朽。豈徒能見古來之佳人才子、怨女癡男,且復能見古來之孝子忠臣、義夫節婦,且復能見古來之兒女英雄,以及圣君與賢后,何惜嘔出胸中數斗血。”可以說其甘愿嘔心瀝血的正是那些傳統的精神偶像,執著不渝的正是傳統文化價值體系。戲劇舞臺是一個比“租界”更具體更奇妙的文化幻想空間,提供給遺老“精神的避難所”。
清遺老面對一個末世、衰世,以及變世,不滿卻又無奈,他們的結社唱和,有“國家不幸詩家幸”的自我期許,希望以“詩史”之筆記下滿眼滄桑。然而他們狹窄的視野以及固執的文化堅持,讓他們的詩歌充滿了“落花時節”的傷感,卻沒有深廣的現實內容,更多的還是在自己的熟悉的舞臺上尋找文化的舊夢。
二只合花前沉醉死,不宜癡絕學首陽
清遺老有一個最不同于前代遺民之處——辛亥國變,竟無一大臣以身殉。相比起明末可歌可泣的遺民史來說,清末的遺民史似乎太“無聲無色”。
對于“死節”問題,遺老們很敏感,也認識到這是關乎“遺民”身份很重要的一個標識。因而在詩文之中多有辯解。或謂尚懷復辟的希望,不能遽死;或謂效司馬遷悲憤著述,忍辱偷活;或謂牽掛親眷不忍死。然而這些問題并非清遺老才面臨,歷代遺民也有之,為何清代遺民卻能在“不忍”之理由下“不為”?
除卻“自解”的話,“自剖”的話更一針見血。“凡托言有待皆自恕之辭也,且其所云待,待富貴也,富貴不可必得,而一己之身世已淪陷于猥賤而不知。”(林紓《讀儒行》,收錄于《林琴南文集·畏廬三集》,中國書店1985年版P7)錢玄同在《告遺老》一文中,勾勒了遺老的幾種生存狀態:一曰大徹大悟,不做“奴才”,做真正的共和國民;二曰復辟帝制;三曰殉節,盡忠于故主;四曰不問世事,優哉度年。(《錢玄同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P99-104)
易順鼎大概是第四種類型。但似乎也非“優哉”,而是頹放,以近耳順之年縱情聲色。但是他對“死節”似乎也存有一段耿耿于胸中。他的詩中充斥著對死亡的認知與辯解。
易順鼎在鼎革之初也處于一種極度的矛盾之中,時而有殉清的打算,“梅花樹下可活埋,較勝梅村草間活”;時而有善保性命的打算,“誓歸扃門保壽命,與花斷絕始此回”;時過境遷之后,和其他遺民一樣也有未能遽死的追悔,“今日始悲君與我,誤留殘命殉滄桑”。
最值注意的是易順鼎 “捧伶詩”中開始宣稱他“另類”向死之心。“自憐海雪風魔甚,他日還應死抱琴”;“本自無心在人世,不辭將骨化灰塵”;“欲埋第一英雄骨,須在溫柔第一鄉”;“江南雪若深三尺,我使從天乞活埋”;“恨不早從花下死,醵金定葬柳屯田”。
這種“好色不怕死”(樊增祥著,涂小馬、陳宇俊點校,《樊樊山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P1786)的心態在《崇效寺牡丹下戲作短歌》中有詳盡的闡述。“人生不過一生耳,若不行樂真堪哀。人生不過一死耳,若尚畏死真庸才。嗟我拼死拼餓死,餓死并不求人埋。一日未死且行樂,安能四萬八千里求佛,三百六十日持齋。西山餓死太癡絕,何如信陵公子醇酒死,連尹襄老輿尸回。而我生平不解飲,請以彭祖八十一女代彼李白三百杯。……彈琴兮且傍黃連樹,摘牡丹兮且上望鄉臺”(俗諺謂苦中作樂為黃連樹下彈琴,死尚貪色為望鄉臺上摘牡丹)。在看似放曠之下,有一種對死亡方式、意義的糾纏。一方面贊賞餓死首陽的高義,一方面又不贊成這樣癡絕的死法,情愿死于聲色,死于婦人。
這似乎有助于理解遺老“捧伶”行為的意義。看戲捧伶一旦變成家國之痛的變相寄托,變成生死去就間艱難掙扎的一種“活路”,在捧伶上就無怪乎不遺余力而顯出狂態。連被捧的伶人也稱難以承受,有當時的名伶劉喜奎寫書告白(劉成禺、張伯駒著《洪憲紀事詩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P213-216),稱“爭雌雄競勝負之慨,誠恐歐洲今日之血戰,亦無逾于此。”一方面也道出此類文人的心理,“夫志不得遂,才不得展,潦倒平生”,雖然有可憐可哀之處,卻可惜沒有將才情致力于有用的途徑,“風云日惡,國步維艱,使君等果懷愛國大志,濟世高才,則值此存亡攸關、千鈞一發之秋,奔命救死之不遑,寧有余暇為喜奎一弱女子嘔如許心血、耗如許精神,以事此無意識之爭論哉?”清遺老在那個波詭云譎的時代,將身心投入到演戲觀戲之中,正是他們對時事的一種無可奈何的應變。
須知,遺老的看戲捧伶,不純然是追求聲色刺激,還交織著遺老身份的自省和拷問;有在“死節”等問題上的隱然心痛;在聲色之中虛擲光陰和熱情,以“不死為死”生活。所謂的“死倘無名托殉花”,易順鼎們對于“死節”,內心又何嘗不在乎?
三他生未卜此生休,浮名區區更何求
士林重清譽。易代之際,士人往往視名節重于生命。清遺老卻陷入一種尷尬之中。“和前代不同,身處民國,遺老更多了一層處世選擇的艱難,一被視為封建余孽;二有為異族守節之嫌。”(王雷《民國初年生存空間的歧異——前清遺老圈里的生死節義》,發表于《安徽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辛亥后是否仕于民國,袁世凱帝制時期如何反應,張勛復辟期間怎樣應對,遺老們舉步維艱,背后是“名”之負累。
易順鼎所謂戲里人生,“是非任唱蔡中郎”,自稱“折福還因竊薄名”,既然看破名累,那些加諸“遺老”的嘲笑可以等閑視之,那些曾有的功名之心可以等閑視之,故而能從心所欲,為荒誕之事,寫荒誕之詩。
易順鼎捧伶在當時梨園是頗引人注意之事。“乙卯年北京鬧洪憲熱,人物麇集都下,爭尚戲迷。……當時袁氏諸子、要人文客長包兩班(三慶園、廣德樓)頭二排。喜奎、靈芝出臺,實甫必納首懷中,高撐兩掌亂拍,曰:此喝手彩也。” “名士如易哭廠、羅癭公、沈宗畸輩,日奔走喜奎之門,得一顧盼以為榮。哭廠曰:喜奎如顧我尊呼為母,亦所心許。……喜奎登臺,哭廠必納首懷中,大呼曰:我的娘!我的媽!我老早來伺候你了。每日哭廠必與諸名士過喜奎家一二次,入門脫帽,必狂呼:我的親娘,我又來了。”(劉成禺、張伯駒著《洪憲紀事詩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易順鼎在其去處選擇上也無顧攸攸之口。他與袁世凱的兒子袁寒云交往頗密,袁寒云曾薦之為安徽電局局長。袁氏帝制起,易順鼎曾任政事堂印鑄局參事,并因局長外出而兩度代理局長。且任全國選舉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
再看其詩。易順鼎的捧伶詩從內容到形式已經完全脫離傳統的范式,有的竟墮入香奩詩之末流;有的不免過于“振聾發聵”,如《數斗血為諸女伶作》,稱堯舜湯武為偽儒,桀紂幽厲為俊物,亡國需有聲有色,故明亡的名妓,清亡的名伶都是最可敬可愛之人,可謂語出驚人。
然而,易順鼎并非如其宣稱那樣無礙于“名”,他對自己的“詩名”也執著辯護。《數斗血為諸女伶作》出,罵者、唾者有之,易順鼎遂作《讀樊山后數斗血歌后作》,一一反駁。
其詩正反映易順鼎這一時期創作心態。易順鼎一方面稱“他人下筆動作千秋想,我下筆時早視千秋萬歲如埃塵。他人下筆皆欲人贊好,我下筆時早拼人嘲人罵、不畏天變兼人言”;一方面又在詩中斤斤于斧正人言。遺老們內心是敏感的,傳統的君子之名已被時勢剝奪,而向名之心又何至于冷卻到無呢?
“名”之下其實也包含一種外界對自我才能認可的渴求。就像元雜劇的興起有賴“書會才人”于勾欄瓦舍求寄托一樣,讀書人的興趣轉移到戲園,是需要借這個舞臺來寄托自己的才華。許多遺老確實在梨園中享有很高的聲譽。他們不僅參與到劇本的創作,還收藝人為弟子,如步林屋以廣收女弟子著名(鄭逸梅《清末民初文壇逸事》,中華書局2005年版),易順鼎也曾收劉喜奎等為弟子教其詩詞,在伶人那里有一種才華被認同感,“猶剩倡優有人在,黃金不愛愛文章”。
在一個風云詭譎的時代,遺老們已經不是舞臺的主角,而他們卻不甘于默默地淡出人們的視野。既然士人執著追求的“三不朽”已經被現實擊破,對于若即若離的詩名,卻在以反傳統的,以舍為取的方式暗暗執著。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易順鼎“捧伶詩”寫得最多的是梅蘭芳,有《萬古愁曲為歌郎梅蘭芳作》、《梅郎為余置酒馮幼薇宅中賞芍藥留連竟日因賦國花行贈之并索同坐癭公秋岳和》、《梅魂歌》、《觀梅蘭芳演雁門關劇》、《以梅伶蘭芳小影寄樊山石遺媵詩索和》、《送蘭芳偕鳳卿赴春申即為介紹天琴居士》、《樊山寄示餞別梅郎蘭芳詩索和元韻一首》、《蘭芳已至再和前韻示之并寄樊山》、《再贈梅郎一首》、《葬花曲》等,另有無數評語散見于詩中。易順鼎在梅蘭芳嶄露頭角時即為之揄揚,大力推介給“遺老”文化圈中好友,被時人稱為“梅黨”。梅蘭芳感念其知遇之恩,在易順鼎病中“饋珍藥,既歿,致重賻,哭奠極哀。”這也不失為一段梨園佳話。
清遺老生活的時代,是末世,更是變世。他們在生死、去處、文化選擇上面臨著前代遺民所沒有過的問題。他們除了感受到生存的擠壓,還有文化的窘境。戲園是一個可以帶給他們精神庇護的小天地,可以回憶過去,懷戀舊的社會人倫秩序和文化精神。對戲劇狂熱的投入,變態的迷戀更是一種“時代病”。從“捧伶詩”中可揣摩遺老們的心態。高者深者可作長歌當哭,下者鄙者則為靡靡之音。詩心可見世情,誠乎信哉!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
責任編輯:尹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