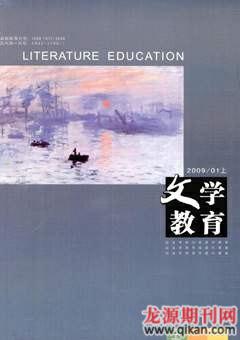評車延高的《把詩寫進光的年輪》
車延高先生曾經將自己的詩作分田園詩、白話詩、愛情詩、朦朧詩、現代詩等八類。這種分法從表面上看起來有一點不合章法,其實這正是表明其詩歌寫作正處于藝術探索的途中。多種多樣的形式與技巧,在其筆下得到了具體而生動的藝術實踐。最近讀到《把詩寫進光的年輪》,我認為這是一組想象豐富、語言美麗,具有歷史感與文化感、具有一定的探索性的佳作。
這組詩有這樣三個特點:
首先,詩人在此組詩中表達了對中國古典詩歌之美的認識,是一部中國古典詩歌史的詩意展示。詩中寫到了李白、杜子美、陸游等詩人,更多的則是以自己的方式與現代的語言呈現了中國古代詩人筆下意境的多種多樣、意象的豐富多彩,讀起來人令人有頭暈目迷之感。開始的時候,似乎并不清楚詩人在寫一些什么,但只要稍微靜下來想一想,就可以發現詩人是在寫自己閱讀中國古典詩歌作品時的那么一種感覺,只不過是一種非常詩意化與表面化的感覺。所以,此組詩中的時間與空間都是一種古今混合的結構,表面上看起來是古代詩人筆下的詩境與詩意,其實是今天的詩人眼中的詩情與詩境。也許我們可以稱之為古今詩人的對話,只不過是當代詩人與古典詩人的對話,附帶與那樣一些詩作及其藝術影像發生關系。從總體上來看,詩人在詩中主要是表達了對于中國古代詩人的崇敬之情,不過也有一些詩人的調侃,有豐富而充實的情趣,是以今人之眼觀古人之詩。那么,歷史感與文化意味就由此而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及其當代詩人的人生體味有機地統一在具體的詩作中,并融合為一種新的藝術意境。從前的中國詩壇也有過這方面的試驗,但寫得如此之復雜、如此之微妙、如此之朦朧,只一人而已。我想,如果要按詩人自己的方式進行歸類的話,這組詩也許可以算作“朦朧詩”。
其次,一種力透紙背的、強大的藝術想象力。中國古典詩歌中的意象與意境,也不是可以隨意組合的;如果隨意組合,并不會產生什么意義,那樣不僅不能說明任何問題,還可能會被認為只是一種文字游戲。車延高以詩人的自我主體為詩作的主軸,以自我的閱讀感覺為線索,將一些古典詩歌中的意象串連起來,并以此表達自己特定的情感與思想。而在這樣一個過程中,高超的藝術想象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其詩中呈現出來的,并不只是唐詩宋詞中固有的意象,而是種種具體、可感、鮮活的意象,有詩人自己的印象與思想于其中,是詩人自我的一種再創造。也許正是如此,才有這樣的生動與豐富的詩句:“長河落日的時候,一切在清醒中睡去 一輪月是香皂,在昨天的河里清洗絕句。”(《詩歌有了一片國土》)“一個腳印坐在自己的腳印里讀書”等等。可以這樣說,其詩作里的一切都是藝術想象的產物,而不是語言物質材料的堆積,更不是一種已有理論的抽象。正是想象讓詩中所有的事物成為意象,并且是種種具有新的特質與意義的意象;詩人自己的感覺與對于古人詩作的印象,都通過這種種意象得到了呈現,歷史感與文化品質才有了著落。
再次,在語言表達上講究虛與實的結合,精致而精美,體現了詩人在語言上的追求。按照柯勒律治的詩學思想,詩的語言絕對不同于生活中的日常口語,因為詩作為一種特殊的文體有自己特定的表達方式。作為與當代朦朧詩比較接近的一種詩體,其語言不僅美妙朦朧,并且典雅華麗,讀來很有興味。如果將詩的語言分為“文”與“白”的話,那此組詩的語言顯然是“文”的。不僅是因為它有古典詩歌相類似的句式與詞語,也因為在語言表達上講究是虛與實的結合,一切空靈與氣象,似乎都從這兩種因素中出來。“他無處可藏,掠長須,兩袖清風迎上去 陌生的目光把夢撞醒 窗外細雨飄飄,剩下背影的大唐遠了 一個孩子的童音背著唐詩:春眠不覺曉”。(《陌生的陽光把夢撞醒》)這樣的詩句如夢似幻,看起來是種種具體的事象,其實有著諸多可以進一步想象的東西。現代詩的語言并不如古詩那樣簡練與凝重,但由于詩人自己的追求,其語言的表達也是夠精致與精美的了。
車延高的詩歌寫作是豐富多彩的,我們很難從一般的意義上來說其詩具有一種什么樣的藝術創造。車延高從2005年開始由雜文創作轉向詩歌寫作,但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里,在一流的文學與詩歌刊物上發表了二百多首詩,有的詩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并且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詩集《日子就是江山》,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是,他也是一個處于前行途中的詩人,更美好的風景還在后頭。
鄒建軍,著名詩評家,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