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中南海(連載)
紅墻內的秘密
我在中南海工作期間,與原來的同事、同學、朋友相見時,他們總希望從我這里打聽一些“報紙上看不到、報告里聽不到”的“內部消息”,希望我能透露一些鮮為人知的資訊。由于當時黨和國家的信息公開化程度比較低,中央的決策程序又比較神秘,加上似真似假的“小道消息”在社會上飛飛揚揚,人們更想知道一些聞所未聞的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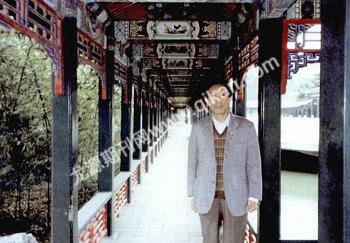
無須否認,置身于被稱為“中國最神秘的地方——中南海”,工作在中央高層核心機關,平時看到、聽到、接觸到的一些事情,帶有一定的機密性。有一段時間,社會上各種“小道消息”和“外轉內”的流言滿天飛。胡耀邦同志曾說,這些東西的發源地往往在北京,在中央機關。為此,中央還專門發文件,嚴肅指出:“現在有少數領導干部無視紀律,隨意向自己的子女、親友談論黨和國家機密……其中不少人又往往在社會上以此炫耀自己,甚至添枝加葉,肆意擴散機密。這種情況,影響極壞,危害很大,必須堅決制止。”組織上對“海”里工作人員的保密要求特別高,提出了許多具體規定,如“不該說的機密絕對不說,不該問的機密絕對不問,不在私人通信中涉及機密”等等。我認識的一位湖南籍同志,他在中辦工作已有20多年,但家里的人只知道他在北京的某個郵局做事,不知道他在中南海工作。因為他每次寄信地址落款只寫“北京市1703信箱”(單位地址的郵政代號)。我在北京的頭幾年也是這樣寫的,直到1982年開始,信封右下方落款處才公開印上紅色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但也不寫具體地址。
保密制度是不可少的,因為這是關系到黨和國家政治、經濟利益和安全的大事。然而,我在中央機關工作多年之后,對“秘密”的含意有了另一種理解和領悟,聯系到文章開頭提及的情況,于1983年5月31日晚上,寫了題為《紅墻內的秘密》:
中南海的四周圍著高大寬厚的紅墻,紅墻邊上的幾座大門都有警衛戰士看守,森嚴而莊重。在許多人看來,這紅墻猶如一把大鎖,鎖住了藏在里面的許多秘密。
有些人總是這樣問我:你在中南海工作,一定知道紅墻內的秘密吧?
什么是紅墻內的秘密呢?我睜大眼睛看,我看見無數的電文、報告、信函在流動,從工作人員的手中流到中央領導同志的案頭,再從中央領導同志的手中流向四面八方……我洗耳恭聽,我聽到總書記和總理的講話,聽到白發蒼蒼的老革命的發言。這講話,這發言,像鏗鏘洪鐘響徹神州上空,像涓涓細流流向干旱的土地……
紅墻內的秘密在哪里?我尋覓,我傾聽,我發覺這紅墻內真正的秘密卻在紅墻外。
秘密在田野里。那飽綻的金穗,那閃亮的銀棉,那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捧出累累碩果的黃土地告訴你“秘密”是什么!那姑娘的笑靨、小伙的喜眉,那原本酸棗般干癟如今變得紅潤而泛起油光的老臉,那從前作為資本主義典型批判、如今作為勞動致富的模范,都在告訴你“秘密”是什么!
請看,靈寶縣陽店公社廟頭大隊原來的貧困戶王二科,全家8口人,這年僅小麥就收了14500斤,為慶豐收,他殺了一頭200多斤的肥豬,請全村145戶人家(每戶1人)吃了一頓飯;請看,運城縣小張塢大隊社員王安順,過去是全村有名的欠款欠糧戶。去年實行了“大包干”,他一年就大翻身,不但還清了欠債,還第一次有了1200多元的存折,家里有余糧,光棉籽油就存了260斤。黨的十二大開幕那天,他禁不住內心的激動,在巷里噼噼啪啪放鞭炮。他們都在用內心的喜悅和激動,詮釋著紅墻內的秘密。

還有,那實行利改稅后重新獲得內在動力的工廠廠長,那商品琳瑯滿目的集貿市場,那山村百姓貼在木門上的大紅對聯——三中全會搭起幸福橋,辛勤勞動走上致富路,都在訴說著紅墻內的秘密。
紅墻內的秘密藏在億萬人民的心坎里;紅墻內的秘密公開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這似乎是寫給向我打聽“秘密”的朋友看的。然而文章寫成后,既沒有寄給朋友,更沒有投寄報刊。在時隔25年后的今天讀來,覺得別有意味。對一個“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的黨和政府來說,它的一切活動、謀劃,作出的每一個決策、決議、決定、指示,制定的每一項方針、政策、措施,歸根結底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百姓的福祉。所以,最終都要落實到基層,落實到民間。這就是紅墻內的秘密的真諦。
讀葉劍英詩《會場素描》
一天晚上,我在辦公室正在翻看《唐詩三百首》。張長行同志拿著一本新出版的《葉劍英詩詞選集》來看我。他說:你喜歡詩歌,這里有一首葉帥寫的詩叫《會場素描》,請你看看是什么意思?接著,他打開《詩詞集》讀了一遍:
一匹復一匹,過橋真費力。感謝牽騾人,驅馱赴前敵。
詩前注明寫作的時間是:1973年7月27日。這是一首五言絕句,文字簡潔,明白如話,但它的蘊意很讓人費解。長行同志走后,我又一連讀了幾遍,反復思忖猜度,還是難得其解。
第二天晚上,長行同志又來我辦公室,我們自然又聊起葉帥的那首詩。老張長期在中央機關工作,知道的情況多,我就向他請教。他向我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1973年7月27日,由周恩來同志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專案”工作,根據中央組織部提出的“解放”干部名單,一個個甄別通過。葉劍英同志的《會場素描》,就是根據這次會議的情況寫成的。他頓了一下又說,據說該詩是葉帥在開會現場順手寫在一張紙上的。這首詩后來被毛澤東同志看到,表示贊賞,并批給當時的中央領導成員傳閱。
聽了這些介紹,我聯系那段歷史時期政治斗爭的形勢,再細細琢磨詩中的含意,茅塞頓開,恍然大悟。不禁為這首詩巧妙的創作構思和獨特的藝術手法拍案叫絕,并為葉劍英同志的浩然正氣和高尚品質所感動。之后,我用兩個晚上的時間寫了《一把鋒利的匕首——讀葉劍英同志詩〈會場素描〉》,主要內容摘錄如下:(為保持原貌,文字未作任何改動)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出于篡黨奪權的野心,妄圖把一大批革命老干部“打倒”。他們捏造了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扣上所謂“叛徒”、“特務”、“反革命”、“假黨員”、“走資派”、“修正主義”等帽子,并設立了許多專案組,對這些革命老同志進行“審查”。對此,葉劍英同志在贈陳毅同志的一首詞中,曾經深有感慨地寫道:“串連炮打何時了,官罷知多少。”到1973年,雖然在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同志的指導下,陸續“解放”了一些老干部,但是還有一批革命老干部或被投入監獄,或被關進“牛棚”,尚未得到“解放”。當時的黨中央曾多次開會,對這些革命老干部的所謂“專案”問題,翻來復去地逐個進行討論研究。“四人幫”心中十分清楚,這些老同志的“解放”,對他們將意味著什么?所以在會議中間,總是設置種種障礙,節外生枝,千方百計不讓通過。葉劍英同志對此非常氣憤,揮筆寫下了《會場素描》這首詩。它像一把鋒利的匕首,對“四人幫”的這種無恥陰謀和險惡用心作了一針見血的揭露。
根據我們的理解,詩中“一匹復一匹”的“騾”,是指因林彪、“四人幫”誣陷而被列入“中央專案組”審查的一批革命老干部。這是一個十分巧妙而貼切的比喻。大家知道,騾子在我國漫長的革命戰爭年代里,曾作出過重要貢獻。它為革命運糧草,送彈藥,馱傷員,跋涉于崎嶇小道、荒原曠野,立下了不可磨滅的汗馬功勞。這正象征著我們一大批在艱難而又殘酷的革命戰爭中,金戈鐵馬,南征北戰,屢經血與火的洗禮,為人民的事業立下了不朽功勛的老同志。“過橋真費力”一句,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四人幫”一伙在逐個討論“專案”時,從中作梗阻撓的卑劣行徑。“感謝牽騾人,驅馱赴前敵”兩句,不僅表達了對“四人幫”一伙的強烈譴責與不滿,而且呼吁要迅速“解放”這些老干部,讓他們盡快重上戰斗崗位,為黨和人民繼續貢獻力量。
我們認為,《會場素描》這首詩是葉劍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歷史條件下,打擊敵人、保護同志的一種特殊方式,是與“四人幫”反革命陰謀活動進行斗爭的一種特殊手段。《會場素描》雖是一首即興之作,但是它蘊含著嚴肅的主題。盡管它是一首匠心獨具、富有藝術魅力的佳作,我們絕對不能只從藝術的角度去欣賞它、理解它,而要看到詩中所反映的重要的政治內容和作者所持的鮮明的政治態度。一滴水可以見太陽。從這首只有短短四句的詩中可以看出,葉劍英同志不僅是一位詩歌藝術造詣很深的詩人,更是一位鐵骨錚錚的共產黨員,一位有膽有識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文章寫好后,我給張長行同志看,他說寫得不錯,并在文字上作了一些推敲、斟酌。應該說,我們這樣的解讀是八九不離十了,但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怕理解有誤造成不良影響,老張又將稿子送葉帥的政治秘書王守江同志審核。第二天我們就收到他的回信:“此件我拜讀了幾遍,感到寫得很好,提不出什么意見。”于是,我們便放心地將稿子投寄出去,文章署名為楊明、昌興(張長行筆名),不久(1982年9月1日)刊登于《解放軍報》。
這是我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寫的詩評文章。
我為地方向中央遞信
當越來越多的人知道我在中南海工作后,通過我向中央領導傳遞信件的事也漸漸多起來。
第一個叫我傳信的是《文匯報》副刊部主任徐開壘同志。我和開壘同志在南匯時就認識了,我去北京前曾到報社看過他。有一天,他和副刊編輯周月泉來中南海找我。我們在西大門的警衛接待室里交談,他先送我一本新出版的一本散文集,隨后又拿出一封信,說:今年是《文匯報》創刊40周年,報社領導想請葉劍英元帥題個詞,以表祝賀。他要我將此信轉交葉帥辦公室。我來北京不久,不知道怎么轉交法,感到有點為難,但還是把信收下了,并表示一定努力辦好。
事后,我找同事許克有幫助,他說小事一樁。接著他就給葉帥秘書打電話,告知此事。隨又將信交到秘書局收發處,由收發處送葉帥秘書收。應該說事情辦得很順利。誰知,過了個把月,徐開壘同志從上海打來電話說,葉帥那里一直沒回音,而報紙周年紀念已臨近,所以十分著急。他還說,如果葉帥不題詞,那么能提供葉帥的一兩首詩發表也可以。我又將此情況告訴許克有。小許經電話聯系得知,近期葉帥正巧出差外地,不久就回來。葉帥回京后,秘書將此作“急件”報告。由于時間緊迫,葉帥來不及題詞,就送去了兩首現成的律詩,供刊發。
再有一次是,給上海市副市長兼市農委主任陳宗烈同志帶信。

1981年8月,我趁去南方出差的機會,回家小住幾天。縣里的同志來看我時說,最近市里召開縣委書記會議,對中央關于“以油換糧”政策的改變,反映十分強烈。明明是農民擁護的政策,實行不久就要“收”了,像草尖上的露珠——好景不長。大家都表示十分不滿。
那是計劃經濟時代,一個縣一個鄉種多少糧食、多少油萊都是國家規定死的。為了減少油料進口,國家糧食部采用“以油換糧”(收購一斤油菜籽國家給六斤糧)的辦法,并說這一政策幾年不變。對此,上海郊區的干部、社員都很贊同,積極擴種油菜。這一年上海郊區擴種油菜95.6萬畝,增收油萊籽80多萬擔,農民收入也有所增加,是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想不到,不久前接糧食部通知:明年不再實行“以油換糧”的政策了。此事在縣委書記會上引起嘩然,意見紛紛:上頭說話不算數,朝三暮四,怎么取信于民?!
陳宗烈同志知道我回家的消息,就專門為此事寫信給時任總書記和總理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同志,托我轉呈。回北京后,我立即將信交給了時任耀邦同志秘書的鄭必堅同志(鄭系我研究室同事,理論組副組長),同時整理了一份情況摘報《群眾擁護的政策不要輕易變》,供中央領導參閱。不幾天,在食堂吃飯時碰上鄭必堅同志,他對我說:耀邦同志很重視上海反映的情況,并作了批示,原信已轉給主管農村經濟工作的李先念同志了。最后中央作如何處理,我不便多打聽,而是聽縣里的同志反饋說:那封信起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我還為上海警備區駐周浦部隊,向中央軍委辦公廳送過信。有年春節回家探親,縣委領導陪同周浦部隊的同志捎來一封信,要我轉送中央軍委辦公廳。我說,我們跟部隊系統無工作關系,送信不方便。縣委領導說,想想辦法吧。于是我收下了。回機關后,得知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王瑞林的女兒在我們研究室工作。我就去找她,用商量的口氣說:你可以不可以幫我帶封信給你父親?該女青年是位剛批準入黨的新黨員,誠實又純樸。那時,我是研究室機關黨委委員。她誠懇地說:我不知道該不該送,但如果你認為可以由我送的話,我就送去。于是,這件勉為其難的事,總算辦成了。
在黨的十二大召開期間,我還為曾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的倪鴻福同志(當時是崇明縣委書記)向大會轉交過崇明縣的“人民來信”等。
應該說,當時下級向上級反映信息的渠道是暢通的,為什么還要熟人轉送呢?我想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按正常渠道上去,寫信者擔心中間被“卡殼”,送不到“首長”手中,有的還認為直接送達的信領導更重視;二是由熟人帶信基本上是“直達車”,時效快些。這樣說來,我是充當了一個“速遞員”的角色,對當事者而言,也算為他們做了一點好事。(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