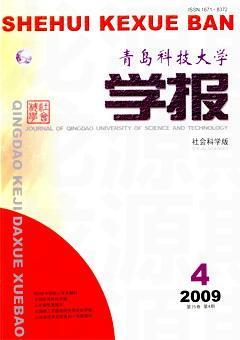試論宋代院畫中的生命意識
殷曉蕾
[摘要]有宋一代,社會功利性生命意識和精神功利性生命意識的并存必然使得院畫呈現出一種雙向糅合的復雜模態,人物畫堅守為政治禮教服務的傳統,社會功利性生命意識依然強勁。而隨著北宋中期日漸強盛的主情寫意審美思潮以及隨之興起的文人畫風影響,山水畫和花鳥畫則日益注重發揮其審美怡情作用,呈現出精神功利性生命意識逐步從社會功利性生命意識母體內部剝離的趨勢。
[關鍵詞]宋代院畫;生命意識;社會功利性;精神功利性
[中圖分類號]T222.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372(2009)04—0081—06
一、引言
生命意識是中國繪畫的靈魂與精髓。中國傳統繪畫藝術正是由生命意識不斷更新演進的邏輯運程構筑起來的形象世界。在宋代以前,由于主要受儒家思想影響,生命意識更多是以社會功利形態顯現出來的。北宋以后,畫家逐漸開始注重對主體精神和內在情懷的抒發,生命意識因之開始了自身的精神功利行程,呈現出由社會功利形態向精神功利形態演進的趨勢,并進而對此期繪畫藝術觀念與繪畫藝術表現產生了相應的制約和影響。
但是由于精神功利性生命意識萌生于社會功利性生命意識母體內部,這就注定了精神功利性生命意識與其不能截然劃開一道鴻溝,兩者必將長期共存,相互對立和消長,并具體體現于此期繪畫藝術創作中。
政治上的極端保守、妥協退讓,思維上的僵化呆滯以及心理上的脆弱感傷和茍安意識,使得宋代的統治階級對藝術的政教功能格外重視。這一傾向,在繪畫活動中集中表現于院畫領域。院畫作為皇家畫院的創作成果,講究法度,強調形似,追求細膩逼真的藝術表現。
因此,從兩宋繪畫的總體狀況看,社會功利性生命意識在院畫中表現得更為明顯突出。而在院畫中,又以人物畫較為突出。至于花鳥畫和山水畫,雖已呈現出某些精神功利性意識的影子,但在社會功利性生命意識的燭照下'多數作品仍然繼續延續寫實再現的傳統。
二、人物畫中的生命意識
按照題材對象的不同,人物畫一般可分為道釋、人物、肖像三類,并且素有為政治禮教服務的傳統。
(一)北宋前期畫院中的人物畫創作
北宋建國后,作為統治階層褒功撻過、潤色宏業工具的道釋畫依然是人物畫創作的主要題材,因此,北宋前期畫院的繪事活動也以道釋題材的宮殿、寺觀壁畫為多。如畫院待詔高益、高文進均是畫院中杰出的人物畫家,俱擅長道釋題材。據文獻記載,高益作畫極為寫實,所畫道釋人物、鬼神感染力極強,如他曾于大相國寺廊壁上畫“阿育王戰像”,宋太宗觀后認為深得用兵之道。高文進于太宗時入圖畫院為祗侯,“工畫佛道,曹吳兼備”,深得皇上恩寵。太宗后期,大相國寺高益所繪壁畫因雨漶水漫,亟需重修,乃命高文進仿效高益舊本重新繪制寺內行廊變相,全都符合上意。此外,高文進還自畫了寺內后門里東西二壁五臺峨眉文殊普賢變相,及后門西壁神、大殿后北方天王等。特別是所繪《擎塔天王》,好像要走出墻壁,栩栩如生。
在北宋前期畫院中,除了高益、高文進外,王靄、趙元長、厲昭慶、勾龍爽、高懷節、李雄、牟谷、王道真、楊斐、趙光輔、高元亨、龍章等俱為擅長道釋題材的高手,足見創作陣容之強大。
除了道釋題材之外,為帝后圖繪肖像的“寫真”在北宋前期也有了長足進步。王靄、牟谷都是這一時期活躍在畫院中的人物寫真高手。王靄工畫佛道人物,長于寫像。曾奉宋太祖命潛往鐘陵圖寫宋齊丘、韓熙載、林仁肇等南唐謀臣肖像,并受到了太祖的嘉獎。又奉詔在定力院畫太祖和太后的御容。由于技巧高超,宋人劉道醇稱“靄之畫也可為至矣”,并將其作列入神品。牟谷亦擅長寫真,太宗時任畫院祗侯,奉命使交趾,遍寫安南王黎桓及臣僚肖像,十余年才回京師,受到了宋真宗的嘉獎慰勞。后又追寫宋太宗正面御容張掛于門外,令真宗“回目悚然”,誤以為真,后因此被授予翰林待詔。流傳于今的《宋太祖趙匡胤像》將太祖的奕奕神采刻畫的至為生動,堪稱北宋前期畫院寫真的力作,也充分說明了此期寫真的技藝水平。
兩宋時期,隨著城市經濟的繁榮,市民文化的興起,人物畫創作突破了以往多局限于宗教題材和貴族生活的藩籬,開始注重描繪和反映市井與鄉村風俗,于是,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的風俗畫創作在北宋前期畫院中開始有所發展,并逐漸成為宋代人物畫創作的一個重心。宋真宗時畫院祗侯高元亨多狀京城市肆車馬,曾畫《從駕兩軍角抵戲場圖》,“寫其觀者四合如堵,坐立翹企,攀扶仰俯,及富貴貧賤、老幼長少、緇黃技術、外夷之人,莫不備具,至有爭怒解挽,千變萬狀,求真盡得,古未有也”。另有《瓊林苑》、《角抵》、《夜市》等圖傳于世。院畫家燕文貴的《七夕夜市圖》描繪北宋都城汴梁潘樓一帶夜市的繁華景象,首開宋人描繪市民風俗畫風氣之先河。
(二)北宋中后期畫院中的人物畫創作
與前期相比,北宋中后期,畫院中的人物畫又有了新的發展趨向,“近世畫手,少作故事人物,頗失古人規鑒之意”。因此,此時院中畫家也不再像前期那樣多以人物畫名世,從事山水、花鳥題材創作的畫家比例明顯增多。根據文獻記載,從仁宗到哲宗朝,畫院中善作人物的畫家只有高克明、陳用志、鐘文秀、郭熙、崔白、馬賁等人。這其中,陳用志為仁宗天圣中(1023—1032)圖畫院祗侯,工畫佛道、人馬、山川、林木,今有《仿尉遲乙僧釋迦出山圖》存于美國波士頓美術館;鐘文秀為神宗朝畫院待詔,“工畫佛道人物。兼學關同山水,亦得其法”。其余畫家的成就則多體現在山水、花鳥畫領域,傳世作品也均屬此列。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以往居于主流的道釋題材在畫院繪事活動中不再占據重要地位,但繪畫的宣傳教化功能并未弱化,為帝后及皇室貴戚、功臣名勛圖寫肖像仍是畫院人物畫家重要繪事。如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于景靈宮建孝嚴殿,奉安仁宗神御。乃鳩集畫手,畫諸屏扆、墻壁。先是三圣神御殿兩廊,圖畫創業戡定之功及朝廷所行大禮,次畫講肄文武之事、游豫宴饗之儀,至是又兼畫應仁宗朝輔臣呂文靖已下至節鉞凡七十二人。時張龍圖(燾)主其事,乃奏請于逐人家取影貌傳寫之,鴛行序列,歷歷可識其面,于是觀者莫不嘆其盛美”。足可想見當時肖像人物畫的創作規模和水平。
北宋后期,畫院人物畫創作可以徽宗朝宣和畫院為代表。由于宋徽宗趙佶對道教的大力倡導,汴京又開始了大規模的宮觀建設,于是,畫院中擅長道釋人物的畫家數量有所增加,出現了能仁甫、郭信、超師、張武翼等名家。而在肖像人物畫上,也不乏寫真高手。如畫院待詔朱漸,宣和間寫六殿御容。由于所畫人物十分傳神,當時遂有“未滿三十歲不可令朱待詔寫真,恐其奪盡精神也”之說。隨著北宋城鄉經濟的進一步繁榮,風俗畫的創作持續高漲,特別是翰林待詔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卷,堪為其中的扛鼎之作,代表了宋代風俗畫的高水平。
(三)南宋畫院中的人物畫創作
如果說,北宋杰出的畫家多在院外,那么,南宋的杰出畫家卻多集院內。宋氏朝廷南渡后,宋高宗趙構醉心于書法,亦雅好繪事,遂繼北宋之余緒,建造紹興畫院。于是,宣和畫院畫家重入紹興畫院,一時名家云集,繪事隆盛。高宗、孝宗、寧宗為南宋畫院鼎盛期,不僅有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四大家,亦有李嵩、蘇漢臣、李安忠、李迪、林椿、閻次平、陳居中等名家積極投身于繪事。這其中,不少畫家都是人物畫的高手,且有作品流傳于世。
南渡之初,由于宋高宗宣揚“中興”,畫院人物畫創作一度高漲,特別是一些借古喻今和針砭現實的歷史故事規鑒畫頗為畫人青睞,如李唐的《采薇圖》、《晉文公復國圖》,肖照的《瑞應圖》,陳居中的《文姬歸漢圖》,劉松年的《中興四將圖》、《十八學士圖》,佚名院畫家的《折檻圖》、《卻坐圖》等作品均屬這一題材類型。與南宋特定的政治環境息息相關,此時的歷史故事畫或弘揚民族氣節,歌頌忠貞愛國的精神,或規勸君主效法圣賢,勇于納諫。
除了歷史故事規鑒畫之外,以君主圣賢為對象的肖像規鑒畫也受到了帝王重視。馬遠有《孔子像》存于北京故宮博物院,其子馬麟則于理宗紹定年間奉帝命創作了《圣賢圖》,共繪制了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十三位歷代圣賢畫像,現存《伏羲》、《堯》、《禹》、《湯》、《武王》五幅,均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此五幅畫像上均有宋理宗親屬贊文,十三個贊文合稱“道統十三贊”,“道統十三贊”前又有理宗自序,亦見于《伏羲》像上方,說明了制作的緣起。大意是理宗在接受了儒學熏陶后,為傳遞“道統”,護衛“道統”而作。宋理宗作成“道統十三贊”后,又命馬麟繪制《圣賢圖》,并將贊文一一題寫畫上,此件繪事的意義在當時必當十分重大而嚴肅。
南宋人物畫創作的另一個高潮則是風俗畫,雖未出現像北宋《清明上河圖》那樣的鴻篇巨制,但風俗畫的題材相當廣泛,涉及到了市民生活的各個方面,舉凡市街、城郭、貨郎、嬰戲、仕女、車馬、耕織以及村學、村牧、運糧、航船等等,皆可入畫。與此同時,南宋風俗畫的藝術成就也達到了相當高度,如蘇漢臣的嬰戲題材和李嵩的貨郎題材作品均以其精湛的藝術技巧受到人們的廣泛歡迎。
考察兩宋時期畫院人物畫發展嬗變的歷程,不難發現,盡管與唐代相比,人物畫已非畫壇的主流,繪畫題材也有所調整變化,但其傳統的政教功能并未弱化,其所內蘊的社會功利意識也因之明顯增強。
三、花鳥畫中的生命意識
花鳥畫在兩宋畫院中的創作最為興盛,而院體花鳥亦被視為工筆花鳥畫的黃金時代。
(一)北宋前中期畫院中的花鳥畫創作
北宋初期,來自西蜀畫院的黃居寀(黃筌之子)進入畫院,他繼承家學,所作花鳥,造型嚴謹,筆法工整,設色富麗,形象準確,于是,“黃氏體制”成為皇家畫院的品評標準,左右和影響了畫院中花鳥畫家的審美取向。黃惟亮、夏侯延祜均承“黃氏體制”,特別是夏侯延祜,是北宋前期畫壇頗具影響的院畫家。陶裔在真宗朝為圖畫院祗侯,工畫花竹翎毛,筆法及形制設色,近于黃筌,時有“后蜀黃筌,東京陶裔”之論。另有李符、李懷兗、李吉,也都追隨黃氏畫風。由于一味因襲,畫院花鳥畫創作“特取形似”,趨于工俗。
到了宋真宗、仁宗時期,繼黃居寀之后,趙昌成為院中花鳥畫的首席畫家。他畫花注重寫生,設色濃麗,畫作“則不特取其形似,直與花傳神者也”,其形神兼備的作風與黃家花鳥畫風有著相同之處。北宋畫院的花鳥畫創作依然籠罩在“黃氏體制”之下。
(二)北宋中后期畫院中的花鳥畫創作
宋神宗熙寧、元豐年間,崔白、崔愨、吳元瑜等花鳥畫家的出現終于打破了左右畫院近一個世紀的“黃氏體制”,引發了院體花鳥畫的變革。崔白尤長于寫生,“落筆運思即成,不假于繩尺,曲直方圓,皆中法度”。因其畫藝卓絕,師其畫者人數眾多,如崔愨、吳元瑜、崔順之、王定國、王充隱、李永、李漢舉等。其中,崔白之弟崔愨、吳元瑜成就最著。
綜合文獻記載和傳世畫跡追蹤崔白畫風,可明顯看出他對傳統的潛心學習和兼容并蓄。他的花鳥畫既有黃筌一派的墨筆勾勒,在運筆上又較其靈動灑脫;他以善畫敗荷鳧雁得名,所作花鳥,“體制清贍,作用疏通”,富有大自然的生趣,這又和徐熙多狀大自然野生花鳥的“野逸”風格相似。除了吸取徐、黃兩派畫風外,崔白還廣泛吸收了趙昌、易元吉等其他名家之長。
作為畫院中畫家,崔白大膽學習“野逸”風格的徐派花鳥,這也充分說明,盡管畫院畫家與在野文人分屬兩同的繪畫陣營,但在兩宋時期,院畫家與院外畫家始終保持著較為密切的關系,并非決然相對,而是相互影響,相互融會。雖然“黃氏體制”籠罩了宮廷畫院近一個世紀,但在野的文人畫對院畫始終保持著或隱或顯的影響,特別是宋神宗熙寧以后,畫院實行以藝業高低選拔人才的制度,從畫院外吸收了許多優秀畫家進入畫院,崔白就是在神宗時因畫藝出眾被選入畫院。
至于吳元瑜,“師崔白,能變世俗之氣,所謂院體者。而素為院體之人,亦因元瑜革去故態,稍稍放筆墨以出胸臆”。從“體制清贍,作用疏通”到“放筆墨”、“出胸臆”,流露出的都是在野文人所提倡的“墨戲”、傳神寫意等意趣旨向。
這種富有文人意趣的畫風對院畫的影響在北宋后期表現得更為明顯,甚至影響到了皇室成員乃至皇帝的藝術創作。
到了北宋末年,宋徽宗的藝術觀則成了院體畫的標準,這一時期的院體畫也被稱作“宣和體”,主要以花鳥畫為主。宋徽宗強調繪畫要嚴于法度,藝術形象要生動逼真,精密不茍。如畫孔雀升墩,應當畫出“孔雀升高,必先舉左”的特征;描繪月季,則當反映“四時朝暮花蕊葉”的不同。同時,受文人畫風影響,宋徽宗又提倡將詩情融入畫境,在構思上追求含蓄巧妙的表現。工致嚴謹、合乎法度的藝術形象一旦注入了詩意,頓時就有了鮮活的靈魂,有了耐人尋味的韻味。“宣和體”花鳥畫風的新變化,顯然是對傳統的寫實再現畫風的新發展,由于“詩意”內涵的注入,作品的愉悅玩賞功能和針對主體玩味情致的表達都得到了增強。如宋徽宗的《芙蓉錦雞圖》上有題詩云:“秋勁拒霜勝,峨冠錦羽雞。已知全五德,安逸勝鳧鷺”,芙蓉、錦雞具有明顯的道德比附意義;而在《瑞鶴圖》中,宋徽宗又通過題詩歌功頌德、粉飾太平。雖然此兩幅作品首要目的仍是為政教服務,但觀賞者必須借助詩句展開詩性聯想才有深刻的體悟。足見,直至北宋末期,畫院始終堅守直接為政教服務的職責,即便是在發揮審美怡情作用的花鳥畫創作中,盡管已內蘊著精神功利性生命意識,卻也時時閃現著社會功利性生命意識的影子。
現存傳為宋徽宗所作的花鳥畫作品中,既有《瑞鶴圖》、《芙蓉錦雞圖》、《五色鸚鵡圖》等工麗風格作品,也有《柳鴉圖》、《池塘晚秋圖》等水墨“逸品”,這自然也是受宋神宗以來逐漸增強的文人畫家“放逸”畫風的影響。
(三)南宋畫院中的花鳥畫創作
花鳥畫自其真正萌生以來就是為了滿足統治階層和上流社會點綴和美化生活之需,故南渡之后,花鳥畫也成為畫院中的重要畫科,頗受到皇帝的青睞。厲鄂《南宋院畫錄》中輯錄的畫院畫家達九十六人,其中,專畫花鳥,或擅長人物、山水又兼擅花鳥的在半數以上。這其中,杰出的花鳥畫家有李安忠、李迪、林椿、毛益等,他們基本上是由徽宗畫院復入紹興畫院,在畫風上也依舊沿襲北宋院畫工筆寫實、設色艷麗的傳統。但受主情寫意審美思潮影響,南宋院畫家已呈現出多元的創作傾向,有的畫家甚至既能畫工筆,又擅長于寫意。如畫家毛益工畫翎毛、花竹,傳世作品《雞圖》、《蜀葵游貓圖》均為工筆之作,而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收藏《柳燕圖》團扇,則是毛益所作的一幅寫意作品,春燕、柳樹、坡石俱以寫意的筆法畫出,用筆疏放而不失法度,畫面亦不施任何色彩,而是通過墨色的濃淡變化予觀者無盡的遐想。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南宋院體花鳥已是工筆、寫意、重彩、淡色、水墨等多種風格并存,但院畫家在創作中還多以工筆為主,這顯然與院畫家對院畫傳統的留戀與繼承息息相關,而在作襯景時卻多以較為疏放的筆意出之,這自然又是注重主體情意的審美思潮誘使他們對其所能作出的某種程度的回應。越至后期,院體花鳥愈發追求閑情逸致的抒發與描繪,構圖簡省,設色更為清淡雅潤,如馬麟的《蘭花圖》冊頁(美國大都會美術館藏),圖中只畫一枝蘭花亭亭立于晴空之下,紛披的蘭葉用墨筆出之,蘭花與蘭梗則是勾勒填彩,設色清潤,巧妙地契合了幽蘭清遠高潔的品格。
綜觀兩宋畫院花鳥畫創作的發展歷程,隨著北宋中期以后注重主體情意的審美思潮骎骎日進,到南宋,花鳥畫的審美怡情作用已將潛存其身的社會功利性生命意識消散殆盡,取而代之的則是精神功利性生命意識。
四、山水畫中的生命意識
五代至兩宋時期是中國水墨山水畫高度發展的時期,風格紛呈,畫家眾多。但是和人物畫、花鳥畫相比,北宋前期畫院中的山水畫創作卻相對滯后。
(一)北宋畫院山水畫創作
北宋前期畫院中,擅長山水畫的畫家主要有黃居窠,“寫怪石山景,往往過其父遠甚”,這顯然與純粹意義上的山水畫有著本質的區別。如前所云,北宋前期畫院的繪事活動以宗教人物壁畫為多,山水只是其中的點綴,多出于實用的裝飾目的。
北宋真宗、仁宗朝以后,畫院中山水畫家逐漸增多,出現了燕文貴、高克明、陳用志、屈鼎、梁忠信等山水名家。燕文貴,工畫山水,自成一家,集山水與界畫于一體,人稱“燕家景致”。據其存世的《溪山樓觀圖》、《江山樓觀圖》等作品分析,所作山水布景巧密,運思精研。高克明善于追憶默寫游歷山川的感受,“鋪陳物象,自成一家,當代少有”,傳為其作的《溪山雪意圖》(美國大都會美術館藏)布景巧密,境界清冷。陳用志工畫道釋、人馬、山川林木,尤工山水,“雖詳悉精微,但疏放全少,而拘制頗嚴。故求之于規矩之外,無飄逸處也,大抵所學不能恢廓耳。”屈鼎山水學燕文貴,當屬“燕家景致”一系,梁忠信風格近于高克明,“而筆墨差嫩,又寺宇過盛,棧道兼繁”。這些畫家的創作足以說明當時院中山水仍拘于“工于形似”的體貌,強調工致巧密的形象刻畫,“殊乏飄逸之妙”,缺乏畫家個性自然流露。
宋神宗繼位后,郭熙進入翰林圖畫院,以其卓絕的畫藝贏得神宗喜愛,進而迅速扭轉了前中期院中山水畫創作相對滯后的局面。據郭熙《林泉高致·畫記》所載,自郭熙進入畫院后,僅神宗朝所從事規模較大的繪事活動多達二十四起,“其后零細大小悉數不及”。郭熙“初以巧贍致工,既久,又益精深,稍稍取李成之法,布置愈造妙處,然后多所自得”,“雖復學慕營丘,亦能自放胸臆。”總之,郭熙的山水畫能在融會前人成功經驗的基礎上自成一家,能真實而微妙地表現不同地區、氣節、氣候的特點,畫出“遠近淺深、四時朝暮、風雨明晦之不同”,創造出優美動人的意境。除創作實踐外,郭熙在山水畫理論上的貢獻尤其重要。在《林泉高致》開篇《山水訓》中,他明確提出了山水畫的審美價值,認為山水畫應表現出“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特性,才能滿足君子“渴慕林泉”的需要。郭熙的藝術探求和理論總結都傳遞出此時院中山水畫創作開始向欣賞和審美需求轉化的訊息。
北宋后期,山水畫重“復古”,畫家多學古而不學今,舍今之水墨而求古之大青綠。于是,青綠山水隨宮廷畫院的繁榮,又顯現出復興的態勢。宋徽宗的宣和畫院中就聚集了眾多畫藝精湛的青綠山水畫家。尤其是畫院學生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堪稱北宋宮廷畫院青綠山水的巔峰。畫卷青綠重彩,章法嚴密,布局宏遠,用筆纖細,千里江山,盡收眼底。當然,這股“復古”畫風并非是唐代青綠山水的簡單復歸,而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對傳統的新發展。總體上看,這時的創作既繼承了李思訓父子青綠山水的傳統,又糅合了北宋文人畫家水墨山水的一些趣味和畫法,既“精工之極,又有士氣”,創造了,一種介于院體和文人畫之間的青綠山水畫。傳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江山秋色圖》,雖系青綠山水,但更顯秀雅,無刻畫之習,舊題為趙伯駒,實出自北宋畫院高手之筆。再如戰德淳,“因試《蝴蝶夢中家萬里》題,畫《蘇武牧羊假寐》,以見萬里意,遂魁。能著色山,人物甚小,青衫白褲,烏巾黃履,不遺毫發。又作紅花綠柳,清江碧岫,一扇之間,動有十里光景,真可愛也。”。可見,北宋文人畫所標榜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創作思想,不僅影響了院中花鳥畫創作,同樣也影響到了山水畫。
除了青綠山水創作外,宣和畫院的水墨山水創作也有了新的發展,受北宋中期興起的士人畫風影響,此時院中水墨山水也偶有放逸之作。如舊題為宋徽宗所作的《雪江歸棹圖》卷,圖繪寒江兩岸的雪景,用筆細勁草草若不經意而又合于法度,氣息近于王維《雪溪圖》。
但是,作為替皇室服務的宮廷畫院,直至北宋后期,山水畫創作延續的依然是偏于寫實再現的傳統,如現藏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的《送郝玄明使秦圖》,是畫院待詔胡舜臣于宣和四年(1122)所作,畫卷鋪排巧密,謹于法度。據載,當時畫家多重視學習畫院前代的山水名家,如何淵“專師克明,往往逼真”;高洵“工山水,師高克明”,后“以畫院多學克明”,晚年復師范寬。即便是向院外畫家學習,仍是謹密有法,“無豪放之氣”,如和成忠“學李成,筆墨溫潤。病在煙云太多爾”;畫院學生劉堅“頗柔媚,師范寬,樓閣人物,種種皆工”。
(二)南宋畫院山水畫創作
南宋建國后,隨彼時審美思潮日益注重發掘個體生命的內在心靈和情緒世界的豐富感受與體驗,院畫家在追求寫實再現的基礎上日益注重抒寫內在的情懷與意趣,追求“詩情畫意”的意境表現。于是,南宋院體山水畫在意境創造、構圖及筆墨運用方面都有了新的發展。具體而言,水墨蒼勁的大斧劈皴、“邊角式”的截景構圖,成為南宋山水特有的
時代風格和審美傾向。最能代表南宋山水畫風格特點的當屬被譽為“南宋四大家”的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
南渡之后,畫院首席當推由徽宗畫院復入紹興畫院的李唐,最能代表其南渡后風格的作品是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長卷《清溪漁隱圖》。此卷構圖已不再是北宋大山大水的“全景式”,而是截取近處的景致著力表現,雖氣勢不足,卻更富于意境。筆墨亦十分洗練簡括,樹干勾勒粗獷坡石用斧劈皴法,水墨并用,元氣淋漓,近處老樹蒼郁,遠景寂靜空蒙。
劉松年擅長青綠山水,代表作品《四景山水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描繪杭州城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景致,并穿插于文人雅士的生活情景,顯示出畫家對畫境意趣的追求。
馬遠、夏珪均師承李唐晚年畫風,風格相近卻又各有千秋,是南宋院體山水畫最典型的代表。馬遠構圖簡潔明快,“全境不多,其小幅或峭峰直上,而不見其頂;或絕壁而下,而不見其腳;或近山參天,而遠山則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獨坐,此邊角之景也”,對局部和邊角作特寫表現。用筆灑脫磊落,剛勁猛烈,氣魄雄強。傳世的《寒江獨釣圖》(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停舟賞梅圖》(美國王己千藏)、《梅石溪鳧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等畫作皆為馬遠的代表作。夏珪“山水布置、皴法與馬遠同,但其意尚蒼古而簡淡,喜用禿筆”,此外,夏珪更注重意境的營造。其晚期作品《山水十二景》長卷(美國納爾遜·艾京斯美術館藏),現僅存“遙山書雁”、“煙村歸渡”、“漁笛清幽”、“煙堤晚泊”四段,或遠山溟漠,或靜水遼闊,或漁人泛舟,或泊船江頭,意境曠遠幽深,欣賞其畫猶如吟詠一首綿綿悠長的詩作,令人回味無窮。與其早期作品相比,此卷技法更為純熟簡練,畫境更趨空靈簡遠,這也典型地體現了南宋末期院體山水畫的創作風格和審美傾向。
從北宋到南宋,畫院中山水畫由全景式的大山大水的整體把握轉向“半邊”、“一角”式山水的簡筆勾勒,由偏于客觀再現到追求主體情思和“詩情畫意”的意境表達,由置景豐富到構圖注重“留白”,清晰地顯示出了精神功利性生命意識日漸突顯的過程。
綜上所述,有宋一代,社會功利性生命意識和精神功利性生命意識的并存必然使得院畫呈現出一種雙向糅合的復雜模態,人物畫堅守為政治禮教服務的傳統,社會功利性生命意識依然強勁。隨著北宋中期日漸強盛的主情寫意審美思潮以及隨之興起的文人“放逸”畫風影響,花鳥畫和山水畫則日益注重發揮其審美怡情作用,呈現出精神功利性生命意識逐步從社會功利性生命意識母體內部剝離的趨勢。
兩宋院畫大膽吸取在野的文人畫風的影響也充分表明,盡管院畫是為皇室宮廷服務,崇尚寫實再現的傳統,講究規矩格法,但它能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充實新的內涵與表現方法,又絕非是一個僵化保守的模式,這對于我們今天的創作仍然有一定的啟發和借鑒作用。
[責任編輯王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