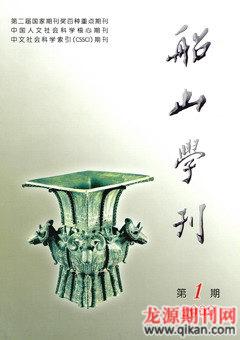《論語》“義”思想芻議
霍國棟
摘要:義常訓(xùn)為宜。宜本義為殺和殺牲而祭之禮,安宜乃引申之義。義字在《論語》中凡24見,時作名詞,時作動詞,時作形容(副)詞;但基本涵義即是合適、合宜,具有道德評價、道德要求、道德標(biāo)準(zhǔn)三重道德職能。從更深層次說,義是由仁循禮的實(shí)踐途徑,內(nèi)圣外王的修養(yǎng)方法,其哲學(xué)境界就是中庸。
關(guān)鍵詞:義宜;由仁循禮;內(nèi)圣外王;中庸
中圖分類號:B222.2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文章編號:1004-7387(2009)01-0115-04
義,作為儒家倫理學(xué)范疇之一,常與仁字并舉為“仁義”。此乃儒家經(jīng)典之德目,亦為歷代儒生自律與育人之恒定坐標(biāo)。嘗有“殺生成仁”“舍生取義”之說。“仁者,愛人”,此解在眾多涉及仁字的場合均可以一以貫之而解,或日克己復(fù)禮,或日忠恕,或日能行五者(恭、寬、信、敏、惠)于天下,或日先難而后獲,但“愛人”之基本涵義仍不失偏頗。然“義”者何義?更兼有“義利之辯”中義字可解釋為公利、整體利益,甚至進(jìn)一步抽象為道德的代名詞,義字的涵義似乎更加撲朔迷離而弗可厘清。本文擬就從《論語》文本著手試探孔子及其弟子門人何以解義。
一、義字的訓(xùn)詁
《論語》一書中,直接論及義的共20章,另外不乏一些章節(jié)間接談及,但無對它明確或直接的釋義。孔子弟子亦無如“問仁”般“問義”。故可以說《論語》編者在使用著義字先前或同時代約定俗成的意思而沒有附加更多或新的發(fā)揮。如此。探尋義的涵義先需從旁門人手。
《禮記·中庸》曰“義者,宜也。”以宜釋義,久已公認(rèn)。《說文》曰“宜,所安也。從‘之下,一之上。一,猶地也。此言會意。”故義通過宜而釋為所安,通俗地說就是“合適、合宜”。《說文》段注:“義之本訓(xùn)謂禮容各得其宜。禮容得宜則善矣。”朱貽庭先生引《左傳》《國語》等書認(rèn)為“義者宜也”的涵義在春秋時期業(yè)已比較明確,并指出宜與不宜在于是否合符“禮”。“義作為適宜于禮的道德要求,其一般含義就是使自己的行為合符禮制,達(dá)到·義節(jié)則度,它的作用就在于‘所以節(jié)也。”龐樸先生亦贊同義并非孔子的發(fā)明,而是其前早已使用的道德評語。他從訓(xùn)詁學(xué)的角度確證了“義”字在金器銘文中原作“宜”字。但他進(jìn)一步指出,宜字之本義為“殺”和“殺牲而祭之禮”,并非所謂的合適、合宜。“宜,所安也”乃是引申之義。個中緣由容庚先生解之為宜金文像置肉于且上之形,疑與俎為一字,宜俎互訓(xùn),而“俎。肉幾也”,“置肉與幾,有安宜之誼,故引申而為訓(xùn)安之宜。”目龐樸先生解之為由“罪有應(yīng)得”之意引申而出。此論曾為李澤厚、張立文二位所采用。
又《說文》:“義,己之威儀也,從我羊。”段注曰:“義各本作儀,今正。古者威儀字作義。”所以“義的本義是儀,亦為一種儀禮形式。甲骨文的字形是人戴羊冠手執(zhí)戈形武器,這種儀禮具有威儀。”而段注又解:“儀,度也。度,法制也。”陳瑛先生因而認(rèn)定“古代極其重視等級制度,所以這些禮儀和容儀都很講究‘度就是說必須分寸適當(dāng),不得過和不及。因此,后來的義字又作適宜、適度、適當(dāng)解。”但分析義字從我從羊,我本是戈形兵器,或曰古殺字;羊一義為吉祥動物,與苦美同義,二義為人首插羽為飾,以修儀容。可見義字當(dāng)有“殺”與“儀容得體”之合義。而事實(shí)上,義確實(shí)具有這樣的涵義。因?yàn)椋x儀相通,“義的這種含義,可以容納得下‘宜的殺戮的意思,以及合適、美善的意思。而且不帶‘宜字所固有的那種血腥氣味:加上二字同音,便于通假,因而具有了取代‘宜字而為道德規(guī)范的最佳資格。義者,宜也的訓(xùn)詁得以確立。只不過天長日久。隨著“合適、合宜”的訓(xùn)詁日益廣泛使用,義字本原涵有的威嚴(yán)肅殺之義逐漸減退甚至于消亡,只能從“義所以節(jié)也”“義節(jié)則度”等語中找到半點(diǎn)隱約的痕跡。
二、《論語》義字的道德意蘊(yùn)
從語法上分析,義字在《論語》文本中時作名詞,時作動詞,時作形容(副)詞,但基本涵義還是“合適、合宜”。亦有譯成“正義、正當(dāng)”者如李澤厚先生。釋為“應(yīng)當(dāng)、當(dāng)然”者如張岱年先生,但皆不出“合適、合宜”之范疇也。作名詞解,亦有三種不同意思。其一指“合宜”這種標(biāo)準(zhǔn)。如“信近于義,言可復(fù)也”(《學(xué)而》),“義與之比”(《里仁》)。其二為合宜之事。如“見義不為,無勇也”(《為政》)。其三乃義、宜本身,可引申為道義。如“聞義不能徙”(《述而》)“主忠信,徙義,崇德也。”(《顏淵》)不過,義作為名詞解的這三種意思并非嚴(yán)格界別,有些章節(jié)可以有不影響理解的交叉解釋,如“君子義以為上”《陽貨》。作動詞用,義可釋為“適宜”,即符合義(這種標(biāo)準(zhǔn))。如“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述而》);“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憲問》)。作形容(副)詞用,義可釋為“合宜的(地)”。如“其使民也義”(《公冶長》),即子產(chǎn)能夠不違農(nóng)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費(fèi)”(《堯日》)地“使民”,或如朱熹所注:“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
正因?yàn)榱x字在語法上存在著多重詞性,所以就通篇而言,義字在《論語》中就不可避免或?yàn)槟硠討B(tài)之寫照,或?yàn)槟踌o態(tài)之描述。自然,在道德意義上,義就具備了動態(tài)的道德評價、道德要求和靜態(tài)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三重道德職能。這三重道德職能有交融互通的特征,即道德評價中往往包含有道德要求的成分,提出道德要求的同時也就內(nèi)在地蘊(yùn)涵著一定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道德標(biāo)準(zhǔn)的確立不免要以一定的道德評價為前提。這里只作大致的區(qū)分。另外需要說明的是義字這三重含義與其詞性之間并無嚴(yán)格的一一對應(yīng)關(guān)系。
在道德評價中。我們可以看到立身之則如:“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陽貨》)“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衛(wèi)靈公》)為政之策如:“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子路》);“務(wù)民之義,敬鬼神而遠(yuǎn)之,可謂知矣。”(《雍也》)學(xué)習(xí)之方如:“德之不修,學(xué)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主忠信,徙義,崇德也。”(《顏淵》)作為一種道德要求,義通常與利、信、勇、達(dá)、道等相關(guān)而言。義利關(guān)系涉及“義利之辯”這一中國古代倫理學(xué)基本問題。儒學(xué)“義先利后,義利統(tǒng)一”的原則既無疑問。故不贅述。而義與信、勇、達(dá)、道等分見于《學(xué)而》、《為政》和《陽貨》、《顏淵》、《季氏》等篇章,文本意思明了,亦不重述。
作為道德標(biāo)準(zhǔn)。義主要與君子密切相聯(lián)。其實(shí)準(zhǔn)確地說,義既是君子應(yīng)具備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又是對君子的道德要求。縱觀《論語》直接論及君子與義關(guān)系的七章文本,不難厘清他們的邏輯次序。首先,君子(在位者或有德者)有九思,其一就是“見得思義”。(《季氏》)然而子張嘗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士在《論語》中提及15次,或指一般人士,或指讀書人、知識分子。孔子曾言:“富而可求也,雖執(zhí)鞭之士,吾亦為之”(《述而》),又言:“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
足與議也”(《里仁》)。可見,孔子對“士”并不是很看好,也就是說“士”是一個道德修養(yǎng)并不很高的人群。君子與士皆“見得恩義”,也就意味著這時的君子無異于為士了。而且士之“祭思敬,喪思哀”與君子的九思亦頗為相近,這實(shí)可作為旁證。又“見得思義”之“思”字。程石權(quán)先生訓(xùn):“思者念也。念念不忘是為欲之”,猶言義并未在君子心中。須思而后得也。故君子“見得思義”實(shí)不為道德之高境界。然思既來之,則說明“君子喻于義”(《里仁》]在先,或日思而后“君子喻于義”也未嘗不可,關(guān)鍵看喻字怎樣理解。義在君子心中之后,“君子義以為上”,即君子十分看重,尊貴義。不過此時的義在君子心中還是一種外在的道德行為規(guī)范,還是一種道德他律,尚存有敬畏與不敬畏,服膺與不服膺的搖擺空間。直到進(jìn)一步“君子義以為質(zhì),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衛(wèi)靈公》)才說明君子已經(jīng)把義這種外在的道德行為規(guī)范轉(zhuǎn)化成內(nèi)心的天然道德義務(wù),完成了由道德他律向道德自律的質(zhì)變過程,從而心中再無有絲毫不敬畏,不服膺的余地。于是。“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里仁》)由于孔子尚經(jīng)世致用之學(xué),故又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微子》)。他還贊揚(yáng)子產(chǎn):“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yǎng)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公冶長》)
以上這些均是《論語》中直接談及義的。除此之外,《論語》中還有很多雖論其它,卻含有義之道德評價、要求和標(biāo)準(zhǔn)的章節(jié)。其中包括禮、孝、祭、君子、為政、做人甚至詩和樂等等。于禮一如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這里飽含對季氏的批評,就是因?yàn)榧臼腺栽搅硕Y制,做出不合宜的事情來;于孝一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yǎng)。至于犬馬,皆能有養(yǎng)。不敬,何以別乎?”(《為政》)這是說孔子認(rèn)為僅僅能養(yǎng)并不算是孝道,還需要有敬,無敬則無以別乎犬馬。換句話說。唯養(yǎng)與敬之共和方是孝之所宜。再如:“父母在,不遠(yuǎn)游,游必有方。”(《里仁》)于祭一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于君子一如:“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xué)也已。”(《學(xué)而》)也就是說一個君子如果食而求飽,居而求安,多言懶事,遠(yuǎn)道而嬉則是不宜的了。于為政一如:“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于做人一如:“弟子人則孝,出則悌,謹(jǐn)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xué)文。”(《學(xué)而》)于詩一如“子日:‘《關(guān)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言外之意,樂哀皆需有度,否則過猶不及,失之安宜。于樂一如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nèi)缫玻缫玻[如也,以成。”(《八佾》)孔子在這里詳細(xì)介紹了一首美妙樂曲應(yīng)當(dāng)遵循的法則,接著他還有點(diǎn)評:“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樂之所宜,略見一般。
三、《論語》義字的哲學(xué)意蘊(yùn)
分析完義字的語法和道德職能之后,《論語》的義思想已基本明了。但就此止步還不能揭示義在《論語》中的實(shí)際地位。進(jìn)一步探討,則不難發(fā)現(xiàn)義字在《論語》中直接談?wù)摰拇螖?shù)盡管比仁字少得多,卻同樣具有相當(dāng)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具體地說,它是由仁循禮的實(shí)踐途徑,內(nèi)圣外王的修養(yǎng)方法,其哲學(xué)境界就是中庸。首先,義是由仁循禮的實(shí)踐途徑。仁是孔子倫理思想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涵義博厚精深又簡約平實(shí),是孔子的人生理想。孔子不輕易許人以仁,其稱之為仁者不過箕子、比干、微子、伯夷、叔齊、管仲六人;余者連顏淵也只能“其心三月不違仁”(《雍也》),更別說其它人了。不過仁并沒有因其博厚而玄奧神秘,不可捉摸;相反卻因其簡約而平易近人,有章可循。這個章就是禮。所謂“克己復(fù)禮為仁。一日克己復(fù)禮,天下歸仁焉。”(《顏淵》)仁禮的統(tǒng)一就是孔子的社會倫理模式。孔子批判繼承了上古禮制思想,不僅發(fā)揚(yáng)了其維護(hù)社會等級次序、鞏固政權(quán)統(tǒng)治的政治功能,而且損益周禮以正其名。顯其用,使之滲透于個人日常行為規(guī)范,具有道德意義上的修養(yǎng)工夫。孔子教育自己的兒子說“不學(xué)禮。無以立”(《季氏》1。但此時禮不再僅僅表現(xiàn)為一種儀禮形式,而是具有了更本質(zhì)的內(nèi)容,即仁。“禮云禮云,玉帛云哉?”(《陽貨》)“人而不仁,如札何?”(《八佾》)孔子甚至夸獎學(xué)生子夏“禮后乎?”的疑問說:“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所以“仁是禮的心理基礎(chǔ),沒有仁這一發(fā)自內(nèi)心的道德意識,就不能遵守禮制”,“實(shí)行仁德,必自約以禮。”
但禮是靜態(tài)的。如果說靜態(tài)的禮表現(xiàn)著仁的本質(zhì)濺者說禮是形式,仁是內(nèi)容,那么現(xiàn)象表現(xiàn)本質(zhì)的過程就是循禮行事,這恰恰邁入了義的范疇。義的本訓(xùn)就在于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使之合乎禮儀,這于前文已有所論及。所以,義就構(gòu)成了仁與禮之問的中介。換句話說,仁愛之心尚處于“知”的范圍,而禮就是這種“知”外在化的完美形式,形式的完成需要將內(nèi)心的“仁知”實(shí)踐出來,這個過程就是義。仁義的關(guān)系就是一個知行關(guān)系。張立文先生認(rèn)為“仁作為體,也就是心性的本質(zhì),本質(zhì)并非外鑠,感物而有,而是本有:義是仁的知覺發(fā)見的作用,是對仁的體認(rèn)和演變的次序。”對張岱年先生則主張:“在孔子,道與仁。只是一事,亦稱為義。從其為原則謂之道,從其為當(dāng)然謂之義。而道之內(nèi)容便是仁。”“依義而行,實(shí)即是依仁而行。”㈣他們從不同側(cè)面道出了仁與義的關(guān)系,卻都沒有將禮也納入考慮范圍之內(nèi)。實(shí)際上,仁、義、禮三位一體,構(gòu)成了一個由知到行的完整行為過程(包括結(jié)果)。沒有義,則仁無以付諸實(shí)踐,禮將流于形式。所以說,義是由仁循禮的實(shí)踐途徑。
其次。義是內(nèi)圣外王的修養(yǎng)方法。內(nèi)圣外王是儒家學(xué)者一生為之追求的理想目標(biāo)。孔子曾明確指出圣高于仁。子貢問:“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jì)眾,何如?可謂仁乎?”孔子答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雍也》)可見與稍有一定現(xiàn)實(shí)性的仁相比。圣完全是一個可望不可及的道德理想,指引著人們修為的方向。然而修圣之道。無外乎一個學(xué)字。學(xué)既指“依于仁。游于藝”(《述而》)之學(xué),亦有實(shí)踐之意。孔子特別重視學(xué),有六言六蔽之說,即“好仁不好學(xué),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xué),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xué),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xué),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xué),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xué),其蔽也狂。”(《陽貨》]并認(rèn)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叫“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xué)也。”(《公冶長》)在學(xué)的過程中,要多聞多見:“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述而》)要好學(xué)知禮:“三人行,必有我?guī)熝桑簱衿渖普叨鴱闹洳簧普摺!?《述而》)“君子博學(xué)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要實(shí)事求是,知錯能改:“知之為知之,不知為
不知,是知也!”(《為政》)“過則勿憚改。”“(《學(xué)而》)更重要的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孔子說自己“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不正是說自己隨時隨地隨心所欲之所為都能夠不偏不倚,合符義了嗎?
外王,就是推行王道。孔子一生孜孜以求,周游列國,就是為了兜售他的王道思想。只可惜知音甚少,落得幾聲感嘆:“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fù)夢見周公!”(《述而》)“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子罕》)但他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世精神又無疑昭示著一位圣人所具有的崇高歷史責(zé)任感和自信心。“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所以只要有君王召見,甚至于公孫不狃、佛腫召見,他都意欲前往。這種“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的態(tài)度似乎毫無原則可言。實(shí)則“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里仁》),無可無不可之間,“義之與比”。故日,義是內(nèi)圣外王的修養(yǎng)方法。
最后,義的哲學(xué)境界就是中庸。中庸作為一種境界和方法,屬于道德哲學(xué)范疇。這一范疇的提出一般認(rèn)為是孔子的功績。《論語》載:“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雍也》)這是《論語》中唯一一處直接討論中庸的章節(jié)。但這并不妨礙中庸的思想貫穿于《論語》的始終。
中的本義是“射箭中的”之意。經(jīng)力中——知中——堪中——中庸四個發(fā)展階段始有中庸之德。朱熹解:“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此外,庸還有動詞“用”的意思,故中庸也可以解為“用中”。陳科華博士追本溯源,認(rèn)為“中庸一詞的內(nèi)涵綜合了靜態(tài)、空間性的中和動態(tài)、時間性的中兩方面的內(nèi)涵,是中國古代兩種文化——弓箭文化和歷法文化想糅合的結(jié)晶,它的精神實(shí)質(zhì)是如何把普遍的道德原理與具體的倫理實(shí)踐想結(jié)合,達(dá)到一種‘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境界。”
在《論語》的文本中,有兩處常被引用說明孔子的中庸思想。其一,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jìn)取。猬者有所不為也。”(《子路》)其二,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先進(jìn)》)孔子在這里批評了狂、猬、過和不及四種不適當(dāng)?shù)淖龇ā?shí)際上,狂猶如過,狷猶如不及,兩類做法皆非中庸之道,而是背離中道走向了極端,故失之所宜。相應(yīng)地,所宜就在于執(zhí)其兩端而用其中,做到不偏不倚,不上不下,不前不后,不左不右,或謂無過無不及,恰到好處。顯而易見,中庸之動態(tài)的“中”的具體要求在不知不覺中又滑進(jìn)了義的范疇。義者宜也。不正是要求一切都要做的符合時境,無偏無倚。合乎中庸之道嗎?且在儒家,作為標(biāo)準(zhǔn)的‘中的內(nèi)容主要是仁、禮等道德標(biāo)準(zhǔn)。一“中作為行為準(zhǔn)則。其要求是‘惟義所在。也就是以義為中。”鑒于前文所述仁義禮的關(guān)系,不難想象一個“中庸”的行為就是由仁心而發(fā)端,符合義的要求。合乎禮的準(zhǔn)則的行為。不過這個行為并不受拘于禮制而刻古呆板,而是因時因地因人因事因勢制宜。既執(zhí)中又權(quán)變,呈現(xiàn)出亦此亦彼、非此非彼、此是彼非、此非彼是、此彼相制辨證統(tǒng)一的特點(diǎn)。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就包括既溫且厲,既恭旦安。溫厲互補(bǔ),恭安互濟(jì)和威是猛非,以猛戒威兩種思維模式。而“質(zhì)勝文則野,文勝質(zhì)則史。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則體現(xiàn)了質(zhì)文互制互濟(jì)的特點(diǎn)。孔子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泰伯》)是一種亦此亦彼的時。正因?yàn)榭鬃幽軌虬盐铡皶r中”的玄妙,所以面對學(xué)生子路、再有相同的提問,他給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緣由是“求也退,故進(jìn)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進(jìn)》)所以,“‘中作為標(biāo)準(zhǔn)是一個多層次、多維度的系統(tǒng),在實(shí)際的運(yùn)用中,全賴行為主體根據(jù)不同的情況去掌握。如果說有一個總要求,即是《中論》所云的‘維變所適,惟義所在。這一要求也是中庸的核心思想所在。”
綜上所述,義字在《論語》文本中出現(xiàn)的次數(shù)雖然不多。卻具有相當(dāng)深邃的內(nèi)涵。無怪乎后來的墨子、孟子都非常重視義了,不過時過境遷,義字的內(nèi)涵也會發(fā)生變化,此是后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