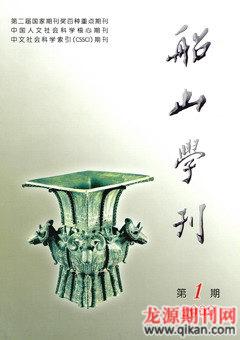“通變”詩學轉向中的崇正傾向
楊 暉
摘要:劉勰創造性地將哲學中的“常變”與《易傳》中的“通變”融合,實現了“通變”的詩學轉向,并賦予其新的內涵。本文揭示了劉勰“通變”思想中的“崇正”傾向。并在其著作中進一步得到驗證。
關鍵詞:劉勰:詩學;通變;崇正
中圖分類號:G11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7387(2009)01-0064-03
“通變”最早見于《周易》,是哲學層面的概念。《系辭傳》日:“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其大意是指事物發展到一定程度,堵而不順,必生變化,變化而順暢,因此,“通變”可以理解為“貫通使之順暢”Ⅲ。劉勰第一次將這一概念引向詩學,成為《文心雕龍》重要的成就之一。那么,劉勰“通變”的內涵是什么呢?在其詩學轉向中是否注入了新的元素?
一、通變的詩學轉向
《序志》云:“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這表達了兩層意思:第一是談《文心》之“本”、“師”、“體”;第二是在“本”、“師”、“體”基礎上論“酌”與“變”。酌,衡量后決定取舍。變,辯也。又辯者。辨也。辯、辨相通。這里的第二層就是劉勰的“通變”思想。這一思想集中體現在《通變》篇中,《正緯》與《離騷》是具體實踐,與《通變》相互印證。《通變》開篇曰:“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認為詩、賦、書、記等都有“體”與“文”兩個方面,前者“有常”,后者“無方”。這一詩學觀念自然見出中國哲學的“常變”痕跡。
中國人很早就確立了“易變”觀念,《系辭》已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即“承認變是宇宙中之一根本事實”,但也不否認“常則”的存在,如《老子》的“知常日明,不知常,妄作兇”,也就是在“變化的不易之則,即所謂的常,常即變中之不變之義。”劉勰接受這一“常變”,并創造性地運用到詩學領域。提出了“文體有常,變數無方”的思想。他說:“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于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于新聲。”(《通變》)認為文體的名稱與寫作原理為不變之“常體”。即“常”,但言辭、氣勢為“無方”,即“變”,因此,詩賦是“常”與“變”的有機統一。在“常”與“變”的關系中,劉勰重視“常”,這就是他“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所表達的思想。可以這樣認為,劉勰是在“常變”觀的基礎上,融入《易傳》中的“通變”思想,實現了“通變”的詩學轉向。那么,劉勰是如何創造性地把“常”與“通”結合在一起的呢?
何謂“常”?《說文》:“常,下蒂也。”帚,裙的本義。段玉裁注:“引申為經常。”《玉篇》:“常,恒也。”《正韻》:“久也。”有恒常、不變的意思。《易經》中有“介于石,不終日。”(《易經,豫六二爻辭》)“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易經·泰九三爻辭》)雖言“變”,但它本身就是“常”。《尚書》有“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命,民中絕命。”其中。“永”為常。“不永”為變。孔子的“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為政》)雖然言的是“損益”,但其中的“因”正強調其“常”。《易傳》中以“恒”言“常”,《管子》以“天不變”為“常”;董仲舒提出“變而有常”等等。由此可見,變中之不變早已為哲學家注意。同樣。劉勰在他的詩學思想中也非常重視“常”,集中表現了他的宗經思想。這就是他的《宗經》篇。
何謂“宗”?何謂“經”?《說文》:“宗,尊祖廟也。”段玉裁注:“當云:尊也,祖廟也。”“經,織從絲也。”段注:“織之從線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后有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天地之常經。”“經”就是綱,是常,是藝,也就是人最根本的東西。對人講,“宗經”就是要尊重祖先;對文章而言,就是尊重經書。對于“文之用心”,劉勰以為“詳其本源,莫非經典”,(《文心雕龍·宗經》)提出了“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文心雕龍·宗經》)此《易》、《書》、《詩》、《禮》、《春秋》等為立文之本,猶如祖廟一樣應當給予尊重。從“常變”這一哲學基礎出發,自然就使他的“通”引向“常”,即那些不變的東西,也就是“經”。劉勰表達他“通變”思想的經典案例,就是“文之樞紐”的《正緯》與《辨騷》兩篇,并表現了他文學觀念的崇正傾向。
二、通變的崇正傾向
劉勰對屈原評價很高,說它“軒翥詩人之后,奮飛辭家之前”(《文心雕龍,辨騷》),歸納出“典誥之體”、“規諷之旨”、“比興之義”、“忠怨之詞”等“四事”,同于《風》、《雅》,宗的是“經”,符合“常”。這是劉勰肯定屈原《離騷》的主要原因。但也指出其“詭異之辭”、“譎怪之談”、“狷狹之志”、“荒淫之意”等“四事”異乎《經》者。是“非常”,即是“變”。然而,在劉勰看來,《離騷》雖然異乎經,但在體上仍“憲乎三代”。“異”只是在“變文之數”,并在不悖“經”的立場上對其“自鑄偉辭”給予了足夠的寬容。“通”是與體之“常”相通,“變”是指文之“變”,由此,劉勰的“通變”,就是以“經”為準,變而不離其經,在不悖“經”的前提下肯定文在方式上的變化。這種理解可以在他的《宗經》篇中得到證實。他不僅肯定《易》統論說辭序之首,《書》發詔策章奏之源,《詩》立賦頌歌贊之本,《禮》總銘誄箴祝之端,《春秋》為紀傳盟檄之根,而且還提出“六義”。認為“五經”“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文心雕龍·宗經》)這里的“首”、“源”、“本”、“端”、“根”異字同義。表達了各種文體之本都起于“經”的思想:“經”體現出來的“六義”也成為他評文章的標準。他的宗經思想明確,且無可非議。
但既然要“宗經”,那又為什么要對異乎經的“四事”找出理由并給予肯定呢?這就是劉勰的智慧。他肯定時代對詩的影響,“時運交移,質文代變”,以及“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心雕龍,時序》),都表現了他思想中的積極因素。面對當時“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以追新”(《文心雕龍,明詩》)的文風,劉勰鮮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張,表現了對追新逐奇,尚麗重飾的不滿,認為“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文心雕龍·通變》)在傳統的詩學思想中,淳、質、辨、麗、雅多贊揚與肯定,而侈、艷、淺、綺,訛、新則多為批評與否定。這就是他所說的“風味氣衰”。他的判斷是建立在“原道”、“師圣”、“宗經”的立場上,提出“從質及訛”。“風末氣衰”,乃是“競今疏古”之故。對這一原因的揭示,表現了他的詩學觀念。
“通變”是先“通”后“變”。“通”是通“經”,以“經”為基
礎的變,即不悖于“經”的變。某種程度上的離“經”雖然能得到劉勰的寬容。但悖離“經書”之“變”卻遭到他的極力反對。這一思想又可在《正緯》中得到證實。張少康認為,《正緯》也是變的一種形式,是“通變”的反例。他說“緯書雖然也是‘經之變,然而,緯書變的結果是以虛假代替真實,‘乖道謬典,亦已甚矣。因此是不能提倡的。”這一說法極有道理,較好地闡釋了為什么《正緯》也在“文之樞紐”之列。劉勰將緯書歸納出“虛偽”、“浮假”、“僻謬”、“詭誕”等“四偽”,即“經正緯奇,倍摘千里”、“緯多于經,神理更繁”、“堯造綠圖,昌丹書”、“先緯后經,體乖織綜”加以反對,態度非常鮮明。這就是他想明確傳達出“變而不失為正”的思想。“正”就是“經”。在堅持“正”的同時也體現出他的靈活性來。
如果引進傳統的正變思想來分析劉勰的“通變”,可以看出他的崇正傾向。在中國傳統詩學中,凡是追求一個源頭,追求本質,在各種體之間強調經典與權威,這就是崇正思想。因此,只要是確立了一個正體,或確定了一種標準,即已經表現了崇正觀念。劉勰在“文之樞紐”中的《原道》、《征圣》、《宗經》正是追求“一源”之“正”。雖然《辨騷》是在不背“道”、“圣”、“經”前提下的改良,表現了劉勰在某種程度上的寬容,但崇正的傾向仍然是沒有改變的。
三、崇正傾向的驗證
通變思想的深層原因,正是劉勰的崇正思想。變的提出是劉勰針對齊梁文風。而這一文風恰好是悖“正”的文風。
齊梁社會風氣變異,如《顏氏家訓》所云:“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贏氣弱,不耐寒暑,生死倉卒者,往往而然。”(《顏氏家訓·涉務》)“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檐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于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顏氏家訓·勉學》)這樣的社會風尚與審美追求必然使文風日漸華靡浮艷,過度逐奇。梁代蕭子野在其《雕蟲論并序》中談到當時的文風時指出:“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于時矣。……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云,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他們故意追新逐奇,如宋代袁陽源的《雞九錫文》,說雞是“天姿英茂,乘機晨鳴”,為雞列爵封邑;江淹《恨賦》講“孤臣危涕,孽子墜心。”故意把上下兩句中的“危”、“墜”二字顛倒使用,《別賦》中的“心折骨驚”一句。也是“心驚骨折”的顛倒,以逐新奇;鮑照《石帆銘》中的“君子彼想”句,也明明是“想彼君子”的顛倒。這種毫無意義的文字逐奇在當時頗為流行。劉勰指出他們是“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事,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文心雕龍·定勢》)劉永濟先生在其《文心雕龍校釋·前言》中進一步闡述了劉勰的想法,指出他有“對于時政、世風之批評”,“亦有匡救時弊之意”,并在《議對》篇的釋義中認為劉勰“針砭當世文風,最為切要。”這就點出了劉勰詩論的針對性。劉勰認為,產生這一文風的原因是“文反正為乏,辭反正為奇”。(《文心雕龍·定勢》)“反正”就是悖“經”。“乏”與“奇”都是貶意。所以黃侃在《文心雕龍札記,定勢》注釋:“終譏近代撩人以效奇取勢,明文勢隨體變遷,敬以效奇為能,是使體束于勢,勢雖若奇,而體因之弊,不可為訓也。”
既然是“反正”造成的“乏”與“奇”,糾正自然就從“反”人手,使它重新回到“正”上來,辦法是“通”向“經”。也就是用“經”來糾正文壇的邪路。讓它回歸到文學的正道上來。從這里可以見出,劉勰“通變”的深層理論依據是他的崇正觀念。為了更好地理解劉勰這一看法,又要涉及到他關于“常”與“變”、“正”與“奇”的理解。
劉勰之“通變”是在主“常”基礎上的“變”。他認為“楚漢侈而艷”已是不好,“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更是有違文統。如何改變這種追新逐奇的不良文風,劉勰選擇了一種安全可靠的,風險最小的方法,那就是從古人那里已得到圣人的認可并得到實踐證明了的“經”中去尋找資源。這種做法表現了他對“經”的兩個基本看法:一,“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是“極文章之骨髓者也。”他提出“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肯定其“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文心雕龍·原道》)認為“唯文章之用,實經典之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成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文心雕龍·序志》)也是典型的儒家文士思想。二,通過“宗經”就可以糾正當時過分逐奇,崇尚華麗艷浮的文風。在劉勰看來,“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本源決定事物的性質。在本源中去尋找詩的本色,就不會再脫離詩道而趨于淺、綺、訛、新。
在他的《定勢》中對“奇”與“正”的認識再次表現了的崇正傾向。他說:“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事,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為乏,辭反正為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茍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定勢”就是定文章的體勢。“因情立體,即體成勢”,有其“情”必有其“體”,有其“體”必有其“勢”,“勢”由“體”定。劉勰認為這是自然的事情。體即指體制、語體,勢即指體所表現出來的外在形式。這表現了劉勰對“正”與“奇”的看法。對“近代辭人”的“文乏”而“辭奇”提出批評,“舊練之才”所以取得成就,正在于他們“執正以馭奇”,堅守正位;批評“新學之銳”是“逐奇而失正”,拋棄了“正”。因此,是否“守正”、“執正”就成為劉勰評文章的關鍵。由此可見,面對齊梁文風,劉勰開出治理不良文風的藥方是:“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文心雕龍-辯騷》),他反對“逐奇而失正”(《文心雕龍·定勢》),力主“執正而驅奇”(《文心雕龍·定勢》)。這是他“通變”思想中崇正觀念的又一次顯露。
總之。面對當時綺靡浮艷的文風。劉勰以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常變”為基礎,創造性地將“易變”與《系辭傳》中的“通變II轉向詩學,建立起詩學中的“通變”思想。他要求在不悖離經的前提下,通過表現方式上的變化,使詩創作與時代變化相應,以此使浮艷逐奇的不良文風回歸到文學的正道上來,正如他所說的,“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文心雕龍·通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