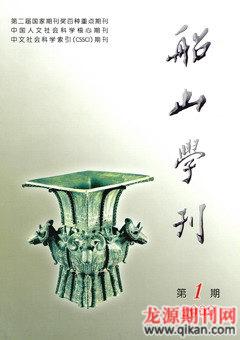五代時期統治者對忠義思想的倡導
曾國富
摘要:五代時期,叛亂頻仍,局勢動蕩,民不聊生。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將相、大臣忠義觀念的淡薄缺失,動輒兵反叛或引誘異族入犯。為穩定社會,鞏固封建統治,五代統治者通過尊崇孔子、推崇儒學、嘉獎忠義者、嚴懲反叛者等途徑,大力倡揚忠義思想,使忠義思想深入人心。
關鍵詞:五代;統治者;忠義思想
中圖分類號:G11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7387(2009)01-0075-03
忠義思想是儒家關于君臣關系及社會道德的重要思想與主張。儒家認為,忠義既是以臣事君的最基本準則,也是為人處世的美德之一。這一點,孔子在《論語》中已早有明確的論述。《論語·八佾》載:“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顏淵》又載:“子張問政,子曰:‘居之元倦,行之以忠”。為臣者的任務和職責是“事君”。為君主服務、效勞:而事君要“忠”。矢志不移。可見孔子已有忠君思想。以后,荀子子、董仲舒等儒家進一步將先秦儒家“忠君”思想加以發展,使忠君成了對君主的無條件的、絕對的服從。即所謂“愚忠”。“義”即正確合理的行為。仁、禮、智、信是義,忠君更是義:君主以俸祿豢養大臣。使大臣養尊處優,大臣理應無條件地為君主服務甚至獻出生命,即所謂“舍生取義”。因而,“忠”是“義”的內涵之一。這是“忠義”常常連稱的原因。先秦儒家之所以倡導對君主的忠義。是因為春秋戰國時代,為臣者不忠不義,惟利是圖,看風駛舵,為所欲為是當時許多大臣的普遍現象,也是“禮崩樂壞”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儒家認為臣民只有忠義于君,惟君主馬首是瞻,才能團結一致。力量強大,才能所向無敵;失去臣民對君主的忠義,天下將會大亂。儒家這一思想不無道理。即以唐末五代歷史觀照之,這一時期之所以叛亂頻仍,局勢動蕩,民不聊生,一個朝代(尤其是中原王朝)。短則三四年,長不過十余年,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將臣忠義觀念的淡薄缺失。動輒興兵反叛或引誘異族人犯。這一點,連當時北方的契丹人也認識得很清楚。據載,契丹出兵滅后晉后。許多漢人(包括君主、大臣)被迫遷徙至契丹。漢人胡嶠也滯留契丹,契丹人對胡嶠說:“夷狄(按,指契丹)之人豈能勝中國(中原王朝),然(后)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并奉勸胡嶠“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言外之義:契丹雖為“夷狄”,然而契丹人忠義于主,故力量強大;漢雖人眾地廣。然臣下對君主不忠不義,故國破家亡;欲改變受人欺凌的屈辱地位,須教“漢人努力事其主”,即讓忠義思想深入漢人之心。
俗語說,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封建史家歐陽修曾感嘆“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
其《新五代史·死節傳》只為后梁王彥章、晉裴約、南唐劉仁贍三將立傳,認為五代之時,
“全節之士三人焉”。歐陽修還就唐末五代史上忠義者文臣少而將士多的現象大惑不解發此感慨:“予于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于武夫戰卒,豈于儒者果無其人哉?”
儒家的忠義思想,不僅有利于君主維護其封建統治,也有利于抑制變亂,維持穩定的社會秩序。正因為如此,歷代封建統治者無不積極倡導忠義思想,大力表彰忠義行為,其目的正在于為廣大將帥、大臣、士卒、民眾樹立忠義的榜樣,以使封建統治長治久安。五代時期,在社會動亂的歷史背景下,統治者更是不遺余力地倡導忠義思想。其表現在:
首先,尊崇孔子。廣印儒經。
忠義思想蘊含在儒家學說之中。儒學由孔子創立。欲其樹茂,先培養其根;欲使包含忠義思想在內的儒家學說深入人心,五代統治者認為應先尊崇孔子,廣印儒經。于是,身披戎裝、能征慣戰而胸無點墨的軍閥們便頻頻舉行尊孔活動,向臣民們顯示統治者對儒家學說的推崇。對孔子的尊崇,其表現在:一是拜祭孔子,興建文宣王廟;二是優遇孔子后裔。后梁于開平三年(909),允準國子監奏請,于朝官及地方官俸錢中。每月每貫扣一十五文充土木之值。修文宣王廟。后唐朝統治者雖出自沙陀族,然而對儒家學說依然重視。表現在:一、每年春秋都舉行隆重的祭孔典禮;二、優待孔子后裔,以文宣王孔子四十三代孫曲阜縣主簿孔仁玉為兗州龔邱令。襲文宣公。后周廣順二年(952),太祖郭威在平定泰寧節度使(治究州,今山東兗州縣)慕容彥超的反叛后,率將帥到曲阜去拜祭孔子,而且表現出對孔子的極端禮敬和虔誠。史載:“六月,已酉朔,帝(郭威)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孔林樵棵。訪孔子、顏淵之后,以為曲阜令及主簿。”
此外,五代統治者還重視儒家經典的印刷發行。后唐明宗時,儒士出身的宰臣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版印賣,明宗許之。“九經”即儒家九部經典,包括《三禮》(《周禮》、《儀禮》、《禮祀》)、《三傳》(《左傳》、《公羊傳》、《谷梁傳》),連同《易經》、《尚書》、《詩經》。這項工作使命艱臣。歷經動亂而不輟,至后周朝完成。“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
其次,嘉獎忠義行為,優待忠義者家屬及后裔。
亂世之中,忠義思想及行為尤顯可貴。欲使忠義得到社會重視,深入人心。最有效的辦法莫過于朝廷的嘉獎。因此,五代時期,統治者對忠義行為嘉獎的記錄俯拾即是。嘉獎的方式主要有:
1、授以高官美爵。在封建時代,官爵代表地位、利益,為眾人所追求。五代時期,許多高官美爵即授予忠義者。如后唐朝,南平王高季興不忠不義,桀驁不馴,引發后唐與荊南的戰爭。高季興幼子高從誨力諫其父,父不從;“及季興卒。朝廷以從誨忠,使嗣,亦封南平王。”即使是敵對政權的忠義者,亦授予高官,如后周出兵攻后蜀,數為后蜀鳳翔節度使王環所敗:后周克取秦、成、階三州后,惟獨王環堅守鳳州百余日不降。城破后,周世宗“召見王環,嘆曰:‘三州已降,(王)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于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王)環右驍衛將軍。”毗外,還有大批因忠義而死的將士受到各朝的榮譽性追贈。
2、給忠義者親幸禮重。君主對某類人員的態度,亦可起到“風化”示范的作用。如當朱溫集中兵力圍攻鳳翔李茂貞而爭奪天子時,青州王師范出于忠義起兵攻之,其中王師范將劉郡勢屈力窮仍不肯投降,直到確認其主王師范已歸附朱溫后才開門迎降。朱溫因此對劉郡極其敬佩,“賜之冠帶”,“飲之酒”。以為元從都押牙。史載“是時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劉)郡一旦以降將居其上,諸將具軍禮拜于廷。”降將而受尊,皆因其忠義。唐末,藩鎮割據,多不尊奉朝廷。而荊襄節度使趙匡凝、荊南留后趙匡明兄弟卻“貢賦不絕”。朱溫篡唐,趙氏兄弟不從,遭朱氏攻擊。
趙匡凝力窮投奔淮南楊行密。楊行密對其忠義表示欽佩。“厚遇之”叫。
3、給忠義者家屬或后裔以政治、經濟的優待。忠義者已逝,對其家屬后代的優待,也可顯示朝廷對忠義思想、行為的尊崇。開平二年(908),后梁朱溫親統六軍征澤、潞二州,為激勵將士盡忠奮戰,“下詔,以去年六月后,昭義行營陣歿都將吏卒死于王事,追念忠赤。乃錄其名氏,各下本軍,令給養妻孥。三年內官給糧賜。”五代史上確有眾多忠義者家屬享受到朝廷給予的物質優待。此外,還有眾多忠義者的子孫被朝廷錄用為官。
再次,對敵對方的忠義者,既誅又赦,既貶又獎。
敵對方的忠義者忠誠于敵對政權及其君主,是為其“罪”。理應誅、貶:然而其忠義精神卻屬可貴,又應有所寬宥,此種看似矛盾之事在五代史上極常見。敵對方忠義者為敵對政權服務,寧死不屈,最易激怒征服者,成為被誅戮甚至族誅的對象;然而也有一些開明“仁慈”之君,常對敵方忠義者“網開一面”。后梁擄獲晉將石君立,“聞石君立勇,欲將之。系于獄而厚餉之,使人誘之。君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為用于梁。雖竭誠效死。誰則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為仇讎用哉!帝猶惜之,盡殺所獲晉將,獨置君立。”不殺即是對敵方忠義者的“獎勵”。后漢朝,郭威被迫反叛。稱兵向闕。后漢在京將領劉銖奉命“悉誅太祖(郭威)與王峻等家屬”。郭威攻人京師,擒劉銖。郭威責讓他慘酷屠戮其家屬。劉誅以“為(后)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他!”為對,表現了其對后漢朝的忠義。按理,劉銖當被族誅。但郭威“方欲歸人心”,只誅劉銖而“貸其家屬”,并“賜陜州莊宅一區”㈣。有些敵對方忠義者先被誅而后被追贈或錄用其后代。亦屬此類。
第四,對不忠不義的叛亂行為堅決鎮壓。殘酷戮殺或冷遇反叛者。
獎勵是推動的手段,懲罰則是控制的手段。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在以各種方式表彰、獎勵忠義者的同時,五代統治者對于不忠不義的反叛行為則嚴肅、嚴厲懲處。以讓大臣、將領引以為戒。如,后唐滅后梁,后梁百官迎降待罪。后唐莊宗將鄭玨等一批后粱高官貶逐到地方任職,“以其世受唐恩而仕(后)梁貴顯故也”。在莊宗看來,這些高官。他們的祖、父輩在唐朝任官,受唐朝之恩,他們卻任職于篡唐而立的后梁朝。這是對唐朝的不忠不義:如今后梁滅亡,他們又投奔新朝,又是對后梁朝的不忠不義。故應貶逐。以做效尤。
對叛亂者殘酷殺戮是五代史上司空見慣的現象。如后唐天成元年(926)五月,詔發汴州控鶴指揮使張諫等三千人戍瓦橋。將士不愿戍邊而反叛。平叛后。明宗下詔“收為亂者三千余家,悉誅之。”同年六月。滑州都指揮使于可洪等縱火作亂。叛平,明宗下詔“斬可洪于都市,其首謀滑州左崇牙全營族誅,助亂者右崇牙兩長劍建平將校百人亦族誅”。天成二年(927)三月,盧臺戍軍作亂。四月,明宗“敕盧臺亂兵在營家屬并全門處斬。敕至鄴都。闔九指揮之門,驅三千五百家凡萬余人于石灰窯,悉斬之,永濟渠為之變赤。”如此一人反叛全族誅戮的做法未免過于殘酷,但它對不忠不義者卻是有力的威懾!即使不是反叛,將士在戰場上不能為君為國奮力作戰,而是望敵先逃,也被認為是不忠不義的行為,也要受到嚴厲懲罰。如后周世宗誅高平敗將等。許多反叛者叛亂后投靠相鄰政權或其他軍閥。然而,這些反叛者總難以擺脫受歧視、受冷遇、受猜疑的境地。這是因為,在這些政權的君主、軍閥看來,反叛者都是忠義思想淡薄者,這些人不會對君主感恩,必然動輒反叛,收留容納他們,無疑于養虎為患。如后蜀施州刺史田行皋因故叛奔荊南。荊南節度使高保融說:“彼貳于蜀,安肯盡忠于我!”執之,歸于蜀,伏誅。許多君主或軍閥在臨終之際,都要設法誅除那些因叛亂而投奔來且掌握實力者,擔心他們的存在會對其后代造成危害,如后漢劑知遠臨終誅杜重威、前蜀王建臨終誅劉知俊等。
總而言之,在五代時期征討叛亂、保家衛國、開拓境土等軍事活動中。最高統治者充分認識到了儒家忠義思想的重要。尤其是在對付此起彼伏的軍事叛亂,殘酷殺戮常常難以阻遏叛亂的再發生,正如封建史家胡三省所言,后唐自明宗“即位以來,汴州張諫之亂。滑州于可洪之亂,以至盧臺之亂,凡亂兵皆夷其家。然而流言不息。吟吟然疾視其上者相環也。此無他,以亂止亂故爾。”這種以“亂以止亂”、“以殺去殺”的方法實際上無助于防上叛亂,它常常使反叛者對君主仇恨更深,抵抗更頑強;反之,儒家的忠義思想常常可以成為阻止、防遏叛亂的有效武器。這種思想猶如叛亂的“滅火器”,如果將士心中都懷著這樣的“滅火器”。叛亂就不會發生,即使發生也容易被鎮壓(不少叛亂剛發生,叛酋即被軍中忠義之將士襲殺即為例證)。不僅如此,在對外拓疆及抵御外敵入侵中,忠義思想又是激發將士斗志的“鉦鼓”:在勾心斗角的政治斗爭中,忠義思想又是阻擋野心家篡權的“銅墻鐵壁”……這就是五代時期統治者尊崇孔子,推崇儒學,嘉獎、倡導忠義思想、行為的原因所在。正因為統治者的積極倡揚。使儒家忠義思想深入社會人心,對人們,尤其是對軍人(將士)的思想、行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