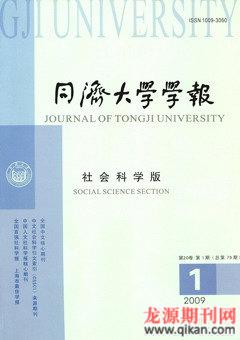跨文化視野中符號意義的變異與多樣性
吳越民
摘要:符號意義的復雜性,主要表現為意義“生命”的過程性、意義類型的多樣性和意義層次的開放性。意義是作為符號能指和所指同時產生的,它也有一個增長、變異乃至消亡的過程。在類型上,符號意義可以有不同的類別,如內涵意義和外延意義、理性意義和聯想意義、象征意義等。我們要在特定的文化語境中,對各種復雜的符號進行動態分析,揭示這些符號在不同文化中的象征意義,揭示其產生與發展的內在規律與生成模式,深入地挖掘其深層結構中的文化內涵,促進跨文化的言語交際和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關鍵詞:符號意義;變異;多樣性;跨文化差異
中圖分類號:GO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3060(2009)01—0091—07
一、引言
符號的意義就是符號通過符形所傳達的關于符號對象的訊息。在我們生活的符號世界里,周圍的符形無時無刻不在向我們傳達訊息:商店門上懸掛的招牌向我們傳遞這家商店賣什么商品的訊息;柜臺上標著的數字向我們傳達著商品價格的訊息;墻上的海報向我們訴說著關于某種新產品的訊息;大廳里懸掛著的橫幅向我們提供有關店慶大減價的訊息。我們從這些符形中獲得各種訊息,也就意味著我們理解了符形的意義。
美國哲學家、現代符號學奠基者之一查爾斯·桑德斯皮爾斯(C.S.Pierce)不但肯定了外部世界的存在,將符號對象引入符號三角,而且認為符號意義是在認知主體與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中產生的。此外,皮爾斯的符號學理論還關心產生意義的生活背景,而不僅僅停留于符號本身。他在論及符號意義時,曾這樣說過:“除非我們將指稱對象同集體意識聯系起來,不然它們不可能具有意義。”這里的集體意識指的就是符號使用者關于生活世界的知識積累,它主要來源于符號使用者的集體生活。這無疑是對符號二元關系的一種突破,使符號的意義獲得一種開放性。
“意義”是一個相當復雜的概念。符號意義的復雜性,主要表現為意義“生命”的過程性、意義類型的多樣性和意義層次的開放性。意義是作為符號所指和能指同時產生的,它也有一個增長、變異乃至消亡的過程。在類型上,符號意義可以有不同的類別,如內涵意義和外延意義、理性意義和聯想意義、象征意義等。在層次上,符號意義具有無限的開放性,除非現實生活的壓力迫使我們中斷這種在理論上具有無限可能性的意指活動。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E.Cas—sirer)認為:“符號化的思維和符號化的行為是人類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類文化的全部發展都依賴于這些條件。”他甚至把符號同人的本質等同起來,與人類文化的產生和發展聯系起來,把人界定為“符號的動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指明人的獨特之處,也才能理解對人開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符號是文化的載體,文化的創造和傳承是以符號為媒介的。人是符號活動的主體,各種文化是符號活動的現實化、具體化。這樣,通過符號活動,人與文化有機地聯系起來。從符號學觀點看,不同民族的文化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現象,它反映著一定社會、民族的經濟、政治、宗教等文化形態,蘊涵著民族的哲學、藝術、宗教、風俗以及整個價值體系的起源。千百年來,它以一種鮮活的形式承載著人類文化的傳播,從而構成了文化的動態化符號。本文擬在跨文化視野的背景下探討符號意義的變異和多樣性。
二、符號意義的變異
意義在不斷增長和延伸中可能會出現變異的現象。“變異”一詞本來是生物學中的一個概念,指的是同種生物世代之間或同代生物不同個體之間在形態特征、生理特征等方面所表現的差異性。在符號學中,符號意義的變異指的是這樣一種現象,即符號能指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或同一歷史階段的不同場合具有多種不同的意義,而這些不同意義與原意之間沒有任何關聯性。
1新理據與符號意義的變異
符號意義的變異主要是因為新理據的引入而發生的。建構新理據的訊息可以來自符號對象,可以來自符形本身,也可以來自符號所處的環境或符號認知主體的經驗。
以文化蘊含豐富的“龜”為例。“龜”有“神靈”意。傳說龜千年則能言,《左傳》記:“龜兆告吉”。古有“龜經”、“龜旗”、“龜龍”、“龜鏡”之說,象征吉祥順利,因為古占卜時用龜甲。《禮記·王藻》記:“卜人定龜”。“龜”可指貨幣,古代曾以龜甲為貨幣,《易·損》載:“或蓋之十朋之龜,弗克違,(遠吉)”“兩朋為一龜,十朋之龜,人象也”。古代人們首先認識到的是龜這種爬行動物生命周期很長的特征,《莊子·秋水篇》;“楚有神龜,死已i千歲矣。”曹操有詩:“神龜雖壽,猶有競時。”唐朝李群玉詩《龜》:“靜養千年壽,重泉自隱居。”因此人們“借龜之名,效龜之行,托龜之庇,以追求長壽,并相沿成習”,現在仍有“龜齡鶴算”之說。“龜”成了中國壽文化的重要象征符號。而到了元代以后,龜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急轉直下,由貴反賤,龜壽崇拜的習俗逐漸消失。其主要的原因是人們發現龜常和蛇、鱉在一起,就用龜來指稱妻子與他人通奸的男子,明朝謝肇浙《五雜俎·人部四》中記:“今人以妻之外淫者,目其夫為烏龜。”“龜”可用來罵人,如“烏龜王八蛋”。“龜”還用來貶斥怯懦的人,如“縮頭烏龜”。元朝尚仲賢《單鞭奪槊》第二折;“如今只學烏龜法,得縮頭時且縮頭。”
楊柳在中國文化中可用來喻指“盎然的春意”,《詩經·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就有春去冬來之意。楊柳風姿綽約,撩人心懷,因此常用“柳姿”來形容女子“姿色”。楊柳柳絮漫天飛舞,漂浮不定,所以,女子用情不專、移情別戀被稱為“水性楊花”。南此,“花街柳巷”、“花門柳戶”、“墻花路柳”、“尋花問柳”、“攀花折柳”等詞語中的“花”和“柳”表達的是“妓院”、“妓女”等意思,楊柳作為象征符號所表達的意義發生了變異。
中華民俗中,處處可見魚的蹤跡。在人們的觀念里,年年餐桌有魚,象征年年有余,生活富足。魚是表現吉祥主題的重要題材。魚是怎樣獲得這種象征意義的呢?這可從上古歷史文化背景著眼來進行考察:初民的謀食方式及對司水魚神的崇拜使魚成了豐收富裕的象征;而由水生殖信仰演化來的魚生殖信仰及魚本身繁殖力強的特性,使“魚”在傳統文化中染上生殖色彩,成為婚姻、愛情的象征物或性愛隱語。
由此可見,如果以符號對象的不同性質為理據,符號的意義就會發生變異。
2場景與符號意義的變異
符號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傳播活動的全部意義,傳播意義的相當一部分來自于場景(所謂“言外之意”)。“場景”包含(1)符號系統自身的環境。如書寫符號系統的上下文、實物實體符號系統的空間布局、圖像符號系統意境配列關系等;(2)傳受雙方的已知信息背景。包括言語的話題、實物實體的“實用”功能、藝術系列的準備
知識等;(3)系統存在的社會環境。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形態、文化氛圍、傳受雙方關系彼此了解等。符號在傳播過程中由于上述因素而衍生出來的意義,就叫“場景意義”。符號基本是我們與周圍世界進行有效交往的工具,但許多感受不是在符號之中的,常常是“言不由喻”的。符形所處的環境也會為符號意義的變異提供理據。例如“他是個大學生”,如果在教授前面說這句話,意味著這個人是一個“初學者”、“沒有經驗的人”;如果在一群工人中講這句話,則意味著這個人“是有學問的”,甚至可能是“專家”。由此可以看出,一個符形的意義是由其所在參考系決定的,參考系發生變化,意義也會隨之變化。
假如沒有一定的音樂知識和背景文化,西方的交響樂對中國人來說理解是十分困難的;同樣,沒有漢字修養和背景文化,中國的書法對外國人同樣是不可思議的。系統內在的環境也是十分重要的,人們總是首先從符號系統內部尋找意義,而符號的內在意義不是預先可知的,需要加以分解和處理,了解其組合關系和結構,使意義顯現出來。
3認知主體的經驗與符號意義的變異
意義變異的理據性支持,有時候還來自于認知主體的經驗。由于認知主體的經驗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對符形進行解釋的依據也會有差異,從而導致符號意義的變異。
《人民日報》海外版曾刊登的一則報道生動地說明了由于認知主體的經驗不同而導致符號意義的變異。這則報道敘述的是:一對旅居日本的華人夫婦在東京開設了一家取名為“北京亭”的餐館。他們拒不接待那些把中國稱呼為“支那”的顧客。他說:“一聽到有人把中國叫‘支那,我就不由地回憶起日本侵略中國,侮辱、殘害中國人的那段歷史。為了中日兩國人民子子孫孫友好相處,請不要叫‘支那,要稱呼‘中國……”。“支那”本是起源于秦代中國的異稱,最初出現在佛教經典中,后傳入日本,在日語中是古今中國的總稱。“支那”在日語中并非貶義詞,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侵略軍總是使用該詞,因此它就帶上了一種特殊的語義特征。那些至今還用“支那”來稱呼中國的日本人當然無法理解該詞在老一輩中國人心中所激起的如此強烈的憤慨。
人們對語言的理解雖然主要取決于符號載體的所指意義,但是也常根據自己的經驗或價值觀繁衍出許多語用意義。因此,符號的意義常常根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個人經歷而表現出較大的變異。在西方,金發女郎,亭亭玉立,必然會受到老板或上司的青睞,英語中因而常用a fair-haired girl比喻“紅人”,但漢語中的“紅人”源于“紅”象征順利、成功或受人重視(《現代漢語詞典》),所以若用a red haired girl表示“紅人”,則是張冠李戴,英美人可能會把它誤解為“紅頭發女人”。同理,西方人讀到中國的“白毛女”,往往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而難以窺見a white-haired girl所蘊含的“舊社會使人變成鬼,新社會使鬼變成人”的這種特殊喻義。
又如,rock and roll(搖擺舞曲)的明指意義是a kind of popular music with a strong beatand a simple,repetitious melody,但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來說,rock and roll可能意味著ex—Citing,amusing,enjoyable,noisy,annoying等。同一個符號的意義,有不同的解釋,完全是因為解釋者所處環境和個人的經驗等因素的不同所造成的。
三、符號意義的多樣性
符號的意義是極其復雜的,這種復雜性在意義類型上表現為意義的多樣性,如內涵意義與外延意義、理性意義與情感意義、象征意義等等。
1符號的內涵意義和外延意義
內涵(connotation)一詞源于希臘語“conno—tare”——“附加”,指附加在詞語(和其他傳播形式)上的文化含義。一個詞語的內涵通常包括其象征的、歷史的和情感的內容。法國著名符號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神話學》(Mythologies)(1972)一書中揭示了法國日常生活很多方面的文化內涵,如牛排、薯條、清潔劑、雪鐵龍汽車和摔跤等。他說,建議舉辦一個全世界的“什么事情是不言而喻的”(what—goes—with—out—saying)活動,以此揭示這個世界的內涵,進一步而言,揭示這個世界的意識形態基礎。
相對的,外延(denotation)指詞語和其他現象的字面含義或外在含義。例如,芭比娃娃(Bar—hie Doll)的外延指一個小玩具,1959年首次在市場上銷售,最初它有11.5英尺高,胸圍5.25英尺,腰圍3.0英尺,臀圍4.25英尺。與之相對,芭比娃娃的到來意味著母親作為婦女支配性角色的終結,意味著消費者文化的重要地位。因為芭比是個把自己的時間打發在購買服裝上的消費者,而且她正在與肯(Ken)以及其他玩具建立聯系。不像其他玩具,芭比娃娃并不想賦予小姑娘以傳統母性的角色——讓她們模仿自己的媽媽,照顧“小寶寶”。
現在,芭比娃娃已經成為了一種文化和政治的象征。甚至有人將芭比視為除可口可樂、麥當勞之外,資本主義勢力的另一種代表。在美國許多大學,“芭比學”甚至可以成為專門一堂課,透過芭比現象探討女性心理、角色、男女關系,以及女性與社會的互動等問題。
符號的內涵和外延現象是一個非常具有能產性的生成過程,因為社會已經從人類語言為其提供的具有第一意義的符號系統,不斷地發展出第二意義的符號系統。這樣每個符號的演化過程就顯得非常接近真正的歷史人類學,每個第一意義系統的符號都真實記錄下人類認知和行為的歷史過程,有的符號當它作為第一意義系統意指的客觀事象已經消失,但它卻在第二意義系統里作為能指或作為所指獲得新的意義而被保存下來。這時,我們甚至有可能從第二意義系統的意指去探求它的初始意義。比方說,“洞房”這個符號形式在第一意義系統里意指遠古時代以山洞為家的原始婚姻情況,但在第二意義系統里以能指形式出現在表達層面,其內涵為“現代人結婚的新房”。第一意義系統的“洞房”成為歷史詞,或者叫“化石”詞;第二意義系統的“洞房”成為內涵的能指(外延系統的構成),它與原來的單位在外延上不具有同樣的大小規格,不僅在質上有了新的蘊涵,而且在所指范圍上也發生變化,例如旅行結婚的旅館客房也屬于“洞房”。在傳播符號學的研究中,第一意義系統的符號構成第二意義系統的所指,也就說語言符號被用來描述傳播符號系統中的能指,它起著元語言的作用。新婚夫婦在旅行途中租借了旅館的客房,度過他們新婚的第一夜:“客房”作為文化性符號存在于第二意義系統的能指,其所指如果是一個外延符
號——“洞房”,那么“洞房”又是作為元語言對“客房”進行了重新定義(即被意指)。
由此可見,符號的內涵意義和外延意義并不是永遠固定不變的。客觀事物本身是發展變化的,隨著客觀事物的發展變化,符號意義也會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化。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不同的歷史時期,相同的詞語在不同的符號情境中的內涵意義和外延意義也有所不同,這些意義與社會的、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等方面有著緊密的聯系。
2符號的理性意義與聯想意義
理性意義是符號解釋項中認知主體在判斷、推理等活動基礎上獲得的那部分內容。科學解釋就是理性意義的典型例子,因為在科學解釋中,情感意義被嚴格地排除在外。如果說理性意義是語言表達某一客觀事物、某一思想概念時所獲得的意義,即我們通常所說的指稱意義,那么符號的聯想意義則是人們在使用語言時聯想到的現實生活中的經驗,表達人們在使用語言時感情上的反應,是符號在認知主體頭腦中激起的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應,如喜歡、憤怒、悲傷、恐懼、愛慕、厭惡等。并從廣義上顯示出特定語言集團的社會文化特征,因此有的語言學家稱之為社會文化意義(social—cultural meaning)。
語言中有一類詞語的聯想意義大大超過它的理性意義。如果觀點和情感是通過這類詞語來表達的話,信息的情感意義就會超過理性意義,聽者和讀者對所說的內容便無法作出正確的評價。正如英國語言學家杰弗里·利奇所說“理性意義是語段公開的或者字面上的意義,即從表面上看來,它告訴我們這語段是‘關于什么的。相反,情感意義則是一種內涵的、潛在的意義。”
一個民族或語言社區是在一定社會歷史階段上發展起來的人類群體。它有著共同語言、共同區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種共性不僅知道和控制人們的心理、情緒,而且為人們提供價值觀念、思想方式、行為規范,從而使人們按照一定的導向去生活、行動,形成一個民族共同的精神形態上的特點。這種精神形態的不同又是一個民族區別于別的民族的重要標志,它包括思想、意識、感情、心理等不同的精神特征。柳樹在漢語中通常被賦予分離、思念的聯想意義,在“詩經”中就有:“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的描述。它比較形象地概括了戎邊戰士思念家鄉和親人的感情。在中國古代詩詞中,借柳樹來抒發離別思念之情的很多,如李白的“憶秦娥”中的“奏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春夜洛城”中的聞笛:“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溫庭筠的“河傳”中的“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聞郎馬嘶”。柳樹之所以具有這樣的文化內涵,是因為中國漢字文化中的諧音造成的。“柳”與“留”諧音,在長期的文字使用過程中,將“挽留、離別、思念”等這樣的涵義賦予“柳樹”也是很自然的,柳條纖細柔韌,象征情意綿綿,永不相忘,這也恰恰反映了中國人喜歡以物喻人,借景抒情,崇尚自然的文化心理。古詩中一個“柳”字有時竟能確定整首詩的基調及主題。中國畫也是崇尚寫意,而不重形式的,也許畫面中對于柳樹寥寥數筆的描繪就完全能使人意會到其中深藏的涵義。
而willow在英語中卻與中國文化中的“柳樹”有著不同的文化內涵,它常能使人聯想起悲哀與憂愁,失去心肱的人等等。如在莎士比亞《奧賽羅》(Othello)中,苔斯德蒙娜(Desdamona)就曾唱過一首“柳樹歌”,表達她的悲哀,同時暗示了她的死。在《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Venice)中,Lorenzo提到女王Dido因她所愛的人Aeneas遺棄了她,柳樹象征悲哀,她過度悲哀而自殺。在Dryden所寫的“Secret Love”中,柳樹也有這樣的聯想意義:if you had not forsaken me,I had you:so the willows may flourish forany branches I shall rob them of,這些都表明willow與漢語中的柳樹雖然所指物體相同,但其中所包涵的文化內涵卻不同。
由此可見,符號的意義和社會文化是緊密相關的。在言語交際中,由理性概念所產生的字面信息并不難接受,因為字典中對詞匯的理性意義一般均有明確的定義。而附加于理性意義之上的聯想意義,即文化信息,由于受交際雙方文化差異的制約,就不那么容易接受。
四、符號的象征意義與跨文化差異
在符號學意義上,象征是符號的普遍功能,廣義的象征可以理解為用一種事物指代另一種事物。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語言符號和表象符號都是象征符號,象征性可視為符號的一般功能。但是,在文化語境中,語言符號和表象符號的象征性功能要比在認知語境或交際語境中的符號更為復雜一些。
首先,文化語境中的表層符號(包括語言和表象)不僅僅指涉另一個事物或意義。某個詞或詞組與某種視覺表象或聽覺表象指涉另一個事物或意義,而被指涉的物體或意義反過來又表示超出其本身的某種事物或意義或具有一個聯想的區域。
其次,一般符號的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必須是約定俗成的,但文化語境中表層符號的這種象征聯系既可以是“公共的”,如旭日象征誕生、竹象征氣節、玫瑰象征愛情,等等;也可以是“個人的”,如麥爾維爾《莫比·狄克》中的白鯨、布萊克《病玫瑰》中的玫瑰等,它們更多被賦予了個人的獨特的指涉含義,其解碼也更為困難。
再次,一般符號象征的能指與所指之間的結合關系可以是任意的,只要約定俗成,得到群體的認同即可。這種任意性表現在符號的能指與所指之間不必存在什么性質上或結構上的相同性,兩者可以是“異質異構”的結合關系。能指一旦引出所指,其自身可以完全消失,并不影響符號的象征功能。而文化語境中的象征符號的能指與所指之間關系要求是“異質同構”的,兩者具有結構上的一致性,且相互依存不可分解,離開能指(符號的表象或語言的音形)來理解所指,往往使原有的象征性發生變異,甚至導致符號功能的消失。
通過分析跨文化視野中符號的象征意義,我們可以管窺一定社會文化生成與發展的源流與底蘊,對一個民族文化之根進行深刻的挖掘。
作為現象符號的神話主角鷹、蛇,積淀了厚重的文化內涵,鷹蛇喻象形成一套具有傳統喻義和道德評價色彩的符號系統,在人類神話系統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鷹與蛇在中西方文化背景下有著不同的文化內涵和象征意義。
中國南鷹蛇變形而來的龍和鳳,經過古人想象,不僅成為華夏民族最神圣的徽號,而且廣泛參與喻象符號的生成。如:龍鳳用于比喻帝王、帝后。秦始皇被稱為“祖龍”,杜甫《哀王孫》詩:“豺狼在邑龍在野”,龍指唐明皇。皇帝登位或死亡稱“龍升”,帝王生氣為“龍顏大怒”。“龍鳳”也用于比喻才德兼備、杰出非凡者。屈原的作品開
辟了“虬龍鸞鳳,以喻君子”的傳統,后世諸葛亮、龐統分別有“臥龍”、“鳳雛”之稱。中國古人在創造這一系列符號的同時,也塑造了美好的自我,“龍”“鳳”成為詩意濃郁的中國文化環境中鮮活的生命。鷹在中國常作為英勇機靈高潔人品的象征,唐代詩人柳宗元在《籠鷹詞》中塑造了勇猛進擊、氣勢不凡的蒼鷹形象:凄風淅瀝飛嚴霜,蒼鷹上擊翻曙光。
在西方,鷹蛇喻象出現于文人作品較早的,是古希臘悲劇家埃斯庫羅斯的《俄瑞斯特斯》三部曲,在悲劇中,阿伽門農出征歸來,被自己的妻子克呂墨斯特拉伙同奸夫殺死,劇中克呂墨斯特拉的喻象就是毒蛇。從文藝復興開始,鷹蛇符號不再是基督教神話中宗教觀念的載體,而是貫注了內在的活力,按照人格化的道路發展,直接與人的生命狀況相聯。這突出表現在莎士比亞的劇作中,莎士比亞多次用鷹蛇作為人的喻象,如李爾王稱自己狠毒的女兒是“毒蛇”、“餓鷹”,美麗、狡猾又富于激情的克莉奧帕特拉被她的情夫安東尼稱為“尼羅河畔的花蛇”。18到19世紀,鷹蛇作為文學符號也沖破古典主義規則,在文人話語系統中重新嶄露其強悍與野性的面貌,并一直延續到現代。此期,有感于現實世界中弱肉強食的慘烈,鷹常作為暴君的象征,如拜倫稱拿破侖為“盤桓不去的兀鷹”,穆爾稱神圣同盟的君主“猶如掠奪成性的鷹鷲”。
由于宗教、文化、民族、思想意識、價值觀念以及社會心理等方面的差異,不同民族賦予顏色的情感語義、象征語義和文化語義是復雜的、有時甚至是對立的。同一種顏色以各種聯想作為橋梁,與不同的事物聯系在一起時就會產生不同的情感意義和象征意義。當它與不同的文化相聯系時又會產生不同的文化意義。以“黃色”為例:漢語中的“黃色”在中華民族所產生的情感及其象征意義顯然不同于英語的yellow在英語文化中的象征意義。“黃色”幾乎成了中華民族及其尊嚴的象征。這不僅是中華民族是“黃皮膚”的民族,擁有“黃土高原”以及母親河“黃河”,且被認為是“炎黃子孫”的象征。我們的國旗上繡有“黃色”的五角星。在歷史上,“黃色”一直是“尊貴”的象征,只與帝王將相相聯系。傳說皇帝服黃衣,戴黃冕。隋、唐時,華貴的服裝被稱為“黃衫”,皇帝的文告須用“黃”紙寫,被稱為“黃榜”。在《野客叢書·禁用黃》中有這樣的記載:“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在英語文化中,黃色的皮膚被認為是由于嫉妒導致黃膽汁分泌過多的緣故。肝炎患者的典型癥狀之一就是yellow eyes,面部有一種jaundiced view。有趣的是“肝”曾被認為是theseat of love,因此yellow成為象征jealousy的色彩。早在17世紀,英語中就有了短語wearyellow hose,意思是jealous。在1602年,Mid—dleton把富有嫉妒心理的女性描寫為yellow la—dy。1611年,莎士比亞在The Winters Tale中首次使用了yellow jealousy一語。
由此可見,文化語境中的符號往往能以一種人們所不期望的方式影響整個文化。符號的象征意義是人類古往今來文化形態共同的深層“密碼”,無論是自然的、歷史的還是現實的、心理的,都無法越過文化形態直接獲得,所以,我們在自己頭腦中對客觀事物進行符號思維的時候,決不能忽略符號在不同文化中所表達的不同含義。
五、結語
綜上所述,不同民族語言的符號意義,其具體的形成條件往往是各不相同的,每個民族都有著不同的文化歷史和文化特征,他們特有的生活習俗、心理定勢、思維方式、觀察視角等,在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制度中得到特殊的傳承、變異以形成與該民族有千絲萬縷聯系的文化特征。在其發展過程中語言符號系統和符號意義的生成都被刻上了社會生活的烙印,反映了一個特定社會獨特的文化傳統。正如德國著名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E.Cassirer)所說,符號是把人與文化連接起來的中介物、媒介物。人是進行符號活動的動物。正是“符號現象”構成了一個康德意義上的“現象界”——文化世界,正是“符號活動”在人與文化之間架起了橋梁。符號象征,經由語言才能得到詮釋。我們要在特定的文化語境中,運用結構分析、功能分析、意義分析等手段,對各種復雜的符號進行動態分析,揭示這些符號在不同文化中的象征意義,揭示其產生與發展的內在規律與生成模式,深入地挖掘其深層結構中的文化內涵,促進跨文化的言語交際和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責任編輯:陳曉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