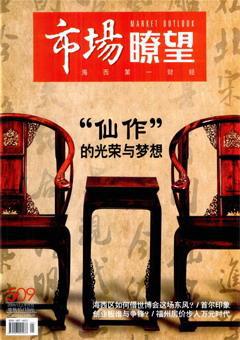《老子的智慧》
論常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wú)名,天地之始;有名,萬(wàn)物之母。故常無(wú)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徽。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mén)。
語(yǔ)譯:可以說(shuō)出來(lái)的道,便不是經(jīng)常不變的道;可以叫得出來(lái)的名,便不是經(jīng)常不變的名。無(wú),是天地形成的本始;有,是創(chuàng)生萬(wàn)物的根源。所以常處于無(wú),以明白無(wú)的道理,為的是觀察宇宙間變化莫測(cè)的境界;常處于有,以明白有的起源,為的是觀察天地間事物紛紜的跡象。他們的名字,一個(gè)叫做無(wú),一個(gè)叫做有,出處雖同,其名卻異。若是追尋上去,都可以說(shuō)是幽微深遠(yuǎn)。再往上推,幽微深遠(yuǎn)到極點(diǎn),就正是所有的道理及一切變化的根本了。
道不可名,不可言,不可談
泰清問(wèn)無(wú)窮說(shuō):
“你瞳得道嗎?”
無(wú)窮說(shuō):“不知道。”
又問(wèn)無(wú)為,無(wú)為說(shuō):“我知道。”
泰清說(shuō):
“你所知的道,有具體的說(shuō)明嗎?”
無(wú)為回答說(shuō):“有。”
泰清又問(wèn):“是什么?”
無(wú)為說(shuō):“我所知的道,貴可以為帝王,賤可以為仆役,可以聚合為生,可以分散為死。”
泰清把這番話告訴無(wú)始說(shuō):
“無(wú)窮說(shuō)他不知道,無(wú)為卻說(shuō)他知道,那么到底誰(shuí)對(duì)誰(shuí)不對(duì)呢?”
無(wú)始說(shuō):
“不知道才是深邃的,知道的就粗淺了。前者是屬于內(nèi)涵的,后者只是表面的。”
于是泰清抬頭嘆息道:
“不知就是知,知反為不知。那么究竟誰(shuí)才懂得不知的知呢?”
無(wú)始回答說(shuō):
“道是不用耳朵聽(tīng)來(lái)的,聽(tīng)來(lái)的道便不是道。道也不是用眼睛看來(lái)的,看來(lái)的道不足以稱為道。道更不是可以說(shuō)得出來(lái)的,說(shuō)得出來(lái)的道,又怎么稱得上是其道?你可知道主宰形體的本身并不是形體嗎?道是不應(yīng)當(dāng)有名稱的。”
繼而無(wú)始又說(shuō):“有人問(wèn)道,立刻回答的,是不知道的人,甚至連那問(wèn)道的人,也是沒(méi)有聽(tīng)過(guò)道的。因?yàn)榈朗遣荒軉?wèn)的,即使問(wèn)了,也無(wú)法回答。不能問(wèn)而一定要問(wèn),這種問(wèn)是空洞乏味的,無(wú)法回答又一定要回答,這個(gè)答案豈會(huì)有內(nèi)容?用沒(méi)有內(nèi)容的話去回答空洞的問(wèn)題,這種人外不能觀察宇宙萬(wàn)物,內(nèi)不知‘道的起源,當(dāng)然也就不能攀登昆侖,邀游太虛的境地。”(《莊子·外篇》第二二章《知北游》)
有關(guān)道不可名的觀念,請(qǐng)參看二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