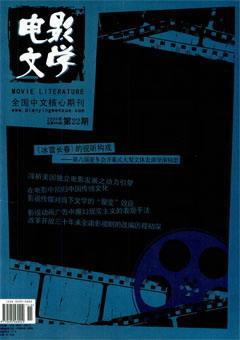電影與何去何從的女性主義
詹才女
[摘要]自西方女性主義電影理論引入中國以來,中國電影理論工作者將理論與電影創作的實踐相結合,進行中國的女性主義電影批評的理論建構。本文通過解讀女性主義電影批評理論史,指出中國女性主義電影批評不僅批評過程中缺乏激進的批判姿態,批評對象(女性電影作品)也迷失了方向,從而試圖闡釋中國女性主義電影及其批評的出路。
[關鍵詞]女性主義;電影理論;女性主義電影批評
在上世紀80年代,引人中國的西方女性主義電影理論是新鮮的視覺理論之一,給中國帶來了女性主義電影批評的思潮。20世紀80年代,尼克·布朗先生來華講學,介紹了他所寫的《女權主義電影理論:起始》。這篇文章評述了穆爾維的《視覺愉悅與敘事性電影》和格萊德希爾的《當代女性主義的最新發展》兩篇女性主義電影理論。穆爾維和格萊德希爾在“兩性差異”上,運用符號學、精神分析學和意識形態理論知識,分析了當時電影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兩人都認為西方國家的文化,基本上是父權制的和以男性為中心的。在這層認識的基礎上,穆爾維研究了影片中女性的角色問題——集中在女性是提供給觀眾視覺愉悅的角色上。格萊德希爾試圖用精神分析學和符號學,解剖電影中的女性元素。她得出“因為女性不是男性,所以她們是不做聲或不露面的”“電影中的女性形象僅用于重新肯定男性的統一、完整和安全”。這些新奇的理論觀點,引起了中國不少電影人的思考。此后,不少電影批評者開始了建構中國的女性主義電影批評理論的歷程。
十幾年后,李道新先生在《中國電影批評史》中寫《女性主義批評》一節,一開文就提及了尼克·布朗先生介紹過的兩篇女性主義奠基作品。他簡述了西方“女權運動”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女權主義電影理論是如何被中國電影批評者意識、認同以及在批評實踐中的運用和演變等情況。《女性主義批評》以選取在中國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主義電影批評文獻作個案闡述與分析的方法,講解了中國女性主義電影批評發展的歷程。在細讀電影批評史的過程中,引發了本人對中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建構過程中的以下幾個方面的思考。
一、關于缺乏的激進批判姿態
細讀《女權主義電影理論:起始》和《女性主義批評》,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穆爾維還是格萊德希爾,與中國女性主義電影批評者相比較,理論的建構傾向性存在著很大差異。同樣都作為建構女性主義電影理論的批評者,在強調性別和以鮮明的女性立場對整個男權意識形態進行批判的共同特征下,中國的批評者的批判態度(尤其是在對社會的意識形態批判上)溫和過多,女性立場不夠徹底。李道新先生對這種差異有這樣一段評述:
總的來看,中國的女性主義電影批評,由于缺少西方婦女解放運動的社會、政治及文化背景,在努力確證中國電影的女性意識前提下,也缺少了西方女性主義電影批評對社會、政治及文化的激進性批判姿態;但同時,作為文化研究領域里的一種解構,顛覆男權文化的反本質立場,中國的女性主義電影批評在對中國電影里的性別差異、女性欲望以及女性主體意識進行解構的過程中,卻也相當清晰地正在書寫一部顛覆經典、重塑性別的中國電影史。
很顯然,李先生對中國的女性主義批評為什么缺乏激進的批判姿態,更多歸咎于“缺少西方婦女解放運動的社會、政治及文化背景”。我卻認為,在提出了女性意識后,對社會制度中的女權被壓抑的事實現狀、理論工作者都應該有戴錦華一樣的女性創作立場:呼喚整個社會對女性權利的尊重,尤其是社會中作為女性自身的主體應自覺提升女性意識。如果說“由于缺少西方婦女解放運動的社會、政治及文化背景,在努力確證中國電影的女性意識前提下,也缺少了西方女性主義電影批評對社會、政治及文化的激進性批判姿態”,不如說中國的女性主義電影理論批評者絕大多數放棄了政治性意識形態批判。近20多年來電影批評的文獻中,對男性中心的批判比比皆是:男導演在電影中書寫的“他者”女性、女導演尋思著社會需要的“類型”女性等等,都是比較鮮明的批判觀點。在《女性主義批評》中,對西方女性主義電影理論誕生闡述如下:
……作為一個同樣在后結構主義氛圍下誕生的,電影理論批評流派,女性主義電影理論批評擁有激進的批判性立場和高度綜合的方法論基礎;它從好萊塢經典電影入手,運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雅克·拉康的“鏡像階段”理論、雅克·德里達的結構思想以及米歇爾·福柯有關的“權利話語”的陳述,試圖公開揭露父權制度下女性被壓抑的事實和特點,結構和顛覆父權制和男性為中心的電影敘事機制……
雖然李先生先有一章節專門寫《意識形態批評》,但上引文中提到了弗洛伊德、拉康、德里達以及福柯,卻沒有提及阿爾杜塞。而阿爾杜塞的社會意識形態批判理論,導致格萊德希爾對編碼規則和解碼規則做了區分,從而提出“為什么女性沒有作為女性在電影中表現”,以及“這種非現實主義的電影為什么如此吸引受眾”等命題。“阿爾杜塞對主體與制度之間的意識形態關系提出的主張認為,制度將自己的觀點強加給主體,主體則在社會制度給予她的映像中逐漸認知自己。”女性主義電影批評,要批判男性中心主義,就是要對抗父權制意識形態,對抗父權制意識形態就一定要批判到現行的男權中心的政治制度,與制度對抗,就不能放棄激進的批判姿態。像李道新先生這樣有權威的電影史論家,在女性主義電影批評中對阿爾杜塞忽略不提,可見,激進的批判姿態不僅是因為沒有“女權運動”,更多的是因為對政治意識形態批判的放棄。由此,不難理解,女性主義的電影批評在中國,應該做得更好。然而直至今天,中國的女性主義批評理論的構建基本上還是圍繞著諸如“女性電影”“女性視覺”“女性意識”的界定、分類等作研究和探討。其不僅建構進度緩慢,批判深度也遠遠不夠。女性主義電影批評者遠嬰指出,近現代中國女性自我反思的意識和批判男子中心主義文化的沖動,不僅進步甚少,而且相對于歷史文化傳統中一直具有的女性意識,是大大地被現狀削弱了。
在女性主義電影批評理論的建構過程中,不僅批評者缺少了女性主義者激進的批評姿態,女性電影作品也是千呼萬喚“難”出來。相當前衛的女性主義電影批評人戴錦華女士就為“不可見”的女性電影表示憂慮和期待。
二、迷失的女性電影作品
遠嬰在《女權主義與中國女性電影》中介紹了西方的女性主義及電影理論,并且對比分析了中國的女性解放的狀況。作者認為,與西方相比,中國的女性研究落后很多。在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中一直有一個女性意識的生成線索,反而是近現代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的社會化特征和男性傾向大大削弱了女性自我反思的意識和批判男子中心主義文化的沖動。女性盲目地把男人當成衡量自身價值的標準。文章分析了較早時期的女導演董克娜、王蘋的影片中的女性,指出她們都是當時男性精神的縮影。女導演以男性的標準來描述和謳歌女性人物。
王春蓉、蒲若梅在《女性電影和女性電影批評》中用“女性視覺”和“女性意識”兩個概念,圈劃出“男”導
演拍攝的影片中女性形象的“非女性電影”特質。
戴錦華的《不可見的女性:當代中國電影中的女性與女性的電影》在女性導演及其創作影片的梳理與分析過程中表白“在中國當代‘女性的電影里,可稱得上‘女性電影的影片,如果不是‘絕無僅有,至少也是‘鳳毛麟角的。”
總之,中國的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工作者感受到了一個悲劇:中國的女性電影實在是匱乏!就是被戴錦華稱為“可以算得上真正的女性電影”的影片《人、鬼、情》,片中女武生秋蕓有自我意識,卻一定要初戀挫敗,婚姻中幸福無望。假設社會接受了男權與女權平等,女性主義在影片中足夠徹底,丈夫對在藝術上能干的妻子(秋蕓)也可以欣然接受,體貼關懷,建構和諧美滿的生活(在這沒有絲毫認為影片故事該如何拍的意思)。“真正的女性影片”《人、鬼、情》中女性主義者有女性遺憾,似乎就不可責怪“女性影片”迷失了該有的女性主義特質了。
與此同時,權威的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創作者(如遠嬰,戴錦華)對“女性電影”的界定和批評電影創作實踐的女性形象的觀點等,鋪天蓋地地影響著后來的女性主義影評人。如方云端同樣認為“……女性主義電影批評在傳統思想的影響下,卻因缺少西方女權主義運動的激進姿態,顯得趨于溫和。”金梅和李琳各自論文中的女性電影的界定也有復述式的觀點……這些因素嚴重影響了女性話語系統的建構。我們該思考如何建構女性話語系統了。
三、建構女性話語體系
中國女性主義電影理論批評的深度和廣度表現出了局限性,批評的女性話語本身也沒有形成系統性。從幾十年來對西方女性主義電影理論的引進,如勞拉·穆爾維的論文《視覺快感與敘事性電影》(周傳基譯)、李奕明《電影中的女權主義:一種立場,一種方法——對勞拉·穆爾維文章的介紹》、丘靜美(港)《西方女權電影理論與批評:介紹與分析》、郭培筠的《西方女性主義電影理論述評》等等,我們可以看出,批評過程對西方女性主義和電影理論有一定的認識和研究,但對西方話語依然表現出一定程序上的隔膜與不接受。中國對影片的女性主義批判。也以解構男性話語為主,而對于如何建構強有力的女性話語,卻缺乏建設性的理論。
從國內女性主義電影理論建構現狀來講,建構女性話語系統是一項迫在眉睫的任務。
策略之一:女性主義電影批評的“女性意識”應不斷進展。女性渴望獲得生理和心理雙重解放的欲求是個牽涉到歷史、階級斗爭、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運動過程。只有女性獨立自主的個體意識得到升華,才能爭取到人權平等,為完成女性話語系統的建構提供可能性。為此,女性意識最后應成為全社會認同和行動的事跡。
策略之二:提倡激進的女性主義批判姿態。尼克·布朗指出“為深化這一理論(女性主義理論)闡述,必須進一步塑造出主體身份的經濟力量和社會力量,后者尤為重要。”如果說有那么一天謝晉導演的影片中塑造的“完美女性”是神而不是人,或者張藝謀導演的影片中那些始終逃不出屈從男權的“倔強”女性形象,會在角色上置換身份,那么女權思想一定成為了一股社會力量。激進的女性主義批評能使社會人更深刻認識到男權中心的制度,促進社會性別平等,從而建設更具和諧的人類社會。
策略之三:呼吁各層電影人大量創作女性主義電影作品。自《昆侖山上一棵草》之后,雖有黃蜀芹的《人、鬼、情》、張暖忻的《沙鷗》《青春祭》、徐靜蕾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以及工黑的《玉觀音》等等影片,探討了比較嚴肅的女性問題,顯示出“解構”女性在社會象征秩序中的“他者”地位,而女性話語如何建構?女性主義將走向何方?影片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在這兩個方面依然是一片迷茫。電影人應該不斷地賦予女性電影作品中的女性,以一片生機式的享用性別平等權利,盡可能地創新角色本我形象。讓我們期待成為一股社會力量的“女性形象”誕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