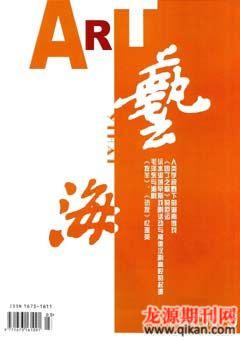戲劇表演中主、配角的關系
朱 米
在戲劇界有這樣一句行話:“紅花須得綠葉配”。準確地闡述了戲劇表演中主、配角的關系。“一花獨放不是春,萬紫千紅春滿園”。也就是說在今天或過去的舞臺上,無論是一臺戲,一個片段,一個折子,都有明確的主角與配角,主唱與幫腔。試想如果沒有這樣的對比關系,舞臺上會是什么局面呢?該揚的揚不起來,該抑的抑不下去,雜亂無章。那樣,就形成不了節奏,產生不了對比,突出不了主題,也就無法達到創作者的最終目的。因此,紅花與綠葉的辨證關系在戲劇表演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如果處理不當,就會出現“搶戲”的現象。如我院排演的歷史劇《白兔記》三娘與二娘岳氏就是一個對立的矛盾體。三娘、二娘同生活在唐五代的歷史時期,在她們身上都十分鮮明地打著封建時代被壓迫婦女深深的印記,也都擁有廣大中華婦女共有的優點,如吃苦耐勞、忍辱負重、賢惠善良等等。三娘、二娘都吃了無數的苦,就吃苦而言,三娘的苦是大眾化的,二娘的苦是個性化的。在觀眾感覺中三娘所吃的苦,能夠代表他們,在許多文學作品中三娘所吃的苦隨處可見。過去的貧苦百姓遭受三娘之苦,是帶有普遍性的。而二娘不同,她所吃的苦帶著一種包裝,有一種華麗的外殼,許多人不覺得她苦。其實不然,請看白兔記第四場“接子”這場戲中二娘的苦也吃到了頭,“新婚、父死、夫去遠征、新婚別離、思親念親苦熬度日”表白為拜相封候無所謂,而只想“白頭廝守”。突然得知劉志遠原有一子,驚悸、不解、又氣、又急、又羞、又恨、又怨、又愁,只怪為什么他沒有對她講實話,無奈當中愿將小孩送回家鄉。后聽老仆人杜忠將身世痛訴,先是心中不安,接著是同情,再是喚起母性良知,“緣何骨肉輕情意”,天性之門頓開,人性、母性的自然流露。二娘,作為母性的偉大形象豁然站立起來,使觀眾自嘆、感慨。以后二娘不僅接受了孩子,還為孩子找醫生、奶媽,為三娘認子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那么請看三娘、二娘,雖然結局都是“苦盡甜來”,她們所吃的苦卻是不同的。因此在人物的創作、設計過程中切忌雷同。用同一種苦的感覺,去創作不同背景,不同的生活環境,不同的人物,那樣就會失敗。從劇情上看,李三娘無疑是主角,是貫穿整劇的核心人物,而二娘這個人物在劇中的份量確實不可低估,雖然她出場的戲不多。
寫到這里我的腦海里閃現了幾組這樣的鏡頭,老舍先生的《茶館》被北京人藝改編成了話劇,久演不衰。記得一百場的紀念演出,我有幸在首都劇場觀看了藝術家們的精彩表演。全劇結束后,大家久久不愿離去。但這場演出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于是之扮演的王利發,也不是鄭榕扮演的常四爺,而是只有幾句臺詞的表演藝術家黃宗珞老師,尤其是他被捕快拿去,臨走時丟給觀眾的一句臺詞,震耳欲聾:“請招呼好我那只黃鳥。”幾十年的表演精華集中在這句臺詞上,集中在一個眼神,一舉手,一抬足,使觀眾記憶猶新。再就是觀看了陳凱歌導演的《霸王別姬》,極具個性的葛優飾演了一個變態的政客加戲迷于一身的角色。印象最深的就是葛優被判了刑,在公判大會會場,押他下去的一瞬間,葛優的表演爐火純青了,只見他腿一歪,來了個戲曲臺步,使觀眾眼前一亮,“臨死還忘不了這愛好”。例舉三例,不足以說明在戲劇表演中,紅花與綠葉的關系,但足以說明只有大舞臺沒有小角色。記得大藝術家金乃千在體驗屈原當時受辱的感受時,在暴雨中沖淋,在烈日下暴曬,讓他人騎在自己身上,以獲得真實的感覺。
“紅花須得綠葉配”,這樣的辯證關系是互相依存和相互對應的矛盾體,紅花須綠葉的陪襯,綠葉須紅花的點綴,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記不得是哪位戲劇大師說過“只有大戲劇,沒有小角色”。我認為,只要在舞臺上,不管這舞臺是農村搭的草臺,還是工廠的露天舞臺或是豪華的劇場,演員都要如同士兵沖上戰場,醫生上了手術臺了一樣,均是生死攸關,同樣的重要。
責任編輯:楊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