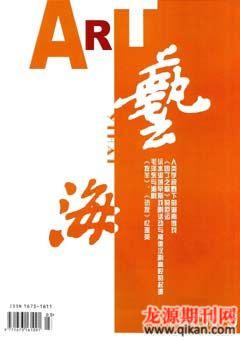毛澤東與湘劇
黎建明
“瀏陽河,彎過了九道灣,五十里水路到湘江。江邊有個湘潭縣,出了個毛主席,世界把名揚,咿呀咿吱喂。”這首瑯瑯上口而親切的湖南民歌,唱出了人民對偉人的心聲。毛主席雖然去世已經三十二個年頭了,但他的豐功偉績,人民世代相傳,永遠懷念。
毛主席愛好甚廣,喜歡戲曲,特別是對家鄉的湘劇更是情有獨鐘。這可能是鄉情關系,但湘劇前輩藝術家在表演藝術方面,確有與眾不同的造詣,因此受到毛主席的喜歡,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毛主席究竟看過多少次湘劇演出(包括電視錄像),筆者雖系親身參與,也很難說出一個準確次數,不過有幾次特殊的演出,可向讀者予以簡介。
毛主席三看《回窯》而不厭
《回窯》即湘劇傳統彈腔劇目《打雁回窯》,毛主席曾經三次看過演出。第一次是1956年7月9號晚上,當時湖南省湘劇團第一次參加全國戲曲巡回演出,經武漢、鄭州、石家莊、保定等地巡演,6月5號到達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到北京最大的愿望是想到中南海為黨中央和毛主席演出,展現古老的湘劇藝術形式。大伙一直盼望這一天的到來。在我們即將告別北京演出的頭一天,即7月9號,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團今晚到中南海向中央首長匯報演出。這一消息傳開,全團頓時就像開了鍋的熱水,沸騰起來。當天下午5點吃飯,5點半上車,5點45到達中南海懷仁堂,各部門認真地準備,當時鐘快到7點半的時候,懷仁堂內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大家知道是毛主席來了。見到毛主席,我們心情激動地跳躍著,個個臉色緋紅;口里雖未喊毛主席萬歲,每個人內心里都在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當晚演出的節目,第一折是《小將軍打獵》,由訓練班的小演員項漢演劉承佑、李自然演李三娘;第二折是《打雁回窯》,由彭俐儂演柳迎春、楊福鵬演薛仁貴;第三折是《轅門斬子》,由劉春泉演楊延昭、熊云欽演佘太君、吳淑巖演趙德芳、黃福明演楊宗保、莊麗君演穆桂英、賀華元演焦贊、蔣華金演孟良。演出過程中,我們窺見主席看得認真,毛主席時而鼓掌為演員們助興。這是建國后毛主席第一次在北京懷仁堂看湘劇,也是我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
毛主席第二次看湘劇《打雁回窯》,是1958年11月,當時黨中央在湖北武昌召開黨的八屆六中全會。湖南省委組織了以湘劇團為首的湖南藝術團赴武漢為大會服務演出。11月29號晚,我團在武昌的洪山賓館禮堂為毛主席演出。演出節目有《轅門斬子》和《打雁回窯》等,這是毛主席第二次看《打雁回窯》。六中全會期間我們為大會演出五個專場。
毛主席第三次看《打雁回窯》是1960年3月8號在湖南省委小禮堂,當晚演出有《斷橋》、《攔馬》和《打雁回窯》等。過了兩天,當時的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同志約了彭俐儂等幾位演員去見毛主席。毛主席和演員們親切地談起了湘劇《打雁回窯》。主席把唐朝確有薛仁貴其人,但不在正史而在野史的歷史情況向演員作了介紹,建議把薛仁貴射死兒子薛丁山這一節不近人情的戲能否改一下(不是原話,是大意)。這就是后來社會上流傳毛主席三看《回窯》而不厭的佳話。
為什么主席對《打雁回窯》如此青睞?我認為可能有如下幾點:一是他老人家為著革命事業,離家數十年,東奔西跑地過著行伍生活,但鄉音未改,仍是一口地地道道的湘潭話,因而懷著濃郁鄉情來看家鄉戲,倍覺格外親切。二是《打雁回窯》的故事情節動人,是一折反映一對患難夫妻的堅貞愛情的故事。薛仁貴與柳迎春是一對沖破封建勢力的愛情伴侶,婚后不久仁貴別妻投軍,丈夫走后帶著背生兒子薛丁山在寒窯苦渡光陰一十八載,一直到官居平遼王才回到寒窯與妻團圓,父子相會,此乃人間之美事也。三是《回窯》是一折表演難度較大的戲,演員之間靠內心活動和面部表情互相交流,尤以其中一段非常細膩的啞劇式的表演,既精彩又夸張,觀眾看了均感滿意。表現內容是仁貴回到寒窯后,柳迎春打水為丈夫洗滌路途之塵土。精彩的表演從此展開:當仁貴拿起洗臉巾往臉上擦洗之時,總覺得不對,有股濃烈的刺鼻氣味,發現是洗臉巾的氣味,為此仁貴使勁揉擦面巾,柳迎春在一旁著急,生怕丈夫把面巾搓爛;仁貴示意叫迎春換盆水再洗,結果還是氣味難聞,仁貴在著急時突然想到自己帶有洗臉用的面巾,當即取了投入臉盆,迎春一見急忙用手接住;待仁貴洗臉時不見剛才自己所投之面巾,問迎春是否看見,迎春把精美的面巾給仁貴看,示意這是做什么用的?仁貴示意這是我洗臉的面巾,迎春示意我穿的衣裳破舊不堪,這樣好的絲綢,我要留它做衣穿;仁貴笑著在迎春肩上輕輕地拍了一下,示意我如今做了大官,今后會有好衣裳穿;迎春仍然不舍,在仁貴的求討后才勉強將帕投入盆中,讓仁貴洗臉。這是一段趣味性很濃的情節,觀眾看了笑聲不止。
毛主席三看《轅門斬子》的故事
毛主席三看《轅門斬子》是一個意味深長而有趣的故事。本來毛主席只在1956年7月9號在北京中南海和1958年11月29號在湖北武昌的洪山賓館看了兩次湘劇《轅門斬子》的演出,不料時隔16年后又在長沙看了《轅門斬子》的錄像演出。
1974年10月毛主席回到湖南,住在省委接待處的“九所”六號樓。當時還是處于“文革”時期,沒有像文革以前那樣隆重為他老人家安排文藝活動,有關人員都集中在接待處等待任務。那時雖然沒有現場為主席直接演出,但演出和錄像仍然在繼續進行。錄好后的節目都送到六號樓播放。在此期間,有一位應中國政府邀請來華訪問的貴賓到達北京,經中央安排請這位貴賓到長沙與毛主席見面。幾天后的一個下午,我們正在看京劇的錄像片,突然工作人員通知,說毛主席今天下午要在六號樓接見外賓,要以家鄉的湘劇招待客人。工作人員忙把早已錄制好的湘劇《打獵回書》和《轅門斬子》送到六號樓。據在場工作人員說,那天毛主席精神特別好,一邊和外賓交談,一邊聚精會神地看錄像劇目;當屏幕上出現精彩畫面時,主席一邊抽煙點頭,并用手在自己的腿上輕輕拍打,為某一段精彩唱段入神而打板。事后從報紙上才知道那天主席接見的外賓是馬耳他政府總理明托夫。這次雖然是看的錄像演出,但比以往看有不同的反響。在1975年的某次高干會議上還專門向干部們敘述了《轅門斬子》的故事情節。1975年正是“文革”晚期,其中有不少高干子女參與其中,所以毛主席以《轅門斬子》的故事,語重心長地提醒和告誡高干們加強對自己子女的教育。毛主席的這次講話后來在各單位都做了傳達,我記得在當年的內參里也有報道。
毛主席聽高腔《沁園春·雪》的演唱
《沁園春·雪》是毛主席于1936年2月所作的一首氣壯山河的詩篇。在國人中廣為流傳。1945年毛主席赴山城重慶與蔣介石和談之時,此作經新華日報發表之后,當時在重慶引起了教育界、文藝界的巨大轟動。蔣介石對此反應很大,并不惜代價聘請一批墨客騷人,企圖撰文來壓制《沁園春·雪》的巨大影響,結果徒勞無益,只得銷聲匿跡地甘拜下風。
主席的這篇光輝詩作,建國以后很少有人譜曲演唱,戲曲方面就更加少有。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春節期間,湘劇表演藝術大師,人稱“高腔大王”的徐紹清先生,懷著對毛主席的忠誠和敬仰之心,想以自己的藝術才華和智慧,用湘劇高腔中最美的旋律來編唱毛主席詩詞《沁園春·雪》,這在當時不僅是湘劇史上的首創,而且在全國劇壇上也較為罕見。徐先生憑著滿腔熱血,冥思苦想地進行創作。首先在選曲方面,立意精巧,思考縝密。幾經修改,終于成此絕唱,流傳至今,仍然受到聽眾的喜愛。
1962年3月中旬,毛主席回到湖南在省委接待處的九所小禮堂,曾親聆徐紹清先生演唱的湘劇高腔《沁園春·雪》。主席聽后非常高興地對徐說,謝謝你為我的小作而高唱。作為《沁園春·雪》演唱時的司鼓者,我離主席很近,所以主席說的話,我聽得十分清晰。記得當時主席說話時語氣謙和而親切,不是以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身份,而是以一個普通的詞作者的身份來向這位為自己詩詞而歌唱的勞動者致謝。徐紹清確實唱得聲情并茂,獲得了主席的贊美。這體現了主席平易近人的偉大之處。
主席看湘劇演出可分為兩個時間段。1956年7月9號至1962年6月16號為第一階段,其中包括幾個重要的活動。如1958年11月黨中央在湖北武昌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195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到北京參加慶典演出,這期間都是直接為他老人家現場演出。
第二個階段是1974年底和1976年的上半年。當時處于文革時期,由于年齡關系,主席的身體狀況也日漸虛弱,不方便到現場看戲了,都是看演出錄像。尤其是1976年周總理辭世,對主席的打擊十分大,黨中央為了主席的身心健康,便通知湖南省委組織幾個毛主席愛看的地方劇種,如湘劇、花鼓、京劇和邵陽花鼓戲等,組織演出錄像,錄好后立即飛送中南海。我們從1976年元月進入省委接待處開始排練演出,到7月底才結束此項任務。幾個劇種錄制了大大小小共七十余個折子戲,都是主席平常愛看的劇目。
毛主席不僅喜歡看湘劇表演,對部分湘劇演員也非常熟悉。有的演員年齡較小,主席連他們的乳名都叫得出。如湘劇表演藝術家彭俐儂,主席知道她的乳名叫三伢子,劉春泉除藝名六歲紅外,主席還知道她的乳名叫春伢子。更有趣的是,當時湖南省湘劇院有兩個姓左的演員,大一些的叫左白翼,小點的叫左大玢,主席為了招呼方便,便將二人分別稱為大左和小左。就像一個慈祥的長輩呼喚自己的后輩一樣,既親切又隨和,體現了主席對新文藝工作者的關懷和愛護。主席與湘劇有緣,對家鄉的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作為湘劇人,我們永遠敬仰主席,懷念主席。
責任編輯: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