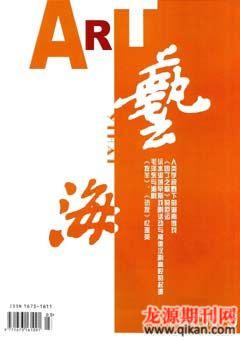“紙新娘”與我的創作歷程
我對古典主義油畫情有獨鐘,其所以如此,可能是如同支宇博士在《紙性真實,易碎人生》中所說的:“曾傳興在早期藝術生涯中恪守著古典主義嚴謹的視覺語言體系和崇尚‘真實的審美趣味:深厚的素描功底、精確的造型能力、逼真的具像摹寫,以及鄉土民族的題材領域和人性人情的人道主義情懷。”這可以理解為,不僅在研究的對象上得到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的結果上得到情感的滿足,從而產生一種動心、怡情、養性的精神效應。這些年來,我在系統強化了自己的寫實主義繪畫語言體系,深刻領悟古典主義關于“真實”的審美理想的同時,把自己的個性完全融化在普遍性之中, 投入更為新鮮的個人生存經驗和美學趣味,并對當代中國古典主義繪畫史進行了綜合的考量。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靳尚誼先生創作了《塔吉克新娘》,將視角從政治轉向了普通的人和現實生活,開始了他的中國油畫寫實風格的轉折。相對于當時占主流地位的“社會現實主義”革命歷史畫的表現手法,靳尚誼先生這種強調對傳統的尊重,對和諧、比例、色彩、結構等造型語言的追求,對人的理想美的贊頌的所謂“新古典主義”畫風,在中國油畫的現代化進程中,意味著一場悄悄的革命。當時,我少不更事,不知天高地厚,僅僅根據一些膚淺的知識和幼稚的認識對前輩藝術家的這場悄悄的革命妄加評論,私下議論靳尚誼先生畫風有達芬奇的形體造型,委拉斯凱茲的用筆敷色,倫勃朗的細節描寫,維米爾的畫面意境。而自己,作為一個晚生代,卻面臨著一個究竟如何選擇的難題。盡管如此,這些年來,我對靳尚誼先生各個時期的作品,還是懷著無限崇拜景仰尊敬的心情來欣賞、解讀,學術態度十分嚴謹。對于靳尚誼先生那場悄悄的革命的意義,后來我也有了一個全面的認識。
我個人的觀點是,在中國油畫的現代化進程中,藝術家們,人人都有所繼承,人人都有所創新,但是創新是有層次之分的,有的人只是作了某些點點滴滴的量的積累,有的人確是引起了質的飛躍,以至開辟了一個新時代。靳尚誼先生的創新就屬于后一種類型。這是一種全面的創新,改變了他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在中國油畫的現代化進程中是一個承先啟后的重要環節。正是在靳尚誼先生的并非耳提面命而是潛移默化的引導下,使我走進了古典主義油畫的世界來尋求屬于我自己的理智的了解和情感的滿足,并且連帶著對那些中國當代新古典主義油畫的后起之秀如楊飛云、王沂東、王玉琦、陳逸飛、艾軒等也產生了一種無限崇拜景仰尊敬的心情。我根據自己審慎的比較鑒別,對這些畫家逐個研究,擇善而從。今天看起來,當時我實際上是在不自覺地去承接他們的思想和風格,承接他們的文化智慧。這與當時風靡全國的“85”新潮美術的觀念并不相同,也許是作為一個晚生代,時間的距離排除了許多主觀因素的干擾,使我作出了實際上是一種自覺的選擇,深思熟慮的決斷。靳尚誼、楊飛云、王沂東等中國藝術家的傳統思想、文化智慧和優秀作品像磁石一樣吸引著我,其中沒有文化的傲慢和霸權話語,沒有家法師法和學派偏見,沒有不容許有絲毫的懷疑和必須遵循的定論,而是洋溢著一種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開放的心態,特別是凝聚著一種對傳統文化智慧的執著,對繼承與創新的不懈追求,所有這些,都體現了這些中國藝術家的傳統思想和文化智慧,在我年幼無知的心靈里播下了一顆無聲無形說不清道不明的文化種子。時隔多年回憶這些往事,一切都變得依稀仿佛,如夢如煙,但是唯有這顆文化種子以及對古典主義油畫的鐘愛始終未能忘懷,隨著時間的推移,年齡的增長,古典主義油畫的世界成了我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
這十幾年來,我創作了《佤女》、《稻草人》、《來客》等作品,特別是近幾年的“紙新娘”系列,是在中國的語境之下,對古典主義油畫傳統的繼承,絕非自身孤立的創作過程。這些創作的語言體系是寫實主義的語言體系,語言的基礎是比例、結構、明暗和透視,對象是人。寫實主義的語言體系反映了傳統社會的文化特征,寫實是一種審美理念,一種美的規定性。為了在繪畫中追求寫實,我做了許多的人體解剖,對結構分析、透視原理、光影變化等等進行了長期深入的科學研究,并畫了無數的素描稿子,精準的造型能力,逼真的具象摹寫,忠實的程度不但到家,甚至于過分。同時, 我深刻的體會到,藝術的本質是主體意識的個性,藝術的最高境界是社會和時代的個性化顯現。主體意識的的個性是藝術家先天的可能性通過個體人生際遇對社會與時代的消化和互動并被記錄在藝術作品中。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藝術家都有自己顯示個性的方式。藝術的個性是開放的,在藝術作品中,造型、構圖、色彩、筆觸、質感、光影等等都是藝術家顯現個性的方面,甚至題材的選擇也顯現出藝術家的個性。同時,我嚴格把握了美術創作的認知方向,對自由、文化、知識、圖符等美術創作的認知要素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自由是一種存在于個人而又超越個人之上的精神力量。對于個人而言,自由精神表現出一種對既成審美秩序和審美規劃的超越。它可以是對集體審美秩序和審美規劃的超越,也可以是對他人,對自我的超越。對人類文化而言,自由精神表現出一種永恒的開放性。從虛無到有限,從有限到無限。它可以是從題材的規定到規定的突破,也可以是從形式語言的建構到完美再到對完美的突破,還可以是從媒材形態到選擇的完善,再到媒材形態的革命等。只有對自由的永恒追求,人類藝術史的完整性才能得到合理的認知。
文化是一種生存方式,畫家應該是文化的載體。美術作品只有在文化即存在方式的境況下,其作用和意義才得以顯現。在文化與美術文本之間不僅存在著必然的因果關系,而且文化的存在方式更為復雜。美術也是一個獨立的知識體系。美術的知識來源于人類對文本的認識。沒有種種關于美術認識形成的知識,美術作品將變得毫無意義。圖符一詞的概念在突破語言學的束縛而謀求哲學的身份時就具有了某種文明創造形式的普遍性。作為一種視覺文化形態,將圖符作為認知美術的基本概念有更大的隨意性和自由性。美術作品如果不具備圖符的基本特征,就和一個批量生產的產品沒有區別。
就“紙新娘”系列的創作而言,創作方法雖然是具象寫實,但創作思維完全是帶著自己對歷史和現實的真切感受全身心的投入。圍繞著創作主題的各種看法,與其說是對客觀世界的一種冷靜思考,毋寧說是對美好理想的一種熱情的追求。既是獨立思考和理性的判斷,又是“使氣以命詩”,直抒胸臆。“紙新娘”創作的主題思想不是塑造典型性格或者交代具體情節,形象的社會歷史特征也不確定。創作的主題思想是在于張顯自我意識的個性,這種個性是自己的全部感情、期望、生活經驗、價值理想以及對時代的特殊感受。
主題思想和主題思想的內容是“紙新娘”的核心主體。“紙新娘”是自我意識所依賴的客體,借“紙新娘”,圍繞主題思想和主題思想的內容,把自我意識提升到一種關于價值理想的悖論與人的整個生存方式緊密相連的精神境界。一方面,“紙新娘”是真實的存在嗎?這純屬一個似真而假,似假而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自相纏繞,自相矛盾,兩解而又無解的悖論。如果把它看成是一種邏輯的悖論,概念系統的悖論,這只不過是邏輯的陷阱,文字游戲。但如果站在側重于探討與人的政治倫理實踐行為緊密相連的人世關懷的角度,切合人們普遍存在的憂患意識和人生追求,它可以成為一種關于價值理想的悖論,人的整個生存方式的悖論,植根于人性本質之中的悖論。由于悖論本質上是無解的,但可以根據時代的需要和自身的處境作出一種價值選擇,宏揚一種價值理想。另一方面,自我意識是一個主體范疇,主體如果不以某個客體為依據,是無法成立的,所以自我意識不能停留于自身,而必須趨向于客體。精神境界是主客合一的產物,自我意識經過一番求索,終于找到某個客體而安息于其中。這種自我是與時代緊密相連的,通過把認識和感受、思維和情感融為一體,通過自我意識中的獨特的個性去把握時代的共性,把時代的某種困惑轉化為自我的深刻認識和切身感受,由此所抒發的心聲,所表現的追求,也就具有了時代的精神。“紙新娘”正是自我意識所依賴的客體。借“紙新娘”,我把自我意識提升到一種關于價值理想的悖論與人的整個生存方式緊密相連的精神境界,給世界點燃一盞理想的光。
“紙新娘”所引發的是理想與現實、事實與價值的對立所產生的生活本身的悖論。在現實生活中,只有在理想與現實、事實與價值之間進行雙向的調整,一方面改造個人心態使之適應社會環境,另一方面改造社會環境使之適應個人心態,來選擇一種以和諧自由為目標的價值取向。也就是說“紙新娘”的這種價值取向包含了“跡”與“所以跡”兩個矛盾的方面,就其表面的形跡而言,“紙性真實,易碎人生”,是拍浮酒船了此一生的感嘆,是以郁悶無奈、彷徨無依、內心分裂為心理背景,是個苦物。
就其“所以跡”而言,“紙新娘”代表了人們對新的精神支柱和美好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堅持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諧自由的價值理想,熱切地呼喚著人們真正的理解,它構成了一種慷慨悲涼的風格主題,所謂悲涼,是由于感受到了這種悖論的悲苦的一面,表現出對現實生活的某種困惑和無奈,力求尋找一條精神的出路。所謂慷慨,表現了對和諧自由的價值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只是這種追求不是從一廂情愿的理想出發,而是立足于現實的土壤。當理想與現實的沖突不可調和,事實與價值產生了嚴重的背離,人們往往把外在世界的分裂還原給內心世界,并且極力探索一種安生立命之道恢復內心的寧靜,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盡量解決矛盾,將苦物化為甜物,讓自我意識在這一過程中得到安息。正如黑格爾說的:“在現在的十字架中去認識薔薇的理性,并對現在感到樂觀,這種理性的洞察,會使我們跟現實調和。”這種以和諧自由為目標的價值取向,是人類社會文化發展史中,人們不約而同共同探索的一個主題。“紙新娘”以一種慷慨悲涼的姿態充當了和諧自由的天使。
雖然“紙新娘”系列作品創作的真意被刻意隱諱,但其“境外之境”、“象外之象”的邏輯線索,還是可以感覺得到的。稱這些作品為當代具象繪畫比稱它們為古典寫實主義繪畫更確切。 我想,“紙新娘”系列作品以及在創作過程中的心路歷程,能給學術界提供一些思考的材料,當然還有許多不足之處,希望得到更多指正。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
責任編輯:蔣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