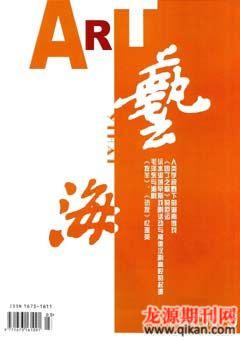《牧羊》、《訪友》憶蓮英
林 一
1954年-1955年,長沙市民眾花鼓戲劇團在中山路上演大型花鼓戲《八百里洞庭》,戲好、演員唱功好、做功好,引起陣陣轟動。城區居民奔走相告:除胡華松、張漢卿這些名角外、又出了個新演員謝蓮英。湘江沿岸,上至坪塘、暮云市,下到銅官、靖港,不少農民、漁民劃著船來看戲。晚黑邊,中山路碼頭多泊了一片船,都是來看《八百里洞庭》的。
古老的花鼓戲劇目中有出《牧羊下海》,戲中有一段打儺腔[十二月放羊]。這首順口而歌、不用管弦的民歌,在洞庭湖區流傳甚廣,幾乎婦孺皆知。《牧羊下海》劇中的女主角,是龍王敖廣的女兒,戲中稱她為三公主;只因失手打碎寶瓶,被貶到湖濱卿家為奴,卿公子納以為妻。小姑不賢,刁唆婆母折磨她,被逐到湖西牧羊。書生柳云英路過憐之,為她捎血書至東海。龍王派性格暴燥的弟弟領兵救她,一怒之下,龍尾掃出一個八百里洞庭湖來。獲救后的三公主,被許配給云英,夫婦二人奉龍王之命鎮守洞庭湖。這故事與唐人傳奇《柳毅傳書》相近,但劇中的情景、風俗習慣、語言、人情物理都洋溢著洞庭湖泥土的芳香。民眾花鼓戲劇團整理本,在傳統基礎上有揚棄、發展和創新,劇名叫《八百里洞庭》,更富傳奇色彩。尤其《牧羊下海》一場,舞臺上朔風呼嘯,雪絮飛揚;謝蓮英唱的[十二月放羊],一字一淚,一腔一泣,使不少觀眾淚水盈眶。
此時的謝蓮英二十歲剛出頭,學戲才幾年。她1932年出生在洞庭湖邊的沅江縣草尾。草尾是個水運碼頭,農民、漁民、船民都愛花鼓戲,常有戲班在草尾演出。謝蓮英和當地許多青少年一樣,耳濡目染,從小愛看愛唱花鼓調。沅江解放后,謝蓮英參加了當地的街道文藝宣傳隊。1950年文華花鼓戲班來演出,她拜龔福元為師學戲。開蒙戲是《玉堂春·大審》,先學會唱,然后學身法,動作。上臺試演,一炮打響,便參加文華班。1951年,她隨戲班——不久改成劇團在湖區流動演出;7月到了長沙。正好長沙市要舉行會演,他們排演了李煥章從呂劇改編來的《李二嫂改嫁》,受到好評。演李二嫂的謝蓮英被長沙市民眾花鼓戲劇團看中,她也看中了有何冬保、蔡教章、張漢卿、胡華松、姚悟卿、孫少云、楊福生等名角薈集的民眾花鼓戲劇團。從此,她成為長沙民眾花鼓戲劇團的一員。此時劇團收入不高,她的工資也低,還靠母親擺個小攤,搓紙煝、卷紙煙、繰襪底,接衣洗來維持生活。
到民眾劇團時,她學戲才五年多,劇目少,又沒有童年功底。她平日靦腆,說話有點口吃,但在學戲求師上她不靦腆,面對劇團里這么多名老藝人,這么多好師父,她公開說要當“公眾徒弟”。她也是這樣做的,尊敬每一位老藝人,虛心求教,不懂便問便學,學劇本、學臺步、學身法、學唱、學演技。和她同臺的老藝人,特別是常演對手戲的胡華松對她幫助最多。她只讀過兩年小學,對劇本、臺詞不僅不能全理解,有時字都不認得。她向老同志、向觀眾請教后,一字一句死摳硬記;身段不漂亮、圓場(臺步)不好,散戲后在房里對著鏡子練身段,圍著桌子跑圓場。有點閑暇,她會跑很遠路去找湘劇名演員彭俐儂、王福梅和省花鼓戲劇團的同行學水袖、學身段,學現代戲。那時長沙沒有公共汽車,她不會騎單車,坐不起人力車,全靠走路。說她認真,讀劇本認真,排演戲認真,化妝也認真。平常演出,她都提前到后臺,妝要花兩個小時。她說自己動作慢,其實是細致、認真、一絲不茍。為演《兩兄弟》、《姑嫂忙》等現代戲,她跑到鄰近居民家、效區農民家,觀察、體驗喂豬、推磨,回來不厭其煩地練,直到同臺演員認可,觀眾滿意。《八百里洞庭》在兩三年中演出近300場。謝蓮英的藝術得到磨煉提高,她的名聲也不脛而走。1955年冬天,她和何冬保、胡華松、李國文合作演出花鼓戲《中秋之夜》,獲得湖南第二屆戲曲會演演員一等獎。
謝蓮英藝術上的全面提高,是1956年夏天參加文化部在北京舉辦的全國第二期戲曲演員講習會。這期講習會上,不僅有張庚、羅合如、阿甲等專家講了戲曲藝術理論和演員道德、修養,還有梅蘭芳、程硯秋和川劇、越劇的許多名家,理論聯系實際,現身說法。講習會結業時,她和胡華松、保冬保、蕭重珪把學習的收獲,融化到自已的藝術里,合作演出《山伯訪友》。他們分別飾演祝英臺、梁山伯、四九、人心。花紅葉綠,相得益彰,得到專家的贊許,同行的肯定。他們把劇中人物的愛、怨、離、恨表現得絲絲入扣,淋漓盡致,聲情并茂。特別是劇的結尾,山伯第三次上馬時英臺不松馬韁,被山伯咬手失聲的細節,感人肺腑。難怪當時省文聯主席、作家康濯看了后題詩贈她:“泣會樓臺眾客哀,打神告廟萬家悲。蓮英永葆青春旺,花鼓長沙國譽輝。”(注:詩中“泣會樓臺”指花鼓戲《樓臺會》;“打神告廟”指花鼓戲《情探》)康濯還多次在談話和文章中,認為她刻畫人物深刻,表演具有湖南特色,符合農民想像。
《山伯訪友》又名《樓臺會》,是全本《梁祝》(湖南花鼓戲又稱《同窗記》)的一折。戲的開頭,梁山伯是在嗩吶聲中騎馬出場的,高亢跳躍的[梁山調]唱腔,配合奔馳的揮鞭舞蹈,四九挑書箱的急步和喘息,山伯訪友求婚的喜悅心情得到渲染。他知道所許婚的九妹就是英臺本人,更是喜上加喜。當得知英臺已被父母許婚與馬文才時,既責英臺失約,也怨自己來遲,捶胸頓足失態,幾次不避男女嫌,將英臺拉過來責問。英臺勸他“另配女裙釵”,他反復申明“天仙女下凡我不愛,山伯總總只愛祝英臺”。英臺被真情感動,表示“生不同衾死同穴”,將紅綾作為愛情信物交給山伯。山伯睹物傷情,吐血昏迷,英臺將紅綾扎在山伯額上,兩人痛哭告別。離別時山伯三次上馬:第一次由書童四九帶馬,山伯心酸上不去;第二次由丫環人心帶馬,又沒上去;第三次由英臺帶馬,英臺不忍看山伯心悲痛,背過臉去。愛極恨極的山伯,輕撫著英臺抖擻而不忍松韁的手,猛然低頭口咬英臺手腕。英臺被嚙松韁,失聲痛呼。山伯欲為撫傷,英臺報以眼神后,兩人抱頭痛哭。山伯騎上馬,跌跌撞撞下場,英臺用輕如游絲的聲音呼喚“梁兄”。此情此景,撕肝裂肺,觀眾怎不動容!梁山伯、祝英臺都是知書知典的人,這一咬有個典故,出于《左傳·莊公三十二年》,魯莊公愛大夫黨氏的女兒孟任,答應娶她,孟任于是割臂向莊公表示守信,后來便把男女相愛私下訂定的婚約稱為“嚙臂盟”或“割臂盟”。這一口咬,也為梁祝的殉情化蝶作了伏筆。
觀眾喜歡謝蓮英扮演的角色,還有秦香蓮、孟姜女、江姐、《張羽煮海》的龍女、《情探》的敫桂英、《盤夫索夫》的嚴蘭貞……。她演出向鐘宜淳學來的《姑嫂忙》,1956年在北京招待過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和黨的八大代表,受到周恩來等領導人的接見。1962年11月,應邀來長沙參加省三次文代會的田漢、安娥、鄭君里等看望老藝人時,曾到她家問寒問暖。就這么一個謝蓮英,文革中被打成“三名三高”、“黑線人物”打入牛棚,遭受批斗。1969年,她所在的長沙市花鼓戲劇團撤消,被下放到九龍服裝廠勞動,后又轉入人民印刷廠。工廠有不少干部和工人看過她的戲,知道她的為人,十分尊重她、照顧她,在印刷廠,只要她做裝訂工作,也不給她下定額。1979年,省市文藝界為一批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同志平反,其中就包括她。1983年,長沙市委分管組織和文化工作的副書記朱尚同、宣傳部長謝作孚,邀我一起到她家做思想工作,才使她回到闊別多年的劇團。回團后立即投身排練,和胡華松等一道,恢復停演十七年的《情探》,1983年10月6日起在青少年宮劇場連演半個多月,座無虛席。由于年齡日大、身體很差,她把精力轉向培養接班人。她帶的陳香云、鄭艷春等幾個徒弟,都有所成就,在市會演中獲獎。
2004年12月17日,謝蓮英病逝。文憶萱、尹伯康、金式和我,寫的挽聯是:“從藝歷艱辛,湖畔牧羊憐龍女;遺響成天籟,樓臺訪友憶蓮英。”
責任編輯: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