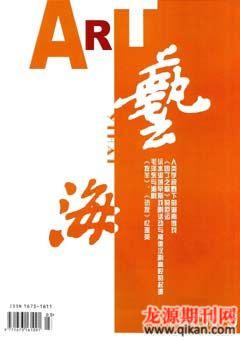線在繪畫作品中的呈現方式
李曉靜
線作為繪畫語言,是作品的外在結構形式。原始藝術中描繪形象的方式,大多是使用線條。線條同樣也用在中國國畫的線描和西方繪畫的素描里面。從造型的角度來看:原始藝術里的線,是依附具體形象的;寫生素描里的線,多具有輔助再現對象的功能。很顯然,線頭在各種繪畫中的運用,其呈現方式各有不同。
宋代畫家馬遠的《秋水廻波》,雖然有具體的描繪對象——水流,但水流的造型和排列是藝術家主觀意圖的表達,也就是說,它并不是以寫實作為第一目的。水流的波紋是弧形的,卻也是非常硬的,由排列的節奏產生流動感,線條有遠近、長短和虛實的變化,呈現一種平面上的空間感。作品產生的背后,應該是中國古代畫家對待藝術的態度,中國繪畫不提倡以寫實為最高標準,而是與創作者的人格聯系在一起,藝術作品里表達出一種對人格盡善盡美的追求,有“畫如其人”的觀點。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達芬奇的鉛筆手稿中,有一些是描繪類似風景和天氣變化的。這些繪畫手稿里面的線條是有虛實的,類似于寫實素描里用的線條,但卻相對地脫離了具體的形象。單從手稿呈現出來的直觀感受來看,同樣的,線條的虛實呈現出一種空間感,此外,線的硬度、形狀和氣質,傳達出來的感受是指向人的心理空間的。也許這是作者無意識的表達,正如史前巖畫上有許多動物的形象,造型使用的是一種質樸的線,傳達出一種古樸、單純和氣韻。
20世紀的畫家馬蒂斯和蒙克也極其偏愛使用線條。其中,馬蒂斯的線條是自由,不受具體形象的限制,更多的是呈現出一種自然的流暢,舒適和安逸,寧靜的流淌。他的線條同樣也是簡練和單純的,正如他在筆記里所說:我希望有一種均衡、純粹的藝術,這種藝術不煩擾人,也不使人不安;我希望一個疲憊的、傷心的、困憊的人,在我的畫面前享受到安寧和休息。而蒙克的線條,更多的是表現出一種不安的情緒和心靈。蒙克的作品《吶喊》里,線條是充滿涌動的,對具體的形象雖然有依附,但更多的是脫離了具體形象,直指藝術家內心的變化和情境,傳達出來的感受正如作品的題目,表現出人物內心的狂亂、恐懼和焦躁。其中,線條在作品里同樣有著層次上的變化,也就是說,每一處線條所承擔的都是藝術家的情緒。在畫面里,這樣的情緒所在之處,都有一個時間和空間上的布局。所以,整個作品看起來是豐富和富有變化的,是渾厚和完整的。在某種程度上,它所呈現的剛好是人的盡量完整的狀態。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畫家波洛克的作品中所呈現出的錯綜雜亂與有秩的線,更多的是源自他對待繪畫的理念,即線沒有任何具體的形,是屬于單純意義上的線。波洛克認為畫不是畫出來的,是自己產生的。畫是有生命之物,畫家只是讓它呈現出來。波洛克創作時,大多是把顏料直接滴灑在平放的畫布上。他說,現代藝術家生活在一個機器時代,我們有機器手段來逼真地描繪客觀對象,如相機、照片。在他看來,藝術家的工作是表現內在世界——換句話說——是表現活力、運動以及其它的內在力量。現代主義藝術家的著眼點是時間和空間,他表現情感,而不是圖解社會。波洛克曾經詳細介紹了其“滴畫”的創作方法,他的畫不是來自畫架,在作畫時他幾乎從不平展畫布,更喜歡把沒有繃緊的畫布掛在粗糙的墻上,或放在地板上,以利用粗糙的表面所產生的摩擦力。在地板上他反而覺得更自然些、更接近,更能成為畫的一部分,因為用這種方法作畫時可以繞著走,從四周工作,直接進入繪畫之中。這和西部印第安人創作沙畫的方法相似。進而,波洛克放棄畫家們通常用的工具,如畫架、調色板、畫筆等等。波洛克喜歡用短棒、修平刀、小刀、以及滴淌的顏料或攪和著沙子的厚重涂料、碎玻璃和其它與繪畫無關的東西。“一旦我進人繪畫,我意識不到我在畫什么。只有在完成以后,我才明白我做了什么。我不擔心產生變化、毀壞形象等等。因為繪畫有其自身的生命。我試圖讓它自然呈現。只有當我和繪畫分離時,結果才會很混亂。相反,一切都會變得很協調,輕松地涂抹、刮掉,繪畫就這樣自然地誕生了。”(埃倫·H·約翰遜編,姚宏翔等譯:《當代美國藝術家論藝術》)
塞·特沃布利的繪畫作品同樣也是把線作為單獨的線來運用的,雖然他作品中的線也是雜亂無章的,但是他不同于波洛克對待繪畫的方式。他的繪畫材料一般是蠟筆、鉛筆、油畫顏料,作品里出現的線條有時候像是筆跡,有時候像是數字、標記的符號,有時候像是草圖,反映出了藝術家在對線條使用的可能性和表達方式上的嘗試,同時也體現出了藝術家本人的氣質。他的作品《尼尼繪畫》(Ninis Painting),在淺藍色的背景上呈現出一些看起來雜亂,但卻很有層次的線條,有力度的舒緩的控制,像是要描述出某種狀態。有傳記作者認為,這些作品喚起了白天與黑夜之間的一種淡淡的海藍色,它漫漫地翻騰有如四季的變化,它們成就了一種罕見的永恒,表示了對藝術與生活矛盾的緩解與協調,如果沒有緩解與協調,藝術與生命也許將永久分離。
朱莉·梅雷圖的作品,從直觀上來看,呈現在眼前的是層層疊加的線,里面有直線、曲線,線的分布很明顯是按照某種思路來布局,像是傳達了某種信息或勾勒某個空間。她的作品《叛逆者的發現》,正如作品的名字,呈現出來的是某種可以辨認的空間。在畫面的最底層,所勾畫出來的線條是淡淡的,細線條和曲線比較多,看起來像是在描畫一些東西,并且由線組成一個個區域,有著精心的布局。前面幾層的線條,相對第一層多了很多的直線,這樣的直線類似于電腦制圖中矢量圖的線,逐層地變粗變實。在作品背后似乎有復雜的認識,而線在這里的使用,是一種被選擇的語言方式,也就是說,線是表達這種復雜心理認識的工具,同時也是承擔認識的載體。盡管這樣的敘述更多的是朝向藝術家本人,但是對于觀眾來說,仍然可以從里面體會出某種強烈的感受和信息。 羅伯特·威廉姆斯的帆布油畫作品里面的具體形象,主要是用線來勾畫的,但這樣的用線,不同于前面所說的依附于具體形象的線。他的形象勾畫更像是常見的城市連環畫,即作品里面出現的是城市、教會、異域,這與藝術家本人關心的問題有關系,也就是說,這是相對外化的普遍問題,所以他的作品中線所組成的形象并不十分帶有個人的特點和氣質,更多的像是某個連環畫畫報、電影插畫,或者廣告里的圖像,這在一定程度上或許也呼應了自杜尚以來藝術家對待現成品的態度。
上述幾位處于不同地域、不同歷史時期的藝術家的作品中,線的使用和呈現方式是不同的。他們使得線條這種簡單的繪畫語言變得復雜、深刻,這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藝術家本人的認識、認知、情感,以及其對待藝術的態度;另一方面,也展現了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域的藝術家的創作特點,以及他們創作中的某些相似性。
(作者單位:四川美術學院)
責任編輯:尹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