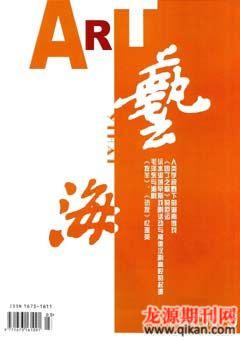騰沖民間情歌意象析
劉雅靜 王愛萍
騰沖,位于滇西邊陲,西部與緬甸毗鄰,歷史上曾是古西南絲綢之路的要沖,是著名的僑鄉、文化之邦和著名的翡翠集散地。西漢的騰沖被稱為滇越,故騰沖又有“騰越”之稱。在這片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土地上,聚居著勤勞善良的各族人民,他們團結奮進,共同鑄造著美好的生活,這其中最為活躍的應該是青年男女了。他們熱愛青春年華,向往美好健康的愛情生活,一顆火熱的心追求著理想的對象,誠摯鐘情,一往情深,不吐不快,不唱不開懷,于是便自然地熱情謳歌起來。“山歌無本句句真”,“姑娘的愛情,只能用心兒換取”。情歌就這樣從年青的心里唱出來,歌聲響徹騰越大地,廣泛流傳于民間,為人們所喜愛和吟唱,民間情歌成為扎根于人民大眾土壤里一朵鮮艷的奇葩。
騰沖青年男女是怎樣寄情于物、寄情于景的呢?
一、關于意象
簡單地說,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就是用來寄托主觀情思的客觀物象。意象理論在中國起源很早,《周易·系辭》已有“觀物取象”、“立象以盡意”之說。不過,《周易》之象是卦象,是符號,是以陽爻陰爻配合而成的試圖概括世間萬事萬物的六十四種符號,屬于哲學范疇。詩學借用并引申之,“立象以盡意”的原則未變,但詩中之“象”已不是卦象,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具體可感的物象。
在廣大民眾以口頭或書面形式廣泛傳承的民歌中,數量最多、內容最豐富的愛情民歌猶如大海彩貝,耀人眼目。而孕育其中的審美意象則更是異彩紛呈,是廣大青年男女至真至誠之情感,在剎那間碰撞出的愛情小精靈。民間情歌中的意象,不同于一般的文學意象,它是青年男女愛的萌發,是他們心靈深處激情的火花。因而物象是民歌文本的文化符號,情意是其靈魂與精髓。
騰沖,這座南方絲綢之路上的歷史名城,歷經滄桑,積淀了豐實深厚的歷史文化,邊陲古道的馬鈴聲,記錄著中、緬、印的商貿歷史;春秋戰國時期的銅案、銅鼓凝集著兩千多年悠久燦爛的文明;大自然似乎特別鐘情于這座邊陲古城,整個地貌就像一個天然的情歌臺。崇山峻嶺中依稀露出幾塊平地,到處綠樹成蔭,翠竹修茂,田間耕作的那些純樸農民,他們沒有什么文化水平,在唱山歌時卻能信手拈來。身旁隨意的事物即可成為他們情感的寄托,對這些紛繁復雜的情歌意象進行淺略的探討,有利于發覺情歌文本背后的意味,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蘊含其中的深層文化心理。
植物不僅有美麗迷人的外表,還有深刻的文化內涵。在漫長的人類文明歷史長河中,植物以其獨特的方式與人類進行著交流。花草樹木正是通過人們所賦予它們的象征意義,而融入到人們的生活中來。
二、 花中有情
我們中國人對花是情有獨鐘的,所謂“花開富貴”、“花好月圓”、“如花似玉”,多是基于對花的熱愛而產生的感嘆。騰沖民間情歌在抒發情感上也離不開對花的眷戀:
男:三月鮮花正在開,好久不見妹趕街,
今天來了見到你,笑個瞇眼睜不開。
女:三月鮮花正在開,好久不見哥趕街,
今天既然得見你,恩愛姊妹分不開。
陽春三月,春天是鮮花盛開的季節,也是年輕人思春的季節。看到鮮花開放,也就思念起情人來,當兩人見面后,男的“笑個瞇眼睜不開”,激動之情全都表現在臉上,而女方好不容易看到心中的他之后,也一改往日的矜持與羞澀,要和阿哥“恩愛姊妹分不開”了。同樣是在花開的季節還有這樣表達的:
男:走了一嶺又一山,二月江南梨花香,
青山綠水不留戀,只想小妹在眼前。
女:走了一嶺又一山,油菜開花遍地黃,
妹打紅傘路邊站,專等小郎到這方。
兩位有情人為了要相見,不怕路途遙遠,跋山涉水,聞到了“江南梨花香”,卻不留戀沿途美麗的風景,一心只想著要和小妹相見。然而小哥有情小妹更有意,在路邊遍地盛開的油菜花旁撐起一把與黃色形成鮮明對比的紅傘,只為小哥能一眼望見自己,那種急于相見的迫切溢于言表。
騰沖民間情歌這種將相思之情寄托于花的歌詞數不勝數,而將贊美之情寄托于鮮花的亦不少:
梔子花開白如霜,靈靈巧巧手一雙,
在家會煮十樣飯,下田會栽對行秧。
梔子花潔白如霜,高雅的香氣令人無法忽視她的存在。梔子花的花語是——“永恒的愛與約定”,不僅是愛情的寄予,平淡、持久、溫馨、脫俗的外表下,蘊涵的是美麗、堅韌、醇厚的生命本質。這里,阿哥不僅夸贊阿妹靈巧的雙手,同時也對她“在家會煮十樣飯,下田會栽對行秧”的能干給予了贊揚,為阿妹脫俗的外表所傾覆,并表達了他的愛慕之心,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感情抒發得很逼真。當然,阿哥慕情于阿妹,阿妹同樣也傾情于阿哥,在阿妹的心中,阿哥亦是那樣的可愛:
葡萄開花串串連,哥哥生得好齊全,
臉嘴紅紅逗妹愛,手桿粗粗會種田。
很少有人看到過葡萄開花,然而在這里,將阿哥的長相與葡萄花相比,證明了阿哥在阿妹心中的特別,表達了一種愛慕之情,感情真摯直接。
以花為媒是基諾族青年男女的婚姻戀愛的一大特點。女青年到了求偶年齡,母親便給自己的女兒縫制一套美麗的服裝,讓女兒去談情說愛。小伙子見到姑娘穿上這種特殊標志的服裝,也就知道可以去追求她了。青年男女可以對歌,但男青年不能直接向姑娘提出求愛,只能由姑娘向小伙子提出。當姑娘選中某個小伙子時,就準備一朵最美的鮮花,托自己的朋友轉交給那個小伙子,如果小伙子也鐘愛那姑娘,他收下鮮花之后,就可以直接找姑娘對歌,提出訂婚。然后向雙方父母公開他們的愛情,商訂結婚大事。在這里,男女戀愛不需要什么介紹人,更沒有媒人,傳情的媒介是一朵花,一朵寄托著對美好愛情向往的鮮花。
三、 樹上結情
在中國人心中,象征長壽的一則為龜,二則為樹。莊子在《逍遙游》中“嘆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贊龜與大椿的長壽。其實,我們不是追求有如神龜、椿樹的千年壽命,但我們應懂得生活的真諦。樹,亦可作為人的各種情感的精神依托,成為雁字回時的音信相通。故一樹可囊括壽命、生死、各種情感于一體,其所寄托的情思也可謂盡善了。騰沖民間情歌里,將情感寄托于樹的也有很多:
河邊楊柳河邊生,楊柳不怕水泡根,
真心實意我倆個,風吹雨打不變心。
楊柳,本是自然界的一種植物,但在中國古典詩歌中,卻有著獨特的意義,象征著離別、送行、相思、想念、懷舊、回顧、美人、述志等。在這首情歌里,河邊的一排排楊柳已經成蔭,我們能夠體會一對情人想要相會的情感,就像牛郎織女相會一樣的期待,感受一種相思之苦寄情于柳。而另外一首寄情于柏樹的相思之歌則是期待中帶有幾分羞澀:
我家門前柏樹多,手攀柏枝望小哥。
爹娘問我望哪樣? 數數柏枝有幾棵。
爹娘看“我”手攀柏枝站在家門前遠望時,想要問出“我”的心聲,但因羞于矜持,只告訴爹娘在數柏枝。柏樹莊重肅穆,且四季長青,歷嚴冬而不衰。《論語》贊曰:“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作者贊揚松柏的耐寒,來歌頌堅貞不屈的人格,形象鮮明,意境高遠。那么將柏樹置于愛情中考慮,柏樹則代表了愛情的堅貞,這首情歌中一句“數數柏枝有幾棵”,既表現出“我”的羞澀,又包含“我”在思念小哥的同時更想知道小哥對“我”的忠貞有多深!
竹與松、梅一起,素有“歲寒三友”之稱。竹枝桿挺拔修長,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四季青翠,凌霜傲雨,歷來倍受我國人民喜愛。人們通常一提到竹,就會把它和氣節相聯系起來,但在騰沖人民的心中,竹不僅可以表現高尚的氣節,還可以表現高尚的情操,借以抒發強烈的思想情感:
金竹串進苦竹園,
不知你家喲——
金竹可串苦竹根。
在騰沖民間流傳著一種說法:金竹與苦竹雖然同為竹類,但因苦竹根較長,金竹根較短,兩種竹生長在一起就會受到影響,用當地的話說就是“苦竹根趕著金竹根跑”,因此,金竹難以成活。于是騰沖民間產生了這樣的情歌,情歌中將男子比喻為金竹,將女子比喻為苦竹,情歌是由一個男子唱出的,開頭一句“金竹串進苦竹園”說明女子已有了心儀的男子,后兩句“不知你家喲,金竹可串苦竹根”既有惋惜之意,又有埋怨之情。
四、草中生情
“草”作為意象,在許多詩詞里都有出現。“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這是一首膾炙人口的名曲。它以悠揚而低回的曲調和動人的曲詞曾撩撥了多少人的心緒,催生了多少人的惆悵,喚醒了多少人藏于心底的真情!還如:漢樂府《飲馬長城窟行》:“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古詩十九首》之二:“青青河畔草,郁郁園中柳”;唐李白《灞陵行送別》:“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無花之古樹,下有傷心之春草”;等等,這些都是膾炙人口的名句。
騰沖民間情歌作為民間口頭文學中的一類,在詞藻上無法象這些名句那樣的華麗,在意義上也沒有較深的內涵,但它卻直接表達了一種真情。他們對生活中的事物都飽含深厚的感情,如秧苗、蘿卜、生姜、辣子等。他們以喜聞樂見的事物為情感的觸發點,順手拈來,借以表達自己的情感。有一首歌是這樣唱的:
男:大田栽秧稗子多,拔開稗子長苗棵,
苗棵發黃需要水,小妹長大需找哥。
女:大田栽秧稗子多,拔開稗子長苗棵,
小妹無心拔稗子,時時抬頭望著哥。
男女雙方均以“大田栽秧稗子多”起興,小伙子先是說明苗棵發黃了需要水來澆灌,從而引發出對小妹的情意,含蓄的向小妹表達了愛意。而小妹的心也被情哥的愛意傳達打亂了,已經“無心拔稗子”,以至于“時時抬頭望著哥”,郎有情,妹有意,兩情相悅,甚是感人。
愛情美好但不完美,“世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相愛中的兩個人性格總有不合之時,戀愛的路上總會有磕磕碰碰,唱情歌不僅可以唱出對心上人的愛意,也可以唱出對心上人的不滿:
辣子辣嘴蒜辣心,小哥對妹不真心,
你拿真情對別人,專說假話給我聽。
辣子辣嘴蒜辣心,小哥才是沒良心,
虛情假意欺哄我,心中想的是別人。
一句“辣子辣嘴蒜辣心”就唱出了小妹對小哥的虛偽充滿埋怨。現實中不僅小哥會辜負小妹,小妹同樣會對小哥不真:
牙齒草來根連根,浮萍生來不定根,
阿妹說話無定準,十句不有一句真。
牙齒草是一種野草,在生物學上屬茜草科,生于田野間的濕地處,它的根都是緊密串連在一起生長的;浮萍無根,漂于水上。阿哥通過對牙齒草和浮萍的比較,直接抒發了對阿妹對自己不真誠的不滿之情。勞動人民愛的是有情有義、對愛情堅如磐石的人。而不是那種喜新厭舊,見異思遷的人。因此,草中生情,不僅可以生出愛情,亦可以生出怨情。
動物作為與人類一樣有著同等生命的生物,在人類不斷追求著社會進步的過程中,漸漸成為了人類的附屬品。許多作家嘗試給動物一個意義,附加一個象征,高爾基筆下的海燕被隱喻為一個沖破暴風雨的革命者形象,藏克家先生筆下的老馬成為吃苦耐勞的底層人民代言人。其實,海燕和老馬完全可以是其它,像鋼琴一樣沒有生命,成為一架擺設,但在作家的筆下,這些可愛的生靈都被賦予了生命的意義。騰沖民間情歌中也有著不同種類的生命體,雖然它們沒有海燕那樣的生命價值,卻也承載著勤勞大眾的情感寄托。
五、蜜蜂傳情
人們歷來是喜歡贊賞蜜蜂的。 唐末詩人羅隱曾作《蜂》: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為誰辛苦為誰甜。這首詩總體上看是對蜜蜂的贊美,但在具體寓意上卻人云亦云。有人說:詩人似有所悟,實乃嘆世人之勞心于利祿者。有人說:此譏有人橫行鄉里,聚斂無厭,而百姓不能自保。唐末社會動亂興滅無常,故詩人有所感諷也。更多的人則認為是通過對蜜蜂的贊美與同情,為封建社會里無數終年辛苦難得溫飽的勞動人民鳴不平。在騰沖民間情歌里,蜜蜂不再作為政治寓意而被理解,而是多了幾分浪漫色彩,成為人們傳情示愛的生命載體:
妹是南山月月紅,哥是一只小蜜蜂;
蜜蜂落在花心上,蜂不揉花花不紅。
蜜蜂與花為伴,與花為善,不厭其煩,認真采擷每一朵花,精選能釀造好蜜的新鮮花粉,甘作月下老,使之花開滿樹,青果滿枝。詩歌中阿哥把阿妹比喻為“月月紅”,把自己比喻為“小蜜蜂”,卻不甘愿作月下老,只待阿妹這朵鮮花綻放后,落到花心上,揉紅鮮花,傳達對阿妹的情意。
六、 蜘蛛網情
在西方,人們認為蜘蛛能帶來好運,找到蜘蛛開始結網時的起點,你就會永遠幸運;在中國,提起蜘蛛,很多人想到的大概就是廢棄屋檐下那一張結實的網,又或許會想到多情的作家們給它賦予的象征意義:專注沉穩,心靈手巧;在騰沖,勤勞的人們賦予蜘蛛更加多情的意義。有一首《綠網蜘蛛》是這樣唱的:
哎~~綠網蜘蛛串樹根,人人說妹來跟哥,
只要我倆感情好,不怕鄉村起風波,
哎~~綠網蜘蛛串樹梢,莫怕風浪起多高,
只要我倆站穩腳,不怕別人用火燒。
哎~~綠網蜘蛛串中梁,人人都說妹跟郎,
兩朵鮮花一起開,郎心妹心進屋房。
哎~~綠網蜘蛛串大門,小妹就是屋的人,
苦得銀錢回家轉,花花轎子討進門。
“起興”是民歌中常用的修辭手法,在這首民歌中,“蜘蛛網” 作為其中一個主要的具體意象,它有兩種象征意義:一是結在戶外樹上的蜘蛛網,用它來起興,用的是它牢固結實、不怕風雨的引申意,來喻指情人之間的感情經得起考驗,承受得住外界的打擊;一是結在房梁中和大門上的戶內的蜘蛛網,它是“成家結戶”的喜慶象征:一些古老的廟宇中,廟中畫了蜘蛛網,吊著一只拉著蛛絲下垂的蜘蛛,叫做“喜從天降”。老人認為它是可以預示吉祥的蟲,故叫它“喜蟲”。用它來起興,比喻兩情相悅,喜結連理。
綠網蜘蛛結網的形象和男情女愛的描寫相結合,既使山歌顯得生動活潑,充滿鄉野氣息,又使情歌對情愛的表達曲折生動,充滿生活情趣,蜘蛛網出一番深情。
七、 杜鵑啼情
從情歌表征主體情感的角度,情歌意象可以分為寄情意象和抒情意象兩類。
寄情意象,是將“情”寄托在某一類“物”之中的意象,此種意象因物附情。而“物”又有有形的和無形的兩種。有形寄情意象是主人公的情感寄托在具體的物質形態和可見可感可觸的現實生活事象中。騰沖民間情歌中的動物意象就是有形意象。如《杜鵑》:
高高的杉樹插云間,
矮矮的錐栗在水邊;
杉樹上的雄杜鵑高聲啼叫,
錐栗枝頭的雌杜鵑涕淚漣漣!
杜鵑在中國古典詩詞中常與悲苦之事聯系在一起,春夏季節,杜鵑徹夜不停啼鳴,啼聲清脆而短促,喚起人們多種情思。情歌中運用“插云間”和“在水邊”的夸張手法來說明兩人之間的距離之遠,在這里距離不再產生美,而產生了“涕淚漣漣”的相思之苦,這首情歌借高杉樹和矮錐栗上的雄、雌杜鵑哀啼意象,寄托了有情人兩地相隔,不得相聚的痛苦愁緒。
騰沖民間情歌中的動物意象其實不僅僅只有蜜蜂、蜘蛛和杜鵑,在此舉出只能算是某一類動物中較具代表性的,云南作為孔雀之鄉,喜鵲作為吉祥的象征,也往往被騰沖人民給予向往美好愛情的寄托:
大田栽秧排對排,一對喜鵲飛過來,
孔雀美麗靠羽毛,小妹打扮等哥來。
盡管提起老虎人們想到的就是恐懼,但它卻擋不住情人想要相見的腳步:
半夜想起半夜來,不怕老虎不怕巖,
不怕老虎來攔路,只怕小妹不出來。
除此以外還有鴛鴦、魚蝦等等,在此不能一一詳述。
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勤勞勇敢的騰沖各族人民,在熱愛祖國、熱愛邊疆、熱愛家鄉的勞作中,他們在不斷創造豐富的物質文明同時,也不斷地創造著獨特的精神文明。只要我們深入他們的生活,你就會發現更多、更美的新民歌。
(作者單位:劉雅靜,湖南省婁底市群眾藝術館;王愛萍,云南省保山市曙光學校)
責任編輯:楊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