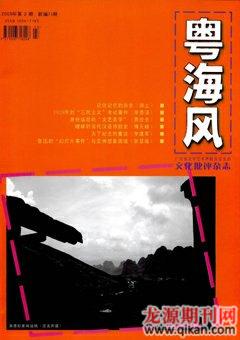未完成的中國現代性:啟蒙主義還是后殖民主義
楊春時
由于中國現代性與現代民族國家的沖突,革命代替了啟蒙,反現代性思潮長期居于統治地位,導致現代性的長期中斷和發展滯后。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是在初步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后重建現代性的歷史運動。現在,這個運動已經取得了歷史成果,主要是市場經濟的確立,為現代性奠定了社會基礎。但是,在世界范圍內,中國現代性仍然是滯后的、未完成的,這是一個基本國情。這主要表現為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善,政治體制改革尚未完成,現代文化建設也沒有實現,傳統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仍然居于統治地位。因此,中國當前的歷史任務仍然是走出傳統社會主義體制,建設現代性,而不是批判現代性。這意味著中國仍然需要啟蒙主義,仍然需要提倡科學、民主,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建立現代意識形態,完成“五四”開啟的現代性任務。
但是,在90年代之后,啟蒙主義衰落,后殖民主義興起。而后殖民主義是中國新左派的理論主張。在對中國國情的估計方面,“新左派”認為中國已經實現了現代性,現在應當進行現代性批判(奇怪的是,他們一方面說改革開放前的傳統社會主義實踐就是中國現代性,并且加以肯定,另一方面又要用后現代主義批判中國現代性——似乎指的是西方化的現代性,從而在何為中國現代性的問題上出現了矛盾)。這是對中國國情的錯誤判斷。他們進行現代性批判的武器,就是后殖民主義理論。后殖民主義是西方后現代主義理論,它在現代性高度發展的歷史條件下,批判現代性,反對全球化,解構西方中心主義。作為一種文化批判,它有一定的合理性,有助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義以及現代性和全球化的弊端。但是,作為一種學說,它同樣存在著弊端。它把人類文化的傳播和交流,與殖民主義等同起來。在批判歐洲中心主義的同時,否定西方現代文明。在批判現代性的弊病的同時,完全否定了啟蒙理性,否定了歷史的進步。特別是否定了啟蒙理性的普世價值,把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永久對立起來,從而把東方專制主義合法化。后殖民主義的肇始者愛德華·W·薩義德,在其《東方學》中認為,東方形象是西方塑造出來的,“東方并非一種自然的存在”,由于“西方與東方之間存在著一種權力關系,支配關系,霸權關系”,因而“可以被制作成——也就是說,被馴化為——‘東方的”。他明確地說:“我本人相信,將東方學視為歐洲和大西洋諸國在與東方的關系中所處強勢地位的符號比將其視為關于東方的真實話語(這正是東方學學術研究所聲稱的)更有價值。”(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第8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后殖民主義理論的弊病在橫移到中國以后更為突出,成為反現代性、反啟蒙主義的思想武器。現在學界出現一種強勁的潮流,那就是張揚后殖民主義的理論,主張反思、批判“五四”以來包括新時期的啟蒙主義,認為啟蒙主義是接受西方后殖民主義的產物,國民性批判是轉述西方殖民主義者的話語,中國被西方文化他者化了。中國是一個后發現代性的國家,現代性尚未完成。在這個時期,以后殖民主義批判現代性,就導致對現代性的毀滅。這不僅具有理論上的偏頗,也帶來了實踐上的災難。“新左派”正是利用后殖民主義理論,否定“五四”以來的啟蒙運動,反對改革開放,反對現代化,主張回到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和計劃經濟體制。從學術上說,這種思想有如下錯誤:
第一,中國從西方接受現代性,僅僅是片面的被給予——轉述后殖民主義的話語,還是文明對話和實踐選擇的結果?現代性來自西方文明,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不是被動的接受,而是主動的選擇。鴉片戰爭以來,對西方現代文明,中國并不是一開始就接受,而是由抵制、反對逐步到接受、引進。中華民族接受“洋鬼子”的文化,批判自己祖宗的文化,是經歷了長期的歷史實踐,進行了痛苦的探索和思考,才作出的選擇。在鴉片戰爭前,中國人視中國為文明中心,視西洋人為蠻夷,因此拒絕向世界開放;鴉片戰爭失敗后,意識到中國物質文明落后,西方的物質文明優越,遂有學習西方工業技術的“洋務運動”,但仍然認為中國政治、倫理優越于西方,堅持“西體中用”;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又意識到中國政治文明落后,西方政治文明優越,遂有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之舉,同時也堅持中國精神文明優越于西方(如當時的孫中山、周樹人都這樣認為);辛亥革命完成后,民主政治失敗,又意識到中國的國民性落后,遂有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引進西方科學民主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兩種文明的沖突中,中國人意識到西方現代文明的優長處和自身的短處,并且為了生存和發展,作出了自己的選擇。于是才有步步深入的爭取現代性的運動——從學習西方現代工業文明的洋務運動,到學習西方現代政治文明的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再到學習西方現代文化的“五四”啟蒙運動和新時期啟蒙運動。把這種選擇輕易地描述為轉述西方殖民主義話語,無疑抹殺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實踐和思想智慧。總之,中國的現代性認同是中華民族歷史實踐的結果,是由被動到主動的歷史選擇,是文明對話的結果,而不是被“制作”或者“馴化”的產物。
第二,國民性批判究竟是中華民族的自我意識還是被他者化、后殖民?啟蒙運動從西方引進現代性、批判國民性,正是以西方現代文明為鏡,發現了自我。中國傳統社會,閉關鎖國,自以為天朝大國、世界中心,它沒有世界意識,也沒有民族意識;它認為孔孟之道、宗法禮教是萬世不移的絕對真理。只是在西方現代文明傳入以后,才有了參照物,中國發現了另一種文明,并且意識到自己的落后,開始了反傳統的運動。“五四”啟蒙運動乃至新時期的新啟蒙運動都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如果沒有西方現代文明的借鑒,中國就沒有自我意識,可能還停留在封建時代,而無由融入世界潮流,無由進入現代社會。
第三,中國傳統文化的落后性究竟是西方殖民主義的話語建構,還是事實如此?后現代主義認為一切都是話語的建構,而沒有什么事實本身的存在。這作為哲學對終極存在的否定,也許有其道理。但社會歷史屬于形而下的領域,不能以話語代替事實,而要以事實為根據。后殖民主義理論家正是在這方面出了問題。他們把專制主義、奴隸思想、阿Q精神、愚昧落后、無個體意識等國民的劣根性,說成西方殖民主義話語的建構,而不是事實如此。這是對歷史現實的無知甚至是故意的歪曲。西方人從現代性(啟蒙理性)的視角,發現了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的落后,同時中國的先進分子也接受了現代性(啟蒙理性),發現了這些弱點,從而進行了對傳統文化和國民性的批判,以獲得現代性。國民性批判話語源自西方,并不能證明傳統文化的缺陷不是事實,也不能證明國民性批判沒有正當性。相反,對這種話語的接受(其實,不僅僅是接受,也有選擇和改造,如中國啟蒙主義者并沒有認為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反而要自立、自強,重新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表明中國獲得了世界意識,也獲得了自我意識。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后、挨打,使中國人意識到中國文明的缺陷,更真切地感受到了民族性的落后,從而進行了國民性批判。這并不是響應西方殖民主義的話語,而是為了擺脫落后,爭取進步發展。
第四,文明是互相融合還是永久對立?按照后殖民主義理論,文明只能對立、沖突,不能對話、融合,否則就是文化殖民主義。而事實上并非如此。如果說古典時代文明的融合還沒有大規模展開、世界文化還沒有形成,那么現代性開始了這個歷程。嚴格地說,無所謂文化殖民,文化傳通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并不能等同于政治壓迫。文明的融合是雙向的選擇,各種文明都從其他文明中吸取了異質的要素,從而豐富了自己。特別是東方文明在與西方文明的對話、融合中獲得了現代性。同時,也必須承認,西方現代文明是主導力量,它以現代性的力量整合了異質文明,形成了全球化的浪潮。必須辨證地看待全球化。一方面,它是歷史發展的方向,推動世界走向現代化。僅此而言,相對于后發現代性的中國,啟蒙主義仍然有合理性、必要性。另一方面,它也有西方強勢文化同化弱勢文化,抹殺非西方民族文化特性的問題。僅此而言,后殖民主義既有片面性,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后殖民主義是建立在民族文化本位主義的基礎上的,這意味著不僅西方把中國他者化,中國也把西方他者化。因此,不僅要警惕西方文化中心主義(東方主義),也要警惕中國文化中心主義。而恰恰在這一點上,新左派犯了與東方主義同樣的錯誤,那就是他們把西方妖魔化,把他們(無論是傳教士、政客還是學者)都描繪成一心歧視中國、誹謗中國、殖民中國的陰謀家。因此,他們的結論是,必須抵制西方文明,也拒絕啟蒙主義,不承認中國(無論是傳統的中國還是現在的中國)的落后,也不承認中國文化(無論是傳統的中國文化還是現在的中國文化)的落后方面。在現代性沒有完成的今天,這種思想顯然是錯誤而危險的。當前,后殖民主義成為新左派消解啟蒙主義的理論工具,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也有消極影響。它反對“五四”啟蒙運動以及20世紀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反對現代性在中國的實現,主張回到與世界文明隔絕、對立的傳統社會主義。這種理論有西方現代理論的時髦包裝,又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具有很大的誘惑力,特別是對那些不諳歷史而又知識基礎淺薄的青年人的影響更大。為了學術、更為了社會的現代發展,對此不能置之不理,而因此應該進行系統的批判。
當然,啟蒙主義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歷史的局限和片面性,盡管在當前現代性未完成的歷史條件下,這種負面性相對不突出,但也應該警惕和預防。啟蒙主義堅持引進西方現代文明(這是現代性的發源地),這是其符合歷史需要的主流方面;但對現代性的弊端認識不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有絕對主義的傾向,卻應該加以矯正。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后殖民主義有其合理性。解決啟蒙主義與后殖民主義的沖突,應該在堅持啟蒙主義方向的同時,吸收后殖民主義的合理因素。綜合起來說,就是倡導一種“文化間性”,即中西文化的對話與溝通,而不是片面的對立與隔絕,在文化開放中實現文化的現代化。其實后殖民主義的祖師薩義德本人也不自覺地提出了文化間性的思想。他反對把西方或東方作為一個固定的整體概念,因為這些文化已經與其他文化混雜在一起了,不那么純粹了。這說明和預示著文化融合的現實性與可能性,從而就突破了他的后殖民主義,而通向了文化間性。對中國的現在而言,就是既要接受現代性,迎接全球化的浪潮;也要警惕全球化帶來的文化單一化的危險,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但這絕不意味著狹隘的民族主義,抵制向世界開放、拒絕現代性,而是在積極的開放中能動地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在接受現代性中警惕西方文化中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