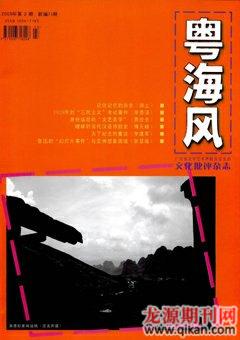廣東整風運動一瞥
董 彥
廣東的整風運動是全國的縮影。從當時的一些文件檔案,比如《廣東省整風運動報告》以及《大鳴大放資料》、《“放”“鳴”選輯》等小冊子,還有各系統各單位的總結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到運動的發展軌跡,知悉當年歷史風暴之中廣東的社會動蕩、思想起伏以及人際關系變化等等。
1956年11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提出,要在1957年開展整風運動。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5月1日,該指示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按照這個指示,這次運動的方針和方法是: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地針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開展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廣東和全國各地一樣,迅速融入了這場巨大的歷史風云。從1957年5月上旬開始,全省縣團級以上的中共機關、大專院校黨組織,紛紛組織黨外人士召開座談會,歡迎他們對中共提出批評意見。5月15日,中共廣東省委討論出臺了《關于整風運動的計劃》,并成立了由陶鑄、古大存、馮白駒、區夢覺、文敏生、尹林平、王德、李堅真、王匡等組成的省委整風領導小組,陶鑄親自任組長。5月19日,陶鑄親臨中山大學,在綠蔭掩映的禮堂里,召開了廣東省第一次關于整風運動的座談會,號召全校教職員工積極投身運動。這次座談會標志著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在廣東的開端,自此,廣東的整風運動匝地而起。據1959年3月11日公布的《廣東省整風運動報告》統計:運動期間,全省參加“鳴放”的約有2500萬人,貼出大字報5億多張,駐穗各單位舉辦大小展覽會2555個,鳴放批評意見163萬多條。
《廣東省整風運動報告》這樣評價整風運動:“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各級領導干部的思想作風和工作方法有了顯著的轉變”。報告還列舉了一些很具體的事例,比如群眾公開指名地批評領導干部或群眾間相互批評。某單位職工這樣批評同事:“病君譚權真作狀,一盅大飯食清光,天天‘偷雞回家去,不見病君食藥湯。”在廣州方言里,所謂“偷雞”指的是上班時擅離崗位、溜號。這張大字報是在批評那位職工裝病。當時被批評的人還可以說話,馬上寫出大字報表示接受批評:“大字報飛揚,警惕我思想,工作學習好,無事不離場。”廣東紡織廠工人批評該廠黨委書記:“忙!忙!忙!終日忙在會議旁,不下車間走一趟……請!請!請!請我們的宋書記,深入瞧一瞧……”如上所述,這個時期的批評主要集中在思想和工作作風等方面,而且態度較為溫和,甚至有批也有贊。比如廣州市八達鉚釘廠的群眾寫大字報諷刺自己的廠長工作不深入,是“貴公子”。這位廠長認真接受批評,在整風運動中即堅持下車間跟班勞動,群眾又寫大字報表揚他:“廠長躬身入車間,虛心學習不等閑,劈機頭上顯身手,工人群眾笑開顏。”
中國土產出口公司廣州分公司的整風總結報告認為:“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最好形式,也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最好方法。我們深深地體會到,大字報是幫助我們改正缺點,解決問題,自我教育及揭露各種問題的有利武器,特別對我們領導干部克服三風五氣,是起著推動作用。”該公司的總結還指出,整風運動使本單位原來“機構臃腫層次重疊,人浮于事,忙閑不均的情況有了根本改變”,因為“狠狠地批判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現在廣大職工自動提出加班,儲運科禮拜天也沒休息過,警衛同志主動提出代替保管員過磅,不安心統計工作的也表示一輩子都要搞統計,到處都呈現了新風氣”。
但是運動很快就呈現出對社會的負面效應,首先是咄咄逼人地顛覆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比如大學停課,師生們都去學習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開展“大鳴大放”。許多企業的生產安排也紛紛給運動讓路。比如《廣東省整風運動報告》顯示,擁有10個演出團體的廣東省民間職業雜技魔術團完全停止演出25天,全體人員集中在沙河頂的廣州音樂和電影技術學校內進行整風。這個僅有278人的單位,共鳴放大字報57684張,平均每人寫了200多張,不能不說是“蔚為大觀”。據當時的統計,這些大字報有揭發、暴露機關鋪張浪費的意見2395條,批評本單位右傾保守的意見616條,關于干部思想作風的3528條,關于規章制度方面的733條,關于生活福利方面的648條,揭露貪污與違法亂紀行為的15條。
到了大鳴大放后期,“鳴放”中對黨和政府批評的言辭日益激烈、尖銳,對右派份子的圍剿也隨即呼之欲出。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么?》,標志著整風運動進入第二階段。7月,毛澤東在上海干部會議上作了《打退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講話,并寫下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和風細雨”的“鳴放”告一段落,批斗右派分子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就此來臨。
北京的號令很快在南方得到響應。1957年7月4日,中共廣州市委在中山紀念堂召開了有4000多人參加的“反擊右派分子大會”,在會上通過了《對右派分子的聲討書》。大會義正詞嚴地宣布:堅決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7月9日,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發出一份題為《堅決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宣傳提綱,列舉了羅翼群、云應霖、儲安平、章伯鈞、章乃器、龍云等人的右派言論,并加以分析、駁斥。
盡管如此,一些系統和單位在反右斗爭初期還是相對謹慎的,斗爭的火力也算不上猛烈。8月9日,廣東省委統戰部發出的《關于工商界講習所反右派斗爭問題的通知》還在要求:“對學員僅在學習中發表偏激言論的不要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即使是對那些已經認定了的右派分子,也要“經黨委研究批準后才實施斗爭”。8月31日,省委文教部的《關于如何在中小學中展開反右派斗爭的報告》指出,“目前由于各地、縣、市機關反右斗爭尚未開始,現在也忙于生產,分不出力量,學校的隊伍未形成,立即在學校展開斗爭,必然產生很多困難,我們首先必須做好準備工作”。這些準備工作包括動員學習、查找收集右派材料、做好排隊工作等,總之,還談不上急風暴雨。該報告還特地強調,有關右派的“材料必須實事求是,查對清楚”。至于反擊右派的具體措施,也只是似乎不無象征意義地“對不稱職、作風不好的干部加以適當調整”。對于中等學校的學生,更是明確指出,“不搞反右派的斗爭,集中二天時間學習反右斗爭形勢”,只是在學習時間結束之后,再“在寒假放假后的10天或半月集中到地委或縣委進行反右斗爭”。從中可以看出,在那個階段,基層組織對那場影響中國社會進程和數百萬知識分子命運的運動并沒有很清醒、很明確的認識,在思想認識上還跟不上毛澤東的整體戰略部署和具體實施計劃。
但是,反右運動很快便呈現洶涌態勢,斗爭開始變得越來越嚴厲。關于右派分子的標準和具體劃分方法已經逐漸明朗而細致,越來越多的人被卷了進去。右派分子的劃分有了可操作性,細分為“極右”、“普右”、“中右”等名目,分類歸檔。還有一種叫“疑似分子”,可以歸入右,亦可以歸入中右,命運就靠運動的組織者隨機決斷。中央給出了“右派分子”的標準,各地又對標準進一步理解和闡釋。這種進一步理解和闡釋都是上綱上線,變本加厲,往深里說。如江門地委財貿部的總結這樣界定右派分子:“就是在政治上攻擊和反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他們非難大躍進,非難人民公社,目的就是在于否定黨的總路線,而代之以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他們污蔑總路線不是實事求是,不符合人民的愿望,執行總路線使國民經濟計劃失調,攻擊大躍進是‘大躍退、‘大冒進,大煉鋼鐵是‘得不償失、‘勞民傷財,公社‘搞快了,搞糟了,‘根本就沒有優越性。右派在實質上就是阻攔中國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資本主義在中國死灰復燃。”
廣州市委財貿部在11月14日下達了《關于反擊右派斗爭中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開篇即指出,斗爭初期有些單位排隊工作做得較粗,要求普遍地、認真地再做一次,并詳細給出斗爭步驟,如“充分地占有材料,儲備彈藥”,然后“看準咽喉,針對不同問題選擇不同的彈藥,對準敵人,命中要害”,“將具有共同性論點的右派分子劃成一批,分交給幾個斗爭小組一起開火,進行全面開花”。從其中使用的那些惡狠狠的詞語就可以深刻感受到,反右斗爭已經被視為兩軍對壘、劍拔弩張的戰斗,彌漫著強烈的火藥味。
據《廣東省整風運動報告》統計,廣東省從文教界、文藝界、衛生界、新聞界、科技界、工商界、民主黨派中揪出了36610名“右派分子”,占參加運動總人數5.5%,機關干部中的右派占參加運動總人數3.68%,民主黨派中則有20%的人成為了“右派分子”。
與全國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在開展反右派斗爭的同時,廣東還開展了以“反對地方主義”為中心的廣東歷史問題大辯論,實際上是借整風的大勢形成了一次關于“地方主義”的大批判。當時認定省委書記處書記古大存、馮白駒是“廣東地方主義”的頭子,對他們開展了重點批判。1957年12月,中共廣州市委召開第十次全委(擴大)會議,連續開了16天,對廣州市的“地方主義”言行進行揭發批判。在會上,受到重點批判的有市委書記處書記吳有恒、鐘明,副市長余美慶,統戰部副部長兼僑務局局長謝創,市財貿辦主任古念良等。市委副秘書長陳恩、市委辦公廳主任王伯群則被打成“反黨小集團”。還有一些由東江縱隊轉業到廣州工作的人,因為節假日常聚集在市勞動局局長李愛農家閑聊,也被說成是“東江會館”小集團活動而受到批判。指責他們“在思想政治上一貫右傾,有嚴重的地方主義和個人主義,又進行非組織活動”,是一股“反黨反馬列主義的逆流”。在進行重點批判后,于1958年3月作出組織處理:吳有恒被撤銷黨內一切職務,留黨察看兩年,行政降兩級,下放廣州造紙廠當車間副主任。鐘明被撤銷中共廣州市委書記處書記和市監委書記,下放到廣州協同和機器廠(廣州柴油機廠)當黨委書記,余美慶、謝創、陳恩、王伯群、古念良以及所謂“東江會館”的一些主要成員也分別受到黨紀處分。
在反右斗爭中,“左”與“右”之間已經形成楚漢不兩立之勢。但是從1957年11月開始,反右斗爭發展成整改(整頓與改造)運動。斗爭矛頭開始從右派轉向一般群眾和領導。這時候,上下之間也產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裂罅。
在廣東省檔案館,存有省商業廳整風領導小組于1958年7月31日寫就的一份調查材料,是關于一位“重點批判對象”的調查結論。這是一份現在看來極為普通的調查材料,但在當時卻極其敏感地關系著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審查對象叫原魯,時任廣東省商業廳廳長。材料顯示,他的突出問題是“對黨領導的偉大整風運動特別是在反地方主義問題上表現嚴重的右傾和作為上一貫表現嚴重驕氣”。材料中列舉原魯的錯誤之一是“不尊重戰線領導”。“原魯常在處以上干部會議上公開說戰線干部是吃干飯的,甚至在戰線整風辦公室傅春梅下來傳達戰線指示時,也對傅說:‘你們戰線干部干啥吃的,我去了沒找到一個人,你們都是吃干飯的。”材料里還寫到,戰線通知開會時指名強調要原魯參加,他不是不出席,就是指派別人去。
材料還反映,原魯“民主作風差,有時對人粗魯”。“一般干部向原請示、匯報,有時碰到原廳長工作忙時就是申斥或漫罵,或當別人尚未開口之前,便揮手把人趕出門外。”“在會議上也往往不傾聽別人的意見,甚至不讓別人做充分的發言,不是中間掐斷,就是背著手走來走去。”有的干部說:“他是首長,我們年輕輕的,罵我們幾句不算什么,對王克清同志(省供銷社辦公室主任)一樣的罵,王主任的兒子已經長我們這樣高了,還挨罵,像什么話。”
這份調查材料認為,原魯的最嚴重、最關鍵的問題是,“對上級有關整風指示、決議不夠尊重”,“對黨的偉大整風運動表現嚴重右傾”。對此,材料還拿出了一些事例來作證。比如提到:在雙反運動時,整風辦公室羅蘭珍同志將省人民委員會《關于下一步運動做法的指示(特急件)》送給原看時,“原不但不看,還說‘什么特急不特急,你這個人,專門來送文件。揮手叫羅出去。后來整風辦公室劉科長認為該件是領導小組必須要看的,又親自送來,原仍是不看,并搖頭擺手說:‘我懂了,我懂了!”當戰線干部面告原魯出席戰線領導小組會議的通知,他說:“什么整風,整風,開會,開會,不下鄉了解情況,開啥會,整啥風,我要抓業務。”
這些繪聲繪神的細節,為我們描繪了一個性格直率,容易急躁,脾氣有點大,喜歡批評人的廳長。但這些似乎只關乎性情或為人處世的態度,屬于脾氣和作風的問題,無關乎大的原則。按照如今的標準,甚至還有幾分可愛。但是材料最后下的結論卻是“原魯同志的錯誤是嚴重的,實質上是喪失立場”,為了教育原魯本人和全體同志,“我們認為原魯同志整風運動第四階段中應作為我廳重點批判對象”。
正因為局勢是這樣的嚴峻,打擊是這樣的嚴厲而寬泛,許多人在運動的暴風驟雨之中驚慌失措。有不少被批判的人認定自己再也等不到云開霧散的一天,只好一死了之。自殺的人數不斷上升,據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在1958年底發出的一份通報披露,僅省人民委員會系統,“從11月20日至12月9日這一期間,先后發生了自殺事件6宗,其中:省銀行1名,工業廳1名,外貿局4名(藥材公司3名,外運公司1名)。內有右派分子4名,疑似分子1名,中右分子1名。已死4名,未死2名。”
整風運動雖然已經過去半個來世紀,但是那些歷史的印跡至今讀來依然令人感慨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