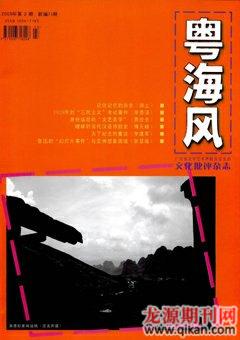現代文化研究中的“上海摩登”
張春田
“現代民族國家”這一敘述和分析單位,在晚近的理論思考中已經遭遇到了空前的挑戰。一方面,跨國資本主義的運作造成了一種全球化的格局,一時一地的變動,往往牽連到多個民族國家,需要在“國際化空間”中才能看清;另一方面,隨著大都市(metropolis)在當代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格外舉足輕重,以及流向各大都市的跨國移民越來越多,并形成了更加多樣的“現代”微觀語境,“城市”的意義得到了高度重視,甚至,“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也從文化研究中脫穎而出,成為顯學。在所謂的“大中華”區域,香港、臺北和上海也逐漸成為了關注的焦點,而尤以上海為最。各種資料和研究成果浩浩蕩蕩,以上海為關鍵詞的學術會議和討論層出不窮,匯聚成了蔚為大觀的“上海學”(Shanghaiology),[1]甚至也成為“上海熱”的重要淵藪之一。
從中國現代文學的角度看,“上海熱”有個前身,那就是“張愛玲熱”。1980年代后期,“張愛玲熱”從港臺登陸后,迅速播散,贏得“張迷”無數。張愛玲對于世俗欲望的直面,對于日常生活的看重,乃至傳奇身世、特立獨行、奇裝炫人、亂世之戀,都為人所津津樂道。然而,一如有研究者所謂的,“‘張愛玲熱熱中有‘冷”,我們這個時代的接受者不愿意看到張愛玲念茲在茲的“荒涼”的“惘惘的威脅”,失去了那樣一個“反面的烏托邦”的悲憫,仿佛張愛玲就是一個只要“物質”,排斥“精神”;只會“瑣屑敘事”、抒寫愛情故事,與“時代”和“歷史”根本絕緣;全然擁抱“現代”或者一味“懷舊”古老中國的作家。[2]遺憾的是,不僅媒體表述和時尚“消費”如此塑造“張愛玲”,而且當張愛玲被現代文學史“失而復得”后,眾多論者也是持這樣簡單化、對立式的“張愛玲觀”,迄今在“張學”研究中仍頻頻可見。[3]
在我有限的閱讀經驗中,孟悅是較早對這樣的論斷提出反思的學者。《中國文學“現代性”與張愛玲》中,從“時代觀”與“怎樣寫作這個時代”出發,分析了張愛玲與“五四-左翼”話語的對話關系。與一般俗見只看到張愛玲文學中形式的新穎精細不同,孟悅更為深入地重視起“形式的意識形態”,“張愛玲知道怎樣為并未整體地進入一個‘新時代的中國生活形態創造一種形式感,或反之,怎樣以細膩的形式感創造對中國生活和中國人的一種觀察,一種體驗,一種想象力。”孟悅試圖揭示形式背后的文化內涵,追問那個“蒼涼的手勢”究竟有怎樣的所指。她從“意象化空間”中引申出“意象化敘述”,發現張愛玲習慣以空間作為對社會和文化形態的表達形式。“意象化地呈現出一個參差不均地分布著‘傳統與‘現代各種因素的地域空間”,“為中國‘半現代的普通社會——具體說是普通市民百姓的社會——提供了寓言式的活動空間”。又提出要把張愛玲的“新傳奇的敘事手法”放回“中國那段以‘現代國家們漂洋過海打上門來的戰爭為開場的近代歷史背景上”去重新考量“傳奇”的歷史的“底子”。[4]正因為有這樣一個“底子”,張愛玲打開了“五四現代觀”所促生的新文學以及左翼文學不曾深入的寫作世界,也超過了鴛鴦蝴蝶派、新感覺派的寫作高度。
雖然現在看來,孟悅的文章中沒有區分“五四新文學”與“左翼文學”,而將兩者界定為一脈相承,這是可以商榷的。但這并不影響此文的重要意義,她打破了用“家”/“國”、“傳統”/“現代”的二元對立的思路去討論張愛玲的研究路數。在文章結尾,孟悅細讀了張愛玲的散文《中國的日夜》中對于“國”和“傳統”的表述,最終把張愛玲的“啟示”概括為:“張愛玲所寫的‘國借用了下層市民文化的想象域,……(她)擬設了一個中國半傳統的普通市民社會的聲音。”[5]孟悅想指出,張愛玲正是通過對“普通市民社會”認同來傳遞她的“中國”認同的。這點,韓毓海后來更直白地點了出來:“她(指張愛玲——引者注)的諸種言說正是作為這樣尖銳的‘意識形態之聲加入到40年代中國走什么樣的現代道路的血與火的廝殺之中……她認為中國城市民間的內在的合理主義,要比外在的烏托邦意義理性的強加,更有利于中國的現代進程。”[6]
值得注意的是,張愛玲所認同的“普通市民社會”并不是一個普泛概念,而就是具體特指她所生活其中的“上海”。《〈傳奇〉再版的話》里那段名言“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里有這惘惘的威脅”中,“我們的文明”其實就是“上海的文明”,更準確地說,是上海開埠以后所形成的“現代上海的都市文明”。考慮到《中國的日夜》中自辯的渴望和自我拯救意味,——《中國的日夜》寫于抗戰勝利以后,其時,張愛玲已面臨上海一些報章上的“漢奸”指責。利用為《傳奇》再版寫跋語的機會,張愛玲不露痕跡地作了個爭辯。——那么,我們也許不應該讓張愛玲“到底是中國”的感慨,掩蓋了她更為深切的“中國,到底”的吁求。就在散文《中國的日夜》最后,有一首同名的小詩,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我真高興曬著太陽去買回來/沉重累贅的一日三餐。/譙樓初鼓定天下;/安民心,/嘈嘈的煩冤的人聲下沉。/沉到底。……/中國,到底。”張愛玲一向甚少寫詩,讀得出這次她是動了真情。在她心中,“沉重累贅的一日三餐”是有可能使中國復興到“譙樓初鼓定天下”那樣的漢唐“安穩”的。而進一步,也許還應當把這個吁求與她為《傳奇》初版所寫的一篇散文的題目——《到底是上海人》聯系起來。[7]在張愛玲發自內心的、根本的認同里,“到底”就是要“到”上海都市的日常生活”這個“底”。所以,與其說張愛玲的“背后”是“中國”,毋寧說是“上海”,是上海的現代文化傳統與都市經驗的沉淀。對于“上海”與“中國”之間某種“此消彼長”的內在緊張、糾結的意識和暗示,以及對此的無奈、無解和感傷,正是張愛玲作為一種現代性的文化和文學表述的意義所在。
張愛玲的“啟示”或者“危機”,提醒了更全面地總結上海文學與文化傳統的必要。這就不能僅僅局限文學領域,而要把視野放寬到媒體、出版、影像、建筑、市民生活等領域,處理更為綜合的“文本”。在美國的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研究中,王德威從地域文化的角度闡釋上海文學書寫與文化記憶的關系,[8]張旭東對于王安憶與上海城市意象的討論,[9]盧漢超對于都市市民生活的再現,[10]以及孟悅的博士論文在亞洲和世界諸多文化影響下考察上海的歷史演變,都值得關注。[11]而在這方面,李歐梵的《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更是著人先鞭,成為典范。他借鑒文化研究和新文化史方法論中都市和文學“對讀”的取徑,重繪了上海1930-1945年代的文化地圖。
先前,李歐梵已經對上海都市文化有所涉獵。他曾經研究上海《申報》“自由談”版上的從“游戲文章”到魯迅雜文,利用對哈貝馬斯“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理論的故意“誤讀”,來探討晚清以降,知識分子利用報紙開創文化和政治“批評空間”的努力。[12]在《上海摩登》中,李歐梵從“文化想象”的角度切入對都市現代性的探討。他強調:“現代性既是概念也是想象,既是核心也是表面。”探索“文化想象”時,不能忽視“構建和交流這種想象的形式”,“換言之,我們不能忽略‘表面”。[13]他撥開整體上歷史性的大敘述,創造性地借鑒了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空間的生產》一書中關于“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的理論,同時,用本雅明筆下的“游手好閑者”“漫游”的姿態和目光,[14]把“物質生活上的都市文化和文學藝術想象中的都市模型”連接起來。他關心都市物象和媒體:外灘、百貨大樓、咖啡館、舞廳、電影院、《東方雜志》、《良友》畫報、月份牌……,感受都市的“摩登”氛圍,以及鑲嵌在各種城市空間里的人的活動和關系;調查當時上海的大眾消費狀況和流行口味,注意電影與出版的結盟下大眾文化文本的獨特性;通過文學翻譯和《現代雜志》,發現了西方現代主義在上海經歷的“文本置換”,從而,對文化、文學的生產、傳播和消費機制作出了更為切近的描述。
在對于具體作家和文學作品的解讀中,李歐梵勾勒了一個都市文學的敘述譜系:施蟄存將現代心理分析引入歷史小說的文體實驗,劉吶鷗和穆時英對于都市消費空間和女性身體“戀物癖”式的沉溺,邵洵美和葉靈鳳文學趣味乃至私人生活的頹廢、浮紈,張愛玲在淪陷的都會中用“參差的對照”寫“傳奇”。馬泰·卡林內斯庫(Matai Calinescu)的《現代性的五副面孔》正好為李歐梵提供了一些概念,[15]將這些作家和文本串起來,共同展布出在上海出現的“另類現代性”及其美學面孔。
對上海的重新解讀,貫穿了李歐梵對于“五四”現代觀及其實踐的反思和反撥的沖動。李歐梵認為,中國現代性“從二十世紀初期開始,是一種知識性的理論附加于在其影響之下產生的對于民族國家的想象,然后變成對于都市文化和對于現代生活的想象”。[16]就像王德威要把晚清“被壓抑的現代性”顛倒過來一樣,李歐梵也要重新追回那曾經存在過、最終卻失落了的都市文化、異域情調及其“世界主義”。
的確,在20世紀30年代,上海已神氣地跨越了“前現代”,和世界最先進的城市同步,并發展出一套比較成熟的都市市民文化。于是,在很多人想來,以“中產階級”、“公共空間”、“市民社會”等為節點編織的“上海現代性”,不僅作為微觀的標本而輝煌,而且在宏觀上,也直指本可造就的“另一個中國”[17]。換言之,“上海”才應當是中國現代化選擇的不二法門。但是,就像李歐梵引用他的老師列文森(Joseph Leveson)所指出的那樣:“對這個新的‘小布爾喬亞世界主義的提倡是注定要失敗的。”[18]而這也正是張愛玲的寫作里所內涵的“大悲”——試圖從“安穩”來抵達“安穩”,對于整個中國而言,事實上行不通。從國門被打開到“五口通商”,從租界的形成和工部局的制度安排,從“華洋分居”到“華洋雜處”,從太平天國運動帶來的大規模難民和資本涌入租界到“一戰”期間上海民族資本發展遇到的所謂“黃金時代”,還有抗戰時期上海特殊的孤島情勢……這些特殊的歷史境域,對于“上海”之為“上海”,至關重要。
如果“上海”的繁榮,很大程度上是以“內陸中國”的犧牲、凋敝、淪喪為代價的,那么,上海的世界主義和上海被殖民處境之間的關系,上海都市日常生活與商業文化、消費主義之間的關系,上海摩登的一面與“霓虹光影之外”的世界之間的關系等等,這些“上海現代性”本身叢結的問題,都需要深刻反省。更何況,“上海”其實并代表不了“中國”。把“上海”編織進一個日益膨脹的美好前景神話之中,除了可能為某種發展主義的新意識形態提供廉價的合法性支持外,并無真正幫助。“中國如何現代”的問題,依然懸而未決。
[1]熊月之、周武編的《海外上海學》,對此有詳細梳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2]參見倪文尖:《不能失去張愛玲》,《欲望的辯證法》,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年,第159—164頁;《懷舊與張愛玲》,《書城》2003年第4期。
[3]不少學者不免入此陷阱。比如,周蕾(Rey Chow)在《婦女和中國的現代性》(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1)一書中,就把張愛玲寫作的意義歸于女性私人敘事和“細節世界”。
[4]參見孟悅:《中國文學“現代性”與張愛玲》,原載《今天》1992年第3期,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收入王曉明主編《批評空間的開創》,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334—354頁,引文見第340,345,352頁。
[5]孟悅:《中國文學“現代性”與張愛玲》,收《批評空間的開創》,第354頁。
[6]韓毓海:《“大悲”——“民間社會敘事”的失敗與張愛玲小說的意識形態性》,《從“紅玫瑰”到“紅旗”》,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年,第98頁。他認為,張愛玲關注民間日常世俗生活導向了“對于中國現代不可化約的悲劇的想象性解決”,“而且它也支持了通商口岸中國現代的繁榮”,見第84頁。
[7]關于“我們的文明”就是“上海的文明”,參見倪文尖:《張愛玲的“背后”》,《欲望的辯證法》,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第165—193頁。
[8]參見王德威:《文學的上海,1931》、《海派文學,又見傳人——王安憶的小說》等文,收《如此繁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
[9]參見張旭東:《上海懷舊——王安憶與現代性的寓言》和《上海的意象——城市偶像批判、非主流寫作、與現代神話的消解》,收入《批評的蹤跡——文化理論文選,1985-2002》,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以及《王安憶、上海、“小文學”》,《書城》2002年第7期。
[10]盧漢超:《霓虹燈外:二十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11]孟悅:《發現上海:文化過程及其轉折,1860-1920》(The Invention of Shanghai:Cultural Passage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1860-1920,Dissertation.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0)。
[12]參見李歐梵:《“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二十一世紀》,香港,1993年10月號。今天重看李歐梵此文,明顯存在一些漏洞。比如,他不斷作規范性的假設,沒有對《申報?自由談》做很好的歷史描述;沒有分析報章體的興起,以及《申報》在報界整體結構中有什么背景;他忽視了“公共空間”本身對邊緣社群可能造成的壓抑,對于魯迅的雜文寫作與對媒體的警惕,更多誤解。11年后,在同一本刊物上,陳建華的《申報·自由談話會——民初政治與文學批評功能》發表,與李文對話。他重視為“典律”(canon)所排斥的?“他者”,考察了1912—1914年的“自由談話會”專欄,肯定其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公共“批評空間”。陳文補充了李文沒有探討的潛藏在“文本”之后的資本經濟的勢力。見《二十一世紀》,2004年2月號。
[13]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毛尖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71頁。
[14]參見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張旭東、魏文生譯,北京:三聯書店,1992年。與本雅明不同,在李歐梵對上海的描繪中,細膩委婉的懷舊情緒取代了“氣息的光暈在震驚經驗中四散”(168頁)。
[15]尤其是馬泰·卡林內斯庫對“頹廢”的美學現代性的討論,參見《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顧愛彬、李瑞華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
[16]李歐梵:《當代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和后現代性》,《文學評論》1999年第5期。
[17]《另一個中國:1919—1949年的上海》是法國漢學家白吉爾(Bergere)一本書的書名。她的另一本著作《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年》,對于城市精英與資產階級,南京國民政府對資產階級的政策,有精彩分析。
[18]列文森:《革命與世界主義:西洋舞臺和中國舞臺》,轉引自李歐梵《上海摩登》,第3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