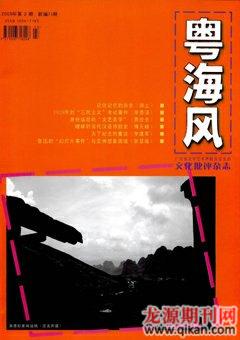身份尷尬的“文藝美學”
黃應全
幾年前,我有幸參加某高校舉行的一次以文藝美學為主題的會議,聽完許多學者的滔滔宏論之后,心中感慨良多,不禁想起一個古老的問題:世界上是否還存在“真理”這種東西?如果有,真理是掌握在多數人手里呢還是掌握在少數人手里?在那次會議上,文藝美學是否成立無形中成了討論的中心問題,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們絕大多數都認為文藝美學是能夠成立的,只有極少數(甚至應該準確地說只有個別人)對此表示了懷疑。這種現象真是讓我大惑不解:人們都承認在西方甚至前蘇聯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沒有過文藝美學這樣的學科,承認文藝美學是中國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發明”出來的,但是人們又竭力證明文藝美學的存在可能性,甚至把文藝美學的建立說成是中國美學研究對世界美學研究的主要成就。或許是由于自己缺乏創造的勇氣或者是由于自己天資愚鈍,我真是難以理解我們的美學學者們何以如此自信。為什么不把西方和別的地方沒有文藝美學的事實看成是我們犯了錯誤的證據而非我們高明的證據呢?難道中國學者在其他方面資質不夠,唯獨在美學方面獨具稟賦,居然能夠創立一門前所未有的學科?靜而思之,答案不言而喻。
實際上,我對文藝美學的懷疑由來已久。“文藝美學”一詞在我做本科生的時候就已經非常熟悉了。當時我們堂堂的系主任就是教文藝美學的。作為一個對美學頗有興趣的學生,我還專門借閱過《文藝美學》之類的書籍。當然,我當時雖然對之偶爾心存疑惑,卻從來不敢懷疑該學科之偽。等到我讀了美學研究生,對美學史和美學理論的認識多了一些,對流行的有關美學分支學科的劃分就產生了很深的懷疑。美學作為一門學科在何種意義上成立已經讓人大傷腦筋,從美學中孕育出的一系列分支學科就更不用說了。我記得,與我有共同感受的大有人在。我的很多師兄弟最終都離開了美學,這其中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對美學的不滿至少也是其中之一。我們當時懷疑的對象雖然還不是文藝美學,而是美學本身。但是,幾年以后,由于我在中文系教美學,我對美學學科本身的疑慮減少了,但對“文藝美學”的疑慮卻增大了。記得系里有一次要求我開文藝美學課,我說我開不了,因為我不知道如何把我正在開設的美學課與文藝美學課區分開來。現在我帶研究生,專業方向又是“文藝美學”,我再次不得不為之煩惱莫名:“文藝美學”究竟是個什么東西?
不應把對文藝美學的這種懷疑歸結為“美學虛無主義”的結果。有人一聽你懷疑美學或文藝美學的存在,就給你扣上一頂帽子:“美學虛無主義”。按照這種人的邏輯,我現在懷疑文藝美學,我現在就在搞“文藝美學虛無主義”。事實上,要說明文藝美學很成問題并不困難。首先,單從名稱上說,“文藝美學”就已經是自拆臺腳的了。“文藝”一詞是含糊的。我沒有考證過它的確切來源,但我想它大概與朱光潛先生有關。朱光潛先生喜歡使用“文藝”一詞。比如,他早年最著名的美學著作就叫《文藝心理學》。但是,即使在朱光潛等人那里,“文藝”這個術語也是不太明確的。它至少包含兩個基本意思,一是作為一種藝術的“文學”,一是以文學為代表的藝術。前者實際上是指今天人們習慣上說的“純文學”,后者則指今天人們所說的包括文學、音樂、繪畫等等在內的“純藝術”。朱光潛主要偏向于后者。他的《文藝心理學》實際上等于《藝術心理學》。“文藝美學”在面對這兩種基本含義時應作何選擇呢?它只能左右為難。一方面,如果“文藝”指“文學”,那么,“文藝美學”的準確說法應該是“文學美學”,“文藝美學”一語就純屬多余。我們只需直接稱之為“文學美學”足矣,使用“文藝美學”不過徒增混亂。另一方面,如果“文藝”指“藝術”, 那么,“文藝美學”的準確說法應該是“藝術美學”,“文藝美學”一語也仍屬多余和添亂。那次會議中對“文藝美學”應該如何譯成英文的爭議就證明了這一點。
當然,“文藝美學”問題并不是一個純粹的名稱問題。事實上,名稱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為它涉及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文藝美學究竟研究什么?一個學科沒有需要專門研究的對象,它就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學科。關于文藝美學的研究對象,“文藝”一詞的含糊性暗示了兩種可能的答案:一是認為文藝美學研究的是文學,二是認為文藝美學研究的是藝術。但是,這兩種答案都是很成問題的。如果認為文藝美學就是文學美學,就是從美學的角度研究文學,那么它與文學理論之間的關系就成了大問題。什么叫從美學角度研究文學呢?有兩種基本可能性,一是從理想形態出發把文學作為一種純審美的現象來研究,一是從現實形態出發把文學中的審美成分挑選出來加以研究。前者導致文藝美學與文學理論是一回事,從而證明根本不需要文藝美學,因為文學理論早就“占有了”它所設定的對象。后者導致文藝美學最多成為文學理論中的一個部分,從而也取消了它成為一個獨立學科的可能性,因為文學理論早就在進行著對文學的審美研究。這樣看來,把“文藝美學”的研究對象確定為文學是很難成立的。
人們最喜歡的還是把文藝美學的對象定為藝術,認為美學可以研究一切審美現象,而文藝美學則專門研究藝術中的審美現象或作為審美現象的藝術。這種觀點貌似有理,其實也是問題重重。其最根本的困難在于它無法說明文藝美學與美學有何不同。我們知道,美學學科誕生的時候還存在“關于美(或丑)的學科”和“關于藝術的學科”兩種可以分開的含義。但是,至少從謝林開始,這兩種含義就已經逐漸合而為一。美主要指藝術美,藝術主要指“美的藝術”(fine art),美學成為關于“美的藝術”的學科。黑格爾美學是其典型。黑格爾之后的西方美學乃至世界美學雖然有時也把美和藝術區分開來,但往往是把二者聯在一起的。美學基本上等于藝術哲學或藝術原理。這是因為,西方藝術本身也不斷走向自律的藝術即多半以審美價值為主的藝術,美學作為研究美(或審美元素)的學科似乎不可避免地要以藝術為它的對象。換言之,過去作為研究美的學科的美學似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通過藝術來研究美的美學。美學就是關于藝術(美的藝術)的原理性研究的學科。在黑格爾之后的西方,美學=藝術哲學一直是主流,這是不爭的事實。如果是這樣的話,“文藝美學”又如何可能呢?如果美學就是關于藝術的一門學科,那么再在“美學”之前加上一個“文藝”(即藝術)有何必要呢?這豈不是同語反復,豈不是犯了最簡單的邏輯錯誤?
當然,通行的未必是正確的,我也不認同“美學=藝術哲學”這一黑格爾公式,我認為美學是美學,藝術哲學是藝術哲學,因為藝術哲學的對象是藝術,美學的對象是審美現象,審美現象與藝術并非重合關系而是交叉關系。但是,仍然有兩個原因讓我覺得即便是藝術美學意義上的“文藝美學”作為一個學科也很難成立。第一,從美學史來看,剛才說過,黑格爾以后的美學常常被等同于藝術哲學。雖然即便在西方也有很多學者認為這種等同很成問題,但是它已經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只要你認可這一事實,你就應該認可下述結論:即使你想強調對“藝術美”的研究,也不需要“文藝美學”,因為已經有了“藝術哲學”,而且是占據美學史主流的“藝術哲學”。第二,即使拋開客觀事實,以創新為己任,把美學和藝術哲學區分開來,確定藝術中只有與審美相關的部分才是美學研究的話題,其余部分與美學無關,但還是存在一個問題:它值得獨立出來作為一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嗎?也許只需要在藝術哲學或美學中安置一部分就夠了。如果是這樣,“文藝美學”也是不能成立的。要知道,把美學與藝術哲學區分開來作為兩個獨立學科已經有點勉為其難了,哪里還有“文藝美學”的生存空間?
我承認,中國學者提出“文藝美學”概念最初的確有它的現實需要乃至積極意義,但我還是要說,它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學術上的錯誤觀念所致。按照“文藝美學”發明者們的回憶,20世紀80年代初,人們對過去一味強調文學的政治性不滿,轉而強調文學的審美特性。“文藝美學”的初衷就是力圖從審美的而非功利的角度研究文學。因此,“文藝美學”產生于文學研究撥亂反正的基本需要。人們也不難發現,“文藝美學”的提出確實強化了人們對文學審美元素的重視。但是,稍稍思考就不難發現,對于文學乃至藝術的審美層面的強調并不必然需要建立“文藝美學”這個非驢非馬的學科。僅就文學來說,文學理論中的“文學性”問題、文學自律性問題等等就已經是對文學審美性質的強調,而且這些問題更為明確具體,至少比諸如“從審美的角度看待文學”要明確得多。換句話說,只要我們徹底改變過去庸俗社會學的文學理論,重新回到視文學為一種藝術的正確軌道上來,我們就已經最好地進行了文學研究的撥亂反正,根本不需要提出“文藝美學”這樣的東西。這樣看來,“文藝美學”一開始就是病急亂投醫的結果。
當然,如果我們回首那個新鮮提法層出不窮的20世紀80年代,我們就應當承認“文藝美學”的出現一點也不奇怪,我們也就不應苛責文藝美學當初的主張者攪亂了美學學術的研究。我們應該詢問的是,在“文藝美學”或許有過的積極意義已經喪失的今天,人們何以還死死地堅守著“文藝美學”這塊成問題的招牌不放呢?我覺得,除了理論上的糊涂之外,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顯然是某些人或某群人的權力和利益。首先,文藝美學似乎關系到在中文系開設美學課程的必要性,從而關系到像我這樣在中文系講授美學的人們的合法性。目前,中國大學的美學課程向來有哲學系和中文系之分。據說中文系的美學是“文藝美學”,而哲學系的美學則是“哲學美學”。對美學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會承認這種劃分完全是荒謬的。中文系和哲學系開不開設美學是一回事,美學是否可以劃分為文藝美學和哲學美學是另一回事。我做美學研究生的時候在哲學系,現在做美學教師的時候在中文系,因此,我對哲學系和中文系雙方力圖在美學研究上保持自身特色的所作所為頗為了解。但是,我對其學理依據頗為懷疑。也許存在哲學美學與心理學美學或社會學美學的分別,但根本不存在哲學美學與文藝美學的分別。我們把自己教育體制上的劃分及其缺陷夸大成了一種學科成立的依據。哲學美學與文藝美學的學科區分與哲學系美學與中文系美學的體制區分之間存在一種循環論證關系:前者證明了后者,后者也證明了前者。而這種循環論證的結果是確保了行政管理上的便利和某些人的利益,卻損害了美學學科本身的科學性。
事實上,在某個系科開設美學并不必須假定美學本身的內涵也要有所偏重。康德、黑格爾的美學是哲學的美學并非因為它們是在哲學系被講授的,而是美學的本質使然。這是極其明顯的道理。在中國,從哲學系畢業的學者之所以把美學搞得“哲學味”濃(往往等于概念化、抽象化)一些,從中文系或其他藝術院校和研究所畢業的學者之所以把美學搞得“藝術味”濃(往往等于形象化、具體化)一些,完全是自身的局限性使然,決不能由此認為存在哲學美學與文藝美學之別。
中國美學的現狀也是助長哲學美學與文藝美學之分的原因之一。我們的美學不知從什么時候起已經僵化為一套完全脫離藝術的相對抽象而固定的理論。它讓所有學習美學和研究美學的人都深深地陷入一個難以自拔的誤區之中。人們以為美學就是研究諸如美的本質、美的類型、美的范疇、審美文化、審美教育等等問題的一門思辨性學科。人們在一系列抽象問題上兜圈子,最后落得一個缺乏任何實質內容的“一般美學”的概念。這里的基本問題就是它遺忘了藝術對于美學的重要性。朱光潛先生晚年曾告誡年輕的美學研究者,脫離藝術而研究美不可能有實質性的成效,只會把美的問題弄得越來越糊涂。很不幸,今天的美學就證實朱光潛的說法。文藝美學的主張者們也許也是因為看到了當今中國美學的空洞,試圖通過強調藝術來使美學具體化。但文藝美學的提出本身就假定了這種空洞美學的有效性,它通過把后者稱為“哲學美學”而使之合法化了。文藝美學沒有澄清問題,而是增添了混亂。因為,既不存在某些中國學者所說的那種“哲學美學”,也不存在與那種哲學美學相對的“文藝美學”,存在的只有一種,那就是“美學”。
我們總是很不情愿去尋找自己扭曲某個學科的原因,而是過于自信,以為自己可以輕易地發現一門新的學科。在文藝美學問題上,許多人眾口一詞,盛贊中國學者的創造力。人們甚至可以援引后現代的某些理論為自己開脫。比如,人們可以宣稱:西方學者沒有發現文藝美學,并不意味著文藝美學不存在,斷言只有西方人有的中國人才應該有乃是“西方中心主義”作祟。于是,后現代主義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似乎為中國人證明文藝美學的存在提供了理論后盾。但是,文藝美學的維護者們忘記了一點:一門學科固然并不需要由西方人提出才具有存在合法性,但也決非可以隨心所欲地確立起來。我們固然不必在西方人面前自卑,但是也不必在西方人面前自信過頭。實際上,中國人建立文藝美學是否可能的問題說到底不是信心問題,而是能力問題。我們比西方學者聰明嗎?我們比西方學者在美學的學識和才能上勝過一籌嗎?何以他們沒有建立“文藝美學”而我們建立了“文藝美學”呢?我們老祖宗留下來的遺產顯然不足以讓我們站在一個更優越的位置上,我們也沒有得到上天特別的眷顧,我們憑什么認為自己居然擁有發現一個新學科的如此了不起的才能呢?
因此,我深信,文藝美學是一門很成問題的學科,它或許不過是人們出于各種原因所進行的一種虛構。為了美學學科的發展,我們有必要對它有一個明確的認識。一個莫須有的學科將大大助長現在早已存在且日趨嚴重的學術泡沫化現象,使學術更加陷入不良境況之中。鑒于文藝美學的確牽涉到某些人的現實利益,我們有必要呼吁美學學者們拿出一點學術良心來,勇敢地打破圍繞文藝美學所形成的那些幻覺。只有這樣,在面對世界其他地方的美學同行的時候,我們才不會顯得可憐可笑;也只有這樣,在面對那些熱愛美學的人們的時候,我們才不會變成一個自欺欺人的學術騙子。人人都說有的未必真的有,安徒生《皇帝的新裝》早就告訴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