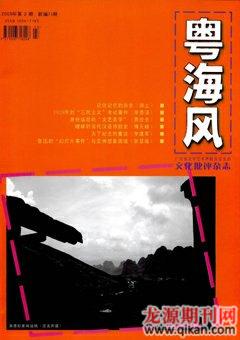傳統中國鄉村治理模式的宏觀透視
孫遠東
傳統中國國家如何實施鄉村治理,是一個饒有意味的學術話題。學術界愈來愈傾向于認為,中西方有著不同的文明路徑,這決定了傳統中國對鄉村基層的控制方式亦迥異于西方。在這方面,目前主要有三種觀點,可以稱之為三種認識范式(paradigm):
第一種是“主-佃關系”范式。
這種方式來自所謂“中國封建社會”理論,它描繪了一種尖銳對立的主佃關系,并且極力強調地主在這種關系中的絕對優勢。按這種說法,當時地主威福自恣,佃戶水深火熱,后者不僅被殘酷剝削,而且受到“代表地主階級”的專制政權蠻橫鎮壓。凡是主佃矛盾,官府一定為地主撐腰。直至矛盾激化,“主逼佃反”,發生代表佃戶的“起義軍”反抗“代表地主”的朝廷的“農民戰爭”。[1]這種范式主要認識資源是來自蘇聯的教條意識形態,長期以來影響深遠,但現在除了官方教科書中仍繼續沿用,已為學界主流所拒斥,但其實也不是全無意義。
第二種是“小共同體”范式。
這種范式的主要觀點是:在傳統中國社會,存在著兩種秩序和力量,一種是“官制”秩序或國家力量;另一種是鄉土秩序或民間力量。前者以皇權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級分明的梯形結構(trapezoid-structure);后者以家族(宗族)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大大小小的自然村落,每個家族(宗族)和村落是一個天然的“自治體”,這些“自治體”結成為“蜂窩狀結構”(honeycomb-structure)。 因此,傳統鄉村社會是散漫、和諧的自然社會,皇權政治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掛名的,無為的,而連接兩種秩序和力量的,是鄉紳階層。但是,鄉紳往往會偏重鄉村一方,因為他們的利益主要在地方上。秦暉對其作了完整的概括:國權不下縣,縣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這種范式的學術資源主要來自于海外中國學研究,其不僅與西方社會科學的認識邏輯合拍,也的確在中國尋找到大量的經驗支持,改革后傳播到中國立刻受到追捧和呼應,但近來愈益引起質疑[2]。不過有一點應該承認,這一認識范式在中國學術史上的意義是不容低估的。
第三種“大共同體本位”范式。
這一范式為秦暉一直所堅持,他在批判上述兩種范式基礎上反復強調:傳統中國鄉村社會既不是被租佃制嚴重分裂的社會,也不是和諧而自治的內聚性小共同體,而是大共同體本位的“偽個人主義”社會;與其他文明的傳統社會相比,傳統中國的小共同體更弱,但這非因個性發達,而是因為大共同體性亢進所致;傳統中國社會的典型景觀實是專制朝廷及其下延組織控制著一盤散沙般缺少自發社會的“編戶齊民”。近來,秦暉通過對20世紀末發現、1999-2000年起開始陸續公布的長沙走馬樓吳簡所見的極端“非宗族化”社會的研究發現:一方面,已發表的部分簡牘涉及的1532戶吏民的姓氏結構表明,姓氏雜居狀況十分驚人,顯示宗族活動微弱;另一方面,“國家政權”在縣以下的活動與控制卻十分突出,基層權力機構比我們所知的復雜得多,不僅有發達的鄉、里、丘組織,而且有常設職、科層式對上負責制與因此形成的種種公文程式。秦暉引述簡牘中一份“東海郡屬縣鄉吏員定簿”記載的當時兩個“鄉政府”的人員編制(原文有缺字):
山鄉吏員卅七人:相一人,秩三百石。丞一人,秩二百石。令史三人,獄史二人,鄉嗇夫一人,游徼一人,牢監一人,尉史一人,官佐四人,亭長四人,侯家丞一人,秩比三百石。仆行人、門大夫三人,先馬、中庶子十四人。凡卅七人。
[建]鄉吏員扇耍合嘁蝗耍秩三百石。丞一人,秩二百石。令史三人,獄史二人,鄉嗇夫一人,游徼一人,牢監一人,尉史二人,官佐五人,鄉佐一人,亭長四人,侯家丞一人,秩比三百石。仆行人、門大夫三人,先馬、中庶子十四人。凡扇恕
所列編制在今日也屬相當可觀,而且其中所列主要鄉吏的待遇,比正史所載要高出許多。[3]須知,傳統中國縣的規模是很小的。秦漢時期確立的“縣”僅僅相當于周代“末等封國”之地。秦時全國共設置“縣政”約為1000個,平均每縣所轄4000戶、20000人左右。漢平帝元始二年,全國共有縣級行政單位1587個,平均每縣所轄7711戶、37552人。東漢中興,平均每縣所轄8184戶、41477人,只是比西漢初期略大一些,更無論魏晉了。[4]
由此秦暉認為,中央集權國家控制下的鄉村社會是所謂“編戶齊民”社會,而世家大族及其部曲、宗族賓客則是朝廷控制不了或只能實行間接的“羈縻”式統治的地方,血緣共同體(所謂家族或宗族)并不能提供——或者說不被允許提供有效的鄉村“自治”資源,更談不上以這些資源抗衡皇權。他還說,在時間上這批簡牘形成的魏晉時期過去被公認為我國歷史上世家大族最盛的時代,但即使在這個時期,只要處在帝國官府的控制下,那里的鄉村仍然是編戶齊民的鄉村,如果這個時期的鄉村社會實況都不那么“宗族化”,那么其他時代文獻上所講的宗族意義究竟如何就更可疑了。這個時期的確存在家族組織與大族政治,但與所謂國權不下縣、縣下唯宗族的說法相反,這種大族活動恰恰是“縣以上”的高層政治現象,而與“縣以下”的平民社會幾乎無關。所以,秦暉對真實的傳統作出新的概括:國權歸大族,宗族不下縣,縣下唯編戶,戶失則國危。[5]
其實,上述三種認識范式不過是韋伯所說的“理想型”(ideal type),是對傳統中國經濟社會某一時段、某一側面現象的抽象。以傳統中國地域之廣闊,歷史之久遠,社會之復雜,經濟社會結構千差萬別,政制倫理千姿百態,各種型式都可能存在或摻雜在一起。如秦暉也提出的傳統中國社會既有以租佃制為基礎的“江南模式”,亦有以自耕農為基礎的“關中模式”,都有其經驗證據。[6]在明清以來宗族最為活躍的東南沿海,“倫理社會”的經驗感知更是俯拾皆是。其實,租佃模式主要是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時的產物,此前傳統中國的土地占有制度是“王有”前提下的均田制;小共同體模式也是宋時開始的“宗族重建”的結果,而且實際的收效,在南中國比較有效,即長江以南的丘陵山區的中國。北中國維系不足。有人認為這和元有關系,元朝的掃蕩,使北方已有的宗法組織機構,大體上被打掉了。元明戰爭,基本上發生在中國北方,即黃淮流域。黃淮流域人口發生了最劇烈的動蕩,人口耗盡了90%,這里的宗法組織基本上被打散了。[7]更何況,上述這些認識范式本身也不是我們想當然認為的那樣。如高王凌通過多年對傳統租佃關系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種認識景觀:在這里地主與佃戶雙方存在著利益上的持續較量。佃戶以拖欠、求讓、偷割私分、壓產、反退佃、辭佃、罷種、逃租及轉佃、恃強、構訟、交“濕谷”、“癟谷”,直到暴力反抗和有組織的斗爭等等方式爭取盡可能多的所得。而且他們的努力顯得相當有效,不要說沒有權勢的平民地主,就是像孔府那樣的貴族之家,也不是都能在主佃博弈中對佃戶穩占優勢的。[8]這就是說,中國歷代自耕農與佃戶的境況差別并不像有些說法講的那么大,傳統農村中佃農的處境未必像過去一些著述說的那么絕望,自耕農的境況也未必像一些著述說的那么值得向往。另一面的真實是:一旦王朝腐敗,橫征暴斂起來,自耕農乃至沒有優免權的平民地主常常都求為佃戶而不可得,形成嚴重的“投獻”、“蔭庇”與棄地逃亡現象。
但是在這里,我們必須關注的是:自秦漢以后,中國確立了“大一統”的專制國家的邏輯。這個邏輯一經確立,傳統中國就與西方文明再無交集。傳統專制國家不管是出于君主個人之私欲,還是為維護“家天下”長治久安之“公心”,都有一種將國家政權直接延伸到鄉村社會、在鄉村社會建立政權的基層組織、將鄉村社會納入統治秩序中的原始沖動。西方學者也發現了傳統中國的這一政治特征,“為了控制目的而把民眾分成小單位的基本思想,連同其變異形式和更細致的形式(最著名的是保甲制)在以后的帝國時代,甚至晚至民國時代仍行之不輟”。[9]把民眾分成小單位就是在鄉村基層建立一定行政區劃和管理層級,設立組織進行治理,區劃設置及名目五花八門,如鄉、亭、里、黨、閭、鄰、族、牌、都、圖、村、團、社、區、保、甲、什、伍等不一而足,縣以下管理層級或三級、或兩級、或直接管理到村,有的是縣及以上衙門的延伸,有的是縣以下基層組織,前者亦有可能演變為后者。秦暉有意思地發現:作為縣衙正式文吏的“勸農掾”竟演變為常設的鄉官,一如我國歷史上上級巡行之官不久就會演變成下面常設職(如刺史、行省、巡撫原來都是中央派下的巡查官,后來都變成常設的政區首長)。[10]我們把這些統稱為“鄉里制度”。國家通過這一套鄉里行政管理制度與其他配套制度(如戶籍制度,戶就是鄉里制的最小單位)結合,把民眾組織起來以提取資源、實施控制,這些按照戶籍和一定行政體制組織控制起來的民眾就是所謂“編戶齊民”,當然還有其他不同等級和貴賤之別的特殊戶籍,但兩千年來,中國最大部分人口,上不是貴族,下不是賤民,而是這些有戶籍,服徭役,納稅完糧的一般農戶,他們是傳統中國的統治基礎。國家通過一整套的鄉里制度與他們打交道。據此,秦暉的大共同體本位認識范式的解釋面更寬一些。
與上述三種認識范式相一致,傳統中國的鄉村基層控制方式理論上說就有兩種基本類型:一是國家通過在基層(縣以下)建立一定的行政區劃,直接通過官僚組織層層控制到每一個人;二是所謂“王權不下縣”,基層社會治理由地主、士紳、家族宗族、豪強等民間勢力主導,形成自身的內生秩序。這也是兩種“理想型”,實際上在歷史中并不是常態。一方面,國家固想一竿子插到底實現正式控制,囿于行政成本和交通、通信和組織技術等所限,“無遠弗屆”根本不可能;另一方面,小共同體的內生秩序構成的所謂“自治”也是有限的,即使統一專制國家瓦解之時,大小割據政權也隨時構成國家的替代,基層鄉村不是桃花源。
我們可以把上述兩種類型視作一個光譜的兩端,鄉村治理的更多類型是在兩端之間游走,無非是國家權力與鄉村基層力量之間此消彼長而已。漢唐時期世家大族聲勢煊赫,但國家在鄉村基層具有強大控制體系也有部分微觀證據,宋明以來形成的“士紳治理”格局也不意味著王權真的下不了縣。清代縣衙的職官除正印官縣令外,還設有佐貳官和屬官。佐貳官即縣丞與主簿,屬官有典史和巡檢等職設。其中縣令佐官主簿、屬官典史的官署通常設于縣城,而一部分縣丞的官署不是設于城里,而是設于縣內其他重要的鎮。這些設于城外的縣丞官署,民間常稱為“二衙”,實際上行使了次縣級權威體系的行政職能。巡檢司署一般也不設于縣城,大都設于關隘和遠離州縣治所的繁華之地,較之縣丞官署更具有明顯的派出性質。事實上,在中國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點,鄉村基層控制類型復雜多樣,變化無常,在哪里達成均衡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與鄉村基層勢力的博弈結局。國家難以一竿子插到底,就要尋求與基層精英的合作、共謀,不同的基層精英也須要援引國家的資源來實現個人的利益(精英層絕不是鐵板一塊);國家的官僚控制體系及下延組織有作為國家代理人的一面,也有維護社區利益乃至完全圖逞個人私欲的一面。但有一個根本的線索,就是上述傳統中國專制國家的邏輯,這個邏輯決定國家(及其各類變種)必然有竭力向下滲透的沖動,即設立代表國家的鄉里制度(也包括其他制度)以實現控制。這條線索可視之為“經”,是主線。而國家與在鄉村的代理人以及其他基層精英總有與國家的意志不一致的地方(國家本身也不是鐵板一塊),這條線索可視之為“緯”,是副線。傳統中國的鄉村治理結構和運作狀況概由此兩條線型塑。就像有的論者根據對晚清民國時期河北獲鹿的一項區域研究表明的:在帝國時代的大多數時間里,國家能夠在大部分地區榨取足夠的賦稅,以滿足正常的需要和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使這些成為可能的是林林總總的地方村社的非正式制度,這些制度是在國家需求和地方社群自發承擔日常政府職能的互動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所以用“治理”一次來描述這一國家權威和鄉村居民共同參與的過程也不無恰當之處。[11]必須指出的是,地方社群的“自發”無疑是被迫的,國家的需要占據主導地位。
學界普遍認為,唐宋之交是中國鄉里制度演變的轉折點,即由鄉官制向職役制轉變。隋唐時,中國鄉里制度已有從鄉官制向職役制變化之端倪。具體言之,應為唐中期。唐代時鄉里制度在制度規定上尚屬鄉官制,如組織設置仍屬職官志范圍,實際上唐中期鄉里制度在形式和性質上已發生變化,所設“里正”已有為人所“役”的苗頭,鄉里組織領袖之地位明顯下降。[12]到宋代,這一轉變得以完成。自此以后,鄉里制度職役性質日見明顯,鄉里組織領袖已名不符實,淪為縣以上統治者手中的工具,到明清兩代,鄉里組織領袖幾近成為“奴隸”,非復往日之榮光。其實二者區別沒有想象那樣大。不管鄉吏是有酬的美差還是強加的重役,都不是“鄉村自治”的體現者,而是國家權力下延于鄉村的產物,其為專制國家之控制工具之一。
[1]蘇文:《關于傳統租佃制的兩大認識誤區 》,《南方周末》2005年9月15日。
[2[[3][5][10]秦暉:《傳統中華帝國的鄉村基層控制:漢唐間的鄉村組織》,載黃宗智主編:《中國鄉村研究》(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34頁。
[4]張新光:《質疑古代中國社會皇權不下縣、縣下皆自治”之說——基于宏觀的長時段的動態歷史考證》,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4627
[6]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
[7]曹錦清:《宋以來的鄉村組織重建——歷史視角下的新農村建設》,http://www.zgxcfx.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7284
[8]高王凌:《租佃關系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
[9][英]崔瑞德、魯惟一:《劍橋中國秦漢史》,楊品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頁。
[11][美]李懷印:《華北村治——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國家與鄉村》,歲有生、王士皓譯,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2頁。
[12]趙秀玲,《中國鄉里制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