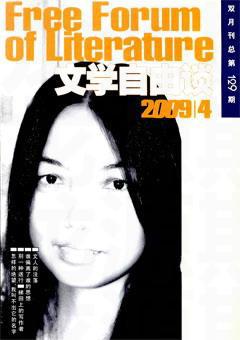一本中國人的必讀之書
李建軍
這本書既不是“紅寶書”,也不是“白皮書”;里面既沒有“生意經”,也沒有“升官圖”。它是一個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一筆一筆地寫給所有中國人的一份沉重的“遺書”,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必讀之書。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1978年12月,巴金開始了《隨想錄》的寫作。他痛定思痛,寫出了一大批樸實、深刻的雜文和隨筆。這些收入《隨想錄》的文章抒真情、說真話、破愚蒙、牖民智,標志著巴金的文學創作進人了一個嶄新的階段,登上了又一個輝煌的高峰。袁鷹先生在《<隨想錄>的啟示》一文中高度評價巴金的“憂心殷殷”的寫作:“五本《隨想錄》,不僅是巴金悠長的文學道路上的一座豐碑,也是‘五四以來我國現代散文史上的一座豐碑。有的評論家稱譽它為當代散文的巔峰之作,我完全同意這樣的評價。這部巨著,標志著我們時代最高的思想藝術水平,充滿了作家對社會生活、精神生活和道德情操的思考的光輝,完全可以同魯迅先生晚年的雜文相媲美。”比較起來,巴金的《隨想錄》也許不如魯迅的雜文那樣尖銳、有力,但是卻像它一樣真誠,一樣熱情,一樣勇敢;它也許不如《干校六記》那樣精致,那樣淡雅,但是,卻比它親切,比它偉大——《干校六記》的文字里隱隱地透著深秋的寒意,但是,《隨想錄》卻從內到外都吹拂著陽春的暖風。
《隨想錄》是一首悼亡的安魂曲。“文革”期間,巴金雖然九死一生,僥幸地活了下來,但是,他的志趣相投的朋友,卻一個個被迫害致死,尤其是與他相濡以沫的妻子蕭珊,剛剛51歲,便因為恐懼和絕望赍恨而歿。這些朋友和親人的死,給性格內傾、天性敏感的巴金帶來巨大的痛苦。“情往會悲,文來引泣”(《文心雕龍·哀吊》),巴金的《懷念蕭珊》、《紀念雪峰》、《悼方之同志》、《懷念老舍同志》、《趙丹同志》、《再憶蕭珊》等文章長歌當哭,寄慨遙深,曾經感動了無數的讀者。
《隨想錄》是一部勇于自省的懺悔錄。自我懷疑和自我批判是新知識分子的基本素質。魯迅說他固然時時解剖別人,但也更嚴格地解剖自己。巴金也是這樣。像魯迅一樣,巴金也勇于“嚴格地解剖自己”——他沒有僅僅把自己當做受害者,而是把自己當做被審視的對象,當做潛在的甚至事實上的“合謀者”。他說:“在那個時期我不曾登臺批判別人,只是因為我沒有得到機會,倘使我能夠登臺亮相,我會看做莫大的幸運。我常常這樣想,也常常這樣說,萬一‘早請示、晚匯報搞得最起勁的時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會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壞事。當時大家都以‘緊跟為榮,我因為沒有‘效忠的資格,參加運動不久就被勒令靠邊站,才容易保持了個人的清白。使我感到害怕的是那個時候自己的精神狀態和思想狀況,沒有掉進深淵,確實是萬幸,清夜捫心自問,還有點毛骨悚然。”(《解剖自己》)這段話,看似平淡無奇,實則非常深刻,深刻得令人“毛骨悚然”:在一個誘使人犯罪的極端可怕的環境里,個人的理性意識和道德自覺,實在太脆弱,實在太無力。所以,重要的是改變環境,完善制度建設,只有這樣,才能把人從不安全的危境里解放出來。
《隨想錄》更是一部“述往事,思來者”的憂患之作。做為中華民族千年未有之“變局”,做為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文革”不僅使中國的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而且對中華民族的文化結構和道德秩序造成了巨大的破壞。社會各階層的人們都受到了沖擊,從國家主席到普通百姓,都付出了巨大的甚至生命的代價。以傳承文化為職志的知識分子,在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中,更是首當其沖,受盡折磨,被迫說不想說的話,被迫做不愿做的事。他們被當做“牛鬼蛇神”,關押進“牛棚”,被遣送到“干校”和“勞改農場”,在身體和精神兩方面,都遭受了嚴重的打擊和傷害,留下了極為嚴重的后遺癥。巴金說:“我至今心有余悸,只能說明我不堅強,或者我很軟弱。但是十年中間我究竟見過多少堅強的人?經過接連不斷大大小小的運動之后,我的不少熟人身上那一點鋒芒都給磨光了。有人‘畫地為牢,大家都不敢走出那個圈圈,仿佛我們還生活在周文王的時代。”(《紀念》)像其他許多優秀的作家一樣,巴金也被當做罪大惡極的“犯人”,有人甚至對他說:“根據你的罪行,判你十個死刑也不多。”(《“友誼的海洋”》)他受盡了侮辱,曾經被迫跪在“領袖像”前“請罪”。他認認真真地改造自己,但是,無論他怎么努力,仍然無法成為“好人”。張春橋惡狠狠地說:“不槍斃巴金就是落實政策。”又說:“巴金這樣的人還能寫文章嗎?”(《究竟屬于誰?》)盡管如此,巴金并沒有喋喋不休地訴說自己的委屈和不幸。在他看來,“文革”不只是哪一個人的災難,也不只是中華民族的災難,而是全人類共同的災難;它不僅同中華民族有關系,而且同世界人民有關系,所以,他說:“我們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個能說服人的總結,如何向別國人民交代!可惜我們沒有但丁,但總有一天有人會寫出新的《神曲》。”(《說真話》)
“文革”是封建主義的大泛濫。《隨想錄》的核心主題就是反思并揭示“文革”的封建主義本質;它的鋒芒所向,就是反專制,反愚昧,反對壓抑人性、踐踏人類尊嚴的昏暴。正像一位評論家撰文指出的那樣:巴金“鞭撻‘四人幫、批判封建專制、反對現代迷信。……他對于那種強加于人、愚弄人民、搞蒙昧主義、人云亦云等等思想僵化、封建專制的做法特別反感。”巴金繼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封建”的精神傳統。他反復強調“五四”對自己的影響:“我說我是‘五四的兒子,我是‘五四的年輕英雄們所喚醒、所教育的一代人。”他為“五四”辯護,贊美“五四”的青春激情,提醒人們警惕精神的“老化”:“‘五四的愿望到今天并不曾完全實現,‘五四的目標到今天也沒有完全達到。但這絕不是‘五四的錯。想不到今天我們之間還有人死死抱住那根腐朽的封建支柱,把幾千年的垃圾當做基石,在上面建造樓臺、寶塔。他們四處尋根,還想用我們祖先傳下來的準則‘行事、做人。”(《老化》)巴金對“文革”的本質有著深刻的認識,始終保持著清醒的批判態度:“在十載‘文革中我看夠了獸性的大發作,我不能不經常思考造反派怎樣成為‘吃人的虎狼。我身受其害,有權控訴,也有權探索,因為‘文革留下的后遺癥今天還在蠶食我的生命。我要看清人獸轉化的道路,不過是怕見這種超級大馬戲的重演,換句話說,我不愿意再進‘牛棚。”(《人道主義》)
那么,“文革”為什么會發生?人是怎樣變成“獸”的?人們的心上留下了怎樣的傷痕?我們到底付出了什么樣的代價?誰應該為這一切負責?怎樣才能避免這樣的悲劇和災難再次發生?進人“撥亂反正”和“解放思想”的“新時期”,巴金開始了痛苦而深刻的反思。他在《絕不會忘記》一文中提醒人們在“向前看”的同時,一定不要忘記“文革”災難,警惕漸漸抬頭的“健忘癥”:“我們背后一大片垃圾還在散發惡臭、污染空氣,就毫不在乎地丟開它、一味叫嚷‘往前看!好些人滿身傷口,難道不讓他們敷藥裹傷?……難道為了向前進,為了向前看,我們就應當忘記過去的傷
痛?就應當讓我們的傷口化膿?”他的以“說真話”為原則的雜文、隨筆寫作,亶亶不置地追問著的,就是這些與中華民族的未來命運密切相關的重要問題:“過去的十年太可怕了!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不允許再發生那樣的浩劫。我一閉上眼睛,那些殘酷的人和荒唐的事又出現在面前。我有這樣一種感覺:倘使我們不下定決心,十年的悲劇又會重演。”所以,“更重要的是:給‘十年浩劫作一個總結。我經歷了十年浩劫的全過程,有責任向后代講一點真實的感受。大學生責備我在三十篇文章里用了四十七處‘四人幫,他們的天真值得人們羨慕。……在今后的《隨想》里,我還要用更多的篇幅談‘四人幫。‘四人幫絕不止是‘四個人,它復雜得多”。(《<探索集>后記》)。順著這一思路,巴金將自己對“文革”的反思,推向了新的高度。他在十幾歲讀《說岳全傳》的時候,就產生了這樣的疑問:秦檜怎么會有那樣大的權力?“順著思路前進,我終于得到了解答”。這個解答就在明代詩人兼畫家文征明的詩句里:“笑區區一檜又何能,逢其欲。”巴金說:“這個解答非常明確,四百五十二年前的詩人會有這樣的膽識,的確了不起!但我看這也是很自然的、很尋常的事,順著思路思考,越過了種種的障礙,當然會得到相應的結論。”(《思路》)巴金是智慧的,也是勇敢的,他于1982年5月6日寫下的這段文字,實在應該成為我們反思“文革”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思路”。
反智主義是封建主義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在封建主義肆虐的地方,“知識即罪惡”,知識分子則是犯有原罪的人。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巴金就被戴上了“緊箍咒”,“這以后我就有了一種恐懼,總疑心知識是罪惡,因為‘知識分子已經成為不光彩的名稱了。我的思想越來越復雜,有時我甚至無法了解自己。我越來越小心謹慎,人變得更加內向,不愿意讓別人看到真心。我下定決心用個人崇拜來消除一切的雜念,這樣的一座塔就是建筑在恐懼、疑惑與自我保護上面,我有時清夜自思,會輕視自己的愚蠢無知,不能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哪里有什么‘知識?有時受到批判、遇到挫折,又埋怨自己改造成績不大。總之,我給壓在個人崇拜的寶塔底下一直喘不過氣來”。(《“緊箍咒”》)因為“知識”意味著發現真相和問題的能力,意味著良心的自覺和批判能力的成熟,意味著對愚昧力量的不合作與不服從,所以,“那些人就是害怕知識分子的這一點點‘知識,擔心他們不聽話,唯恐他們興妖作怪,總是挖空心思對付他們,而且一代比一代厲害。……我本來‘知識有限,一身瘦骨在一次又一次的運動大油鍋里熬來熬去,什么‘知識都熬光了,可是卻給我換上一頂‘反革命的大帽……罪名仍然是:我有那么一點點‘知識”。(《再說知識分子》)
如果說“仇智主義”必然導致謊言的流行,必然使很多人把“說假話”變成一種消極的習慣,那么,“啟蒙主義”則強調真理的價值,必然把“說真話”當做個人和社會生活的重要原則。“說真話”是巴金在《隨想錄》中反復涉及的話題,他曾經寫過至少四篇專門談論“說真話”的文章;“說真話”也是他“晚年奮斗的目標”(《說真話之四》),是在《隨想錄》寫作過程中身體力行的寫作倫理。他之所以如此不遺余力地提倡“說真話”,是因為經過了“文革”,說假話已經成為一種令人擔憂的社會現象:“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間,說謊的藝術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謊言變成了真理,說真話倒犯了大罪。我挨了好幾十次的批斗,把數不清的假話全吃進肚里。”(《說真話》)那些“永遠正確的人”更是把說假話當做家常便飯,“本人說話從來不算數,別人講了一句半句就全記在賬上,到時候整個沒完沒了,自己一點不臉紅。……他們的嘴好像過去外國人屋頂上的風信雞,風吹向哪里,他們的嘴就朝著哪里”。然而,“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再論說真話》)在他看來,“文革”本質上就是一場說假話、做假事的運動,——在說假話上,有的人比“封建官僚”還要可怕:“我不明白在他們身上怎么會有那么多的封建官僚氣味?!他們裝模作樣,虛張聲勢,唯恐學得不像,其實他們早已青出于藍!封建官僚還只是用壓力、用體刑求真言,而他們卻是用壓力、用體刑推廣假話。”(《說真話之四》)顯然,巴金關于“說真話”的議論,主要針對“文革”而發的。
從藝術上看,《隨想錄》屬于高度自覺和成熟的寫作。與“說真話”的精神姿態相應,巴金的《隨想錄》在敘述方式和語言形式上顯示出一種很可寶貴的品質——洗盡鉛華,去除雕飾,表現出一種質樸、清真的風格。在浮華侈麗的“純文學”很受推崇的時代,在“為文造情”的寫作大行其道的時代,巴金的這種寫作的價值和意義,很容易被誤解,甚至很容易被貶低。1980年香港的一位教授寫了一篇題為《我們對巴金<隨想錄>的意見》的文章,選錄了“港大”學生的“七則同題簡論”,表達了他們對《隨想錄》的失望和不滿。一位張姓學生說:“全書不過三十篇短文,但單是‘四人幫就出現了47次之多。”一位李姓的學生說:“《隨想錄》的缺點正是忽略了文學技巧,以致文字意義太膚淺,太表面化。”一位蘇姓的學生則說:“全書內容結構松散、缺乏張力,文字累贅,令人看得懨懨欲睡。”一位方姓的學生的判斷更是斬釘截鐵:“容我大膽下一個結論,就文學的觀點而言,《隨想錄》是一本徹底失敗的作品。”
對于“港大”學生的批評,巴金坦率地陳述了自己的觀點:“最近有幾位香港大學生在《開卷》雜志上就我的《隨想錄》發表了幾篇不同的意見,或者說是嚴厲的批評吧:‘忽略了文學技巧、‘文法上不通順等等,等等。迎頭一瓢冷水,對我來說是一件好事,它使我頭腦清醒。我冷靜想了許久,我并不為我那三十篇‘不通順的《隨想》臉紅,正相反,我倒高興自己寫了它們。從我闖進‘文壇的時候起,我就反復聲明自己不是文學家,一直到今年四月在東京對日本讀者講話,我仍然重復這個老調。”巴金從來就不是一個“純文學”論者,而是一個把寫作的目的和目標看得很重要的作家,因此,他一直反對那種迷戀技巧的傾向,討厭那些繁采寡情的寫作:“有人得意地夸耀技巧,他們可能是幸運者。我承認別人的才華,我缺少這顆光芒四射的寶石,但我并不佩服、羨慕人們所謂的‘技巧。當然我也不想把技巧一筆抹殺,因為我沒有權力干涉別人把自己裝飾得更漂亮。每個人都有權隨意化妝。但是對裝腔作勢、信口開河、把死的說成活的、把黑的說成紅的這樣一種文章我卻十分討厭。即使它們用技巧‘武裝到牙齒,它們不過是文章騙子或者騙子文章。這種文章我看得多了!”(《探索之三》)
“港大”學生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觀點?為什么會如此嚴重地誤解巴金?這其實不難理解。首先,他們與巴金活在兩個世界里——他們沒有嘗過饑餓的滋味,也沒有受過無情的“打擊”,沒有感受過親人之間被迫生離死別的痛苦,不知道“四人幫”和他們的幫兇有多么惡毒,不知道被人當做“毒草”和“牛鬼蛇神”有多么可怕。他們似乎壓根不知道“文革”為何物——這也難怪,在內地,真正了解“文革”的大學生又有多少呢?其次,在他們的觀念里,文學的要義甚至全部內涵就是“形式”和“技巧”,就是“張力”和“陌生化”;一部作品越是讓人看不懂,便越好,相反,越是讓人一看就懂的,則越是不好。巴金的《隨想錄》清明、素凈,如秋水澄澈,似晴空無云,自然不合這些按照“標準化”模式培養起來的“現代”大學生的趣味傾向和評價標準。他們不知道,“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樸素其實是很難掌握的一種風格,也是很難抵達的一種境界。
《隨想錄》是樸素的,但卻并不蒼白;它是溫雅的,但卻內蘊著莊嚴的憤怒。它是一杯上等的淡茶,細細品味,便覺得余香滿口。它是一本說真話且包含著大愛的憂患之作,是值得每一個中國人懷著感恩的心情認真閱讀的一本大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