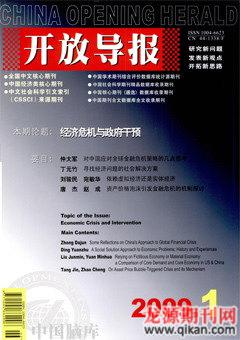原生市場、轉型市場與經濟特區
鐘 堅 羅海平
[摘要]原生市場起源的內在規律同樣支配著轉型時期市場經濟的形成。市場內在化起源于共同體的邊界和盡頭,特區模式是我國非均衡。漸進式對外開放和轉型市場形成的帕雷托改進。作為內地共同體的“人擬邊界”,特區充當了共同體與外部世界的“市場集聚地”和“交換中介”。而作為“公共產品”,特區既要為轉型市場提供試驗,又需迅速成為漸進市場化“誘致極點”。特區功能的實現取決于舊體制能否生產出具有“改革家精神”的“改革家”。因為“改革家”是中國式轉型經濟的獨特增長要素,是“經濟增長的國王”。
[關鍵詞]原生市場轉型市場經濟特區改革家精神
[中圖分類號]F127.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6623(2009)01-0084-05
[基金項目]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五”規劃20017年度一般項目“廣東經濟特區發展歷程與經驗研究”(項目編號:07POI)、深圳市“十一五”哲學社會科學規劃2007年委托課題“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0周年歷史與經驗研究”(項目編號:115D006)和深圳市宣傳文化基金項目。深圳改革開放史”(項目編號:ND2007-1208)。
[作者簡介]鐘堅(1965-),江西萬安人,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經濟特區研究。羅海平(1979-),四川南充人,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從事經濟特區研究。
(一)市場內生于共同體的邊界和盡頭,經濟特區是計劃經濟轉型時期的特殊產物,特區從計劃經濟共同體中分離出來后,充當了內地共同體與外部世界的“市場集聚地”和“交換中介地”
我國市場化的一個最重要特征就在于它不是一個自然進化的過程,而是一個由與市場經濟互否的計劃經濟在人為作用下漸進轉型的過程。在這種“人工速成市場”或“外置市場”的條件下,市場的形成不再經由偶然物物交換、商品關系的進化路徑,也沒有從商品交換的出現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的漫長過程。但原生市場起源的內在規律同樣支配著轉型經濟中市場經濟的形成。根據馬克思的市場起源說,市場從不同人類共同體之間的交換開始,而市場化則是這種起源于不同共同體邊界或盡頭的市場關系向人類共同體內部滲透的過程或者說市場內在化的過程。在我國漸進式誘致轉型和市場經濟的形成路線圖中,經濟特區是“人工選擇”的市場最早萌發地,充當了我國空間非均衡漸進式市場化路徑的起點。
市場的本質是交換,“物體身存在于人之外,因而是可以讓渡的。為了使讓渡成為相互的讓渡,人們只須默默地彼此當作被讓渡物的私有者,從而彼此當作獨立的人相對立就行了。然而這種彼此當作外人看待的關系在原始共同體的成員之間并不存在……商品交換是在共同體的盡頭,在它們與別的共同體或其他成員接觸的地方開始的。但是物一旦對外成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在共同體內部依然成為商品。”為此,要在共同體中形成交易和市場必須將共同體成員外化,特區是部分的外化對象。經濟特區與非特區分化后,于是出現了特區與非特區共同體的內向交換市場,并通過反作用逐漸使共同體非特區間出現交換關系、商品關系,并逐漸市場化。另一方面,經濟特區由于享有與外部世界(尤其是港澳臺)按照國際規則直接進行貿易往來的政策優勢,這樣特區成為了連接內地共同體與外部世界的“市場集聚地”和“交換中介地”。世界市場經由特區向內地共同體滲透,從而內地間接地通過移植“外部市場”或由外部市場誘發內地原生市場實現市場內在化。
馬克思認為,市場作為人類社會進行物質交流、借以維持分工生產的一種經濟方式是從不同的人類共同體之間充滿敵意的對立中產生出來的。市場關系的產生意味著社會的利益單位與社會共同體開始分離,而分離的程度與市場關系的發展成正比。但是我國所要確立的市場經濟并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市場經濟,而是由中央政府主導下的有計劃的市場化,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此,特區從內地共同體分離出來,并不是完全的“外化對象”,而僅僅表現為具有“市場交換”的獨立性,而不是“敵意的對立”。且隨著這種相互間“交換關系”的深入、反作用的強化以及內地非特區間商品關系的廣泛確立,內地作為一個共同體相對于特區而言會逐漸分解,商品關系將使得共同體內部不斷分離出市場的獨立主體。尤其是隨著內地私營、個體企業的產生,國有企業之間、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之間、各類企業之間以及作為市場交換主體的個人之間都可以具有獨立的“交換”關系,都可從共同體中分解出來。這樣通過市場內在化把傳統上依賴于家族或組織單位等共同體的個人轉化為獨立的“社會人”,讓個人轉變為社會的基本單位。特區與作為共同體的內地市場的競爭關系,一直持續到內地非特區與特區具有同等市場交換關系。深圳特區早期與內地非特區地方政府、企業、單位等進行的“內聯”,所反映的就是共同體內部獨立市場主體的形成方式之一。對于這種獨立的競爭關系,愛因斯坦認為“達爾文的生存競爭以及與此相聯系的選擇理論己被許多人作為鼓勵競爭精神的權威依據來引用。也有一些人用這種方法試圖偽科學地證明個人之間毀滅性的經濟競爭的必要性。但這是錯誤的,因為人們進行生存競爭的力量,完全在于他是一個社會性的生活著的動物。正如蟻家中單個螞蟻之間的戰爭對于生存沒有什么根本意義一樣,人類社會中個體成員之間的斗爭也是如此。”盡管商品關系分離出不同的具有獨立物質利益主體身份的群體或者個人,但在現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中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市場是人類創造出來激勵自己的經濟形式,而不是毀滅自己的形式,市場需要競爭者,而不是毀滅競爭者而最終造成壟斷”。
(二)“轉型市場”的形成與原生“進化市場”具有本質區別和特殊性,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市場具有自身特色,選擇非均衡特區模式的市場經濟形成路徑是原體制的帕累托改進
轉型條件下的市場形成具有原生市場自然進化所沒有的特殊性。首先,中國原生市場和計劃經濟沒有將中國的城市化、工業化達到現代工業國家的水平,故中國當前的轉型按照戴維·哈維的分析是一個“時空壓縮”的過程。而“時空壓縮”過程中所積蓄的彈性勢能在釋放中必然帶來矛盾驟發和急劇的形變;其次,轉型是由最不具有市場因素且與市場“相生相克”的完全反面(傳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必然會面臨更多的“路徑依賴”和“傳統勢力”障礙;再次,轉型過程由計劃經濟內部的最高堡壘“中央政府”主導和“自改”,這樣市場化本身就是一個計劃的過程,使得市場經濟帶有更多的計劃色彩,從而帶來市場的“變形”和“市場計劃性”。基于以上的轉型特征,在市場內在化的過程中將受到來自傳統社會結構、特殊利益集團以及社會大眾的認知等多方面的制約。所以,在中國實行激進式市場轉型即休克療法會帶來“時空壓縮”彈性勢能釋放所帶來的劇烈反彈,甚至引發“爆炸效應”。為此,在路徑設計
上要求實行非均衡市場化,化整為零,分化市場化阻力,走漸進式道路,逐步釋放“時空壓縮”的彈性勢能。而在策略上,需從計劃體制勢力和意識形態影響最薄弱、遠離政治場而距離成功市場經濟最近的局部地方開始“市場試點”。這樣更便于市場機制的獨立作用,從而減少計劃經濟傳統體制對市場試驗的干擾;在執行力上,要盡量減少計劃體制利益集團的反對和阻礙,實行“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分化計劃體制下的官僚群體,培育各級政府的“改革家”,強化由改革家主導的政府權威;在目標模式上,從建設公民社會人手,按個人物質利益原則,培養并擴大民間市場受益主體,為個體與私營經濟的發展和資本自積累創造條件。
但經濟特區畢竟是計劃經濟的產物,是計劃經濟與轉型市場經濟結合的“異體”。特區經濟上優先市場化的“特殊”,必然要以政治上的“特殊對待”為前提。因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治資源決定經濟資源的分配。“特殊優惠政策”是高度稀缺的資源,這種稀缺資源分配給誰,取決于政策資源的配置者——中央政府的偏好,或下級與上級之間的博弈。實施特殊優惠政策,一方面意味著原體制不再是“鐵板一塊”,很快特殊優惠政策所帶來的非均衡性迅速轉化為破壞舊體制、建立新體制的催化劑。另一方面,特殊優惠政策是歧視性待遇,必然帶來非均衡經濟利益分割。而這本身有違市場經濟所固有的原則——即平等競爭原則。所以,經濟特區所享有的“特殊政策”具有歷史性,并不會長久“特”下去,必然隨著內地市場的發育而不斷向自由市場收斂,特區的公共屬性將不復存在。
(三)非均衡、漸進性、局部突破是我國解決資本積累、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體形成模式的路徑選擇,而經濟特區構成了空間非均衡漸進改革的起點
中國在歷史上一直存在著原生市場的進化,但進展緩慢,且未能來得及進入工業市場經濟時代就被迫接受西歐工業國家的“外置市場”。解放前中國的市場經濟正是積弱的原生市場和外置市場的混合體。解放后30年計劃經濟把交換關系、商品關系、市場經濟都當作“資本主義的尾巴”割掉,市場經濟的進化、移植和發育被人為中斷。由于意識形態的選擇偏好,社會主義所能允許的市場經濟亦不再是市場主體相互“對立”和“敵意”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是“獨立”與“競爭”的現代市場經濟。在西方,盡管市場內在化的關鍵一步是通過資本原始積累來實現的,而資本原始積累方式無一不是充滿“戰爭”“血腥”“掠奪”。后發而落后的中國不可能走資本原始積累舊路,這既是社會主義性質所決定,也是“轉型市場”區別于“原生市場”的內在特質所決定的。為此,在中國,市場主體的資本積累只能通過如下途徑實現:(1)原有計劃主體的資金向企業市場資本轉換(通過國有和集體企業改制和產權變更實現);(2)給個體市場主體地位,由個體通過自身積累實現,如個體戶;(3)國家通過非均衡分配發展機會,為市場經濟發展潛力好的地區或最能利用外部市場環境的地區提供和創造優先發展機會。通過內外尤其是外部要素優先集聚,迅速形成“市場發展極”和“資金富礦”。(4)計劃體制內部設租,通過“腐敗”使公有資本迅速實現私有化(資本的生產性不變)。以上方案中,方案(1)由于國有和集體企業路徑依賴比較強,會存在效益和物質激勵的問題;方案(2)屬于鼓勵對象,但存在局限性和一定發展瓶頸,而且私人資本積累不具備可控性,不利于市場化進程的計劃性;方案(4)屬法律禁止或疏漏,會帶來嚴重的不公平,引發更大的市場化“內斥力”。惟有方案(3)一方面市場化進程政府可控,另一方面由于非均衡要素“納化效應”(流向特區、開發區、發展新區等),容易在短期內集聚成“極點”,極點形成后制度的空間誘致才能得以引發。
中國非均衡的空間漸進發展模式——特區發展模式即是基于方案(3)。鄧小平指出“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點,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這既是中國的改革開放路線圖又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轉型的路徑規劃。基于這種非均衡發展思想,1978年中央決定進行經濟體制改革,1979年開始啟動深圳、珠海“出口特區”建設;1980年起建立了4個經濟特區;1984年進一步開放了14個沿海城市;1985年后又陸續形成了沿海經濟開放帶;1988年海南省辦特區;1990年開發、開放上海浦東新區,并進一步開放一批長江沿岸城市,形成了以浦東為龍頭的長江開放帶;1992年以來,又決定對外開放一批邊疆城市和進一步開放內陸所有的省會、自治區首府城市。至此,中國形成了沿海、沿江、沿邊、內陸地區相結合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對外開放的格局。在這幅空間漸進改革開放和市場化的路線圖中,起點就是經濟特區。它由中央政府劃定,并置之于改革開放的最前沿,視其為我國開放和發展層次最高的經濟區域。特區是內地共同體分化出來的“隔離體”具有相對“獨立性”,其資金來源以外資為主,而原料來源和產品則以外銷(境外)為主。同時根據自身的資源稟賦主要發展“三來一補”的勞動密集型企業,這樣自由度大、受政府的干預很小。再加之港澳國際市場高度發達、要素價格懸殊,所以特區與外部國際市場具有很大的產業轉移的“俯沖勢能”,特區一旦開放,必然發展迅速。
(四)中央與特區政府特殊關系的“試驗”為中央政府應對全面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問題和矛盾提供了“預知”和經驗,為有計劃釋放矛盾和解決問題創造了條件
“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偉大創造,需要從理論和實踐進行許多艱辛的探索,而真正把這種新的經濟體制全面建立和完善起來,則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江澤民的這段論述體現了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艱巨性。因為一方面世界上沒有成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參照系,另一方面,長期來中國的制度環境和意識形態與市場經濟格格不入。所以無論是本土市場進化和還是外來市場移植在舊中國都不成功。這與中國傳統社會根深蒂固的官僚屬性,缺乏獨立的個人物質利益主體分不開。所以,無論是孫中山“三民主義”,還是毛澤東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再到鄧小平的“放權讓利”,“三個有利于”以及江澤民“三個代表”和當前“以人為本”,貫穿其中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對無所不在的中國傳統式的官僚體系的否定或懷疑,對獨立個體人的重視。為此,在中國要推動市場的內在化,只能從觸動官僚體系開始。但是,數千年的家族社會早己給中國人打了家族或小集團利益至上的烙印,尤其是30多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將中央集權推向了極至。按照前面的分析,在民眾意識
和力量還很弱的情況下,向市場經濟轉型只能是“借力發力”。一方面,適當引導舊體制的“路徑依賴”,借助計劃的行政體制和意識形態實現轉型制度環境的相對穩定;另一方面,借助計劃體制的中央集權強制推動市場化,同時保證市場化進程的計劃性、受控性。
但市場經濟的改革不是“它改”而是“自改”,是傳統體制下的自我改革,改革受路徑依賴和政治家自身改革意識的影響較大。由此形成的市場經濟與原生自然進化的現代市場經濟必然存在一些人為的變形和扭曲。比如,由計劃到市場一個重要轉變就是,中央對地方、對特區的權力下放,但這個過程往往伴隨權力的欲放不能、欲收不忍的反復,“放權讓利”演變為各級政府和部門“爭權奪利”的博弈。總之,中央集權的行政管理體系對于市場經濟的形成是一把雙刃劍,存在一個“諾斯悖論”:一方面,它為制度變遷社會穩定所必需,作為實現穩定的工具和強制的“政策推力”,它必須完全為中央政府所控制,需要強化集權。另一方面,市場化要求中央必須放權,還權于民或還權于“市”。所以,經濟特區的出現是中國式計劃體制改革的特殊產物。通過自上而下局部試辦經濟特區,由中央政府對特區政府的“權力下放”以及給予特區政府的市場經濟試驗的自由權,為理順市場經濟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系進行了“演習”,也為特區贏得了謀求自身發展的先機。這樣就對全面市場化改革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有了一定心理準備和應對經驗,這樣便于讓各種市場化所帶來的問題和矛盾得以“先易后難”有計劃地釋放。
(五)特區的公共性要求特區為內地共同體提供市場經濟形成的“實踐經驗”,另外特區要能成為“誘致變遷”的極點,必須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經濟增長市場”的出現,使得特區試驗的成敗成為中央政府和其他非特區的公共產品
徐現祥、陳小飛(2008)認為,特區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特區的“試驗性”是由中國轉型中“經濟增長市場”決定的。在設立經濟特區之初中央已經給予了明確的定位:先行一步,試驗出可供推廣的如何改革開放才能促進經濟增長的方法、模式。但問題是,這些成功的方法、模式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是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一般應由中央政府提供,特區之所以愿意提供,徐現祥、陳小飛認為是由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了一個“經濟增長市場”。中央政府是經濟增長的需求方,支付的是財政收入、政治晉升等;眾多的地方政府是經濟增長的供給方,得到的是政治晉升等。由于這個經濟增長市場是買方壟斷的,地方政府官員為增長而競爭,而且是錦標賽式的競爭。在試驗期,中央劃出一塊區域設立特區,授權在該區域內先行一步。把特區與國內其它地區隔離開來,從而特區試驗結果具有了“暫時”的排他性,試驗結果的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并不會發生大的背離。因此,特區積極試驗。一旦試驗出如何改革開放促進經濟增長的方法、模式,并通過這些方法、模式取得示范性的增長績效,為增長而競爭的其它地方政府官員,自然有動機學習特區的成功做法以促進本地區的經濟增長。因此,當中央政府開始推廣特區成功的做法時,其它地區會積極響應,最終全國各地改革開放促進經濟增長的方法、模式趨同。徐現祥、陳小飛(2008)認為,這種試驗——推廣——趨同模式不僅使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而且是相對平穩地增長。
特區的最主要職能在于試驗,其次才是作為“經濟增長極點”的建設。如何進行試驗、從何處開始試驗?這必須遵循成本——收益和李嘉圖比較優勢原則。為此,獨特的區位和政策優勢促使特區從引進外資最需要的地方開始經濟體制試驗,從要素市場到產品市場、從局部改革到全面改革,逐步引進了市場經濟體制。至1987年。深圳已經在計劃體制、企業體制、價格體制、流通體制、財政體制、信貸體制、外貿外經管理體制、外匯管理體制、勞動人事制度、工資制度、基建管理制度等方面進行了改革試驗,從而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已搭建好,市場經濟體制已在深圳得到提前演練。
鑒于經濟特區自身的公共產品屬性,試驗的成果和經驗并不為特區所獨有,而是基于局部試驗、全面推廣,所以試驗結果無論成與敗都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因為,一旦經濟特區試驗出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法、模式,就會上升為中央政府的轉型知識儲備,最后通過中央決策在全國推廣,成為正式制度。另外,特區也以非正式制度變遷即“制度內滲”來促進內地共同體市場的發育。由于中央放權讓利以及漸進式市場化使得內地非特區地方、企業和個人漸漸成為獨立利益主體,利益驅使它們積極尋求與特區的獨立合作或合作開發經濟特區建設,從而促進了市場實踐、市場觀念和官員市場意識的“內滲”。而特區則以“內聯”方式邀請國內其它地區官員、部門和公司負責人來特區參觀學習與合作,即時將經驗影響到內地。這樣參與特區合作、特區開發以及與特區產生業務往來的獨立主體獲得了發展的先機,成為繼特區后又一個個誘致變遷的分散“次極點”,為內地市場的“燎原”布下了“星星之火”。
而對經濟特區來說,區域經濟誘致式發展和市場經濟的誘致性形成路徑,都要求存在一個發展和變遷的“高勢能”點,即“誘致極點”或“增長極”。經濟特區作為空間漸進式改革的起點,特區功能能否實現首先在于特區作為“增長極”和“誘致極點”是否真正能實現。而特區要在短時間內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成為引領全國的“增長極”和制度變遷的“誘致極點”,必須舉全國之力來保證實現。而在“中央沒錢,你們要自己殺出一條血路來”的情況下,特區只能定位為主要依靠港澳臺以及海外華僑的投資來進行基建。特區這種“對外”的特殊地位,對于需要完成出口和外匯計劃的內地省市和中央部門以及大型國有企業來說,與特區合作共同引資無疑是雙贏的。因為在特區開發的早期,無論是深圳、珠海、汕頭還是廈門,都是從零開始,毫無工業和基礎設施可言,資金極其貧乏,在這種情況下是很難吸引外商投資的。而內地非特區的許多省市卻在計劃體制時期具有相當的工業實力。所以在早期,特區避開中央直接與內地省市和部門、企業進行合作共同開發特區,盡管與特區發展外向經濟相背并飽受爭議,卻依然得到中央的“默許”。這構成了經濟特區加速自身發展的“捷徑”,為后來大規模發展外向經濟爭得了時間、奠定了基礎。
(六)特區“誘致極點”形成的決定要素是從政治家群體分離出來的改革家,而特區的試驗性形成了對“改革家”和“敢闖、敢冒”的“改革家精神”的需求
轉型市場的形成與原生市場的自然進化不一樣,是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制度變遷過程,是計劃經濟的中央集團發起的“自我改革”。而要實現這一點必然要求原官僚體系能分離出自上而下的“改革家”。改革家和改革家的精神是中國式轉型經濟的突出現象。改革家是計劃經濟政治家中游離出來的主導舊體制改革的政治家,改革家是計劃經濟主動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推手”。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市場,企業家是“經濟增長的國
王”,而在類似中國的轉型經濟中“改革家”卻是實實在在的“經濟增長的國王”。特區改革家扮演著類似于企業“職業經理人”的角色,承擔著特區試驗和特區經濟增長的雙重責任。但特區的公共產品性質決定了特區建設的風險和成本并不完全由經濟特區承擔,而是由中央政府代表的整個非特區共同體承擔。由于沒有硬性改革成本的約束,所以特區建設初期會存在“敢冒、敢闖”等在其它地方看來“膽大”、甚至計劃體制看來“違法”的行為。而這種“敢闖、敢冒”等正是特區“先行試驗”功能所要求特區必須具備的特區精神。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先行先試,開拓創新,是經濟特區超前發展的靈魂。在經濟特區,創新力度要求特別大,這是由經濟特區的地位與作用決定的。因為創新是經濟特區應運而生的歷史前提,經濟特區本身就是一個創新,沒有創新就沒有經濟特區的創立,更談不經濟特區的超前發展。為此,經濟特區改革家和改革家的創新意識、國際關系背景以及市場知識的儲備成為影響特區走向和快速發展的關鍵因素,是特區經濟增長函數最重要的變量。但經濟特區畢竟是在試驗,所以特區改革家必須“膽子要大、步子要穩。鄧小平同志多次囑托改革家“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而且要“不怕犯錯誤”,經濟特區“是一個試驗……是一個新事物,難免要犯錯誤。”“我們的辦法就是不斷總結經驗,有錯誤就趕快改,小錯誤不要變成大錯誤。”
在特區,改革家更是政治家,特區的發展和地位直接與改革家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潛力有關,而改革家的政治前途則與所治理特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密切關聯。但特區的試驗性以及政治敏感性,使得特區改革家面臨諸多的不確定性,尤其是受傳統意識形態的影響,特區的實踐創新往往面臨“變色”、賣國、腐敗等質疑和爭議。這些輿論一方面直接影響改革家的繼續創新,考驗著改革家精神,另一方面影響中央對特區改革家的重新審視和檢討。所以,我國經濟特區無一不面臨“政治性經濟周期”的問題。為此,對特區改革家來說中央決策高層的肯定和公開支持是最重要的。而對于中央來說,對特區實踐的正確判斷和適時推廣是重要的。所以我們看到,1984年鄧小平在視察深圳、珠海經濟特區后。肯定“珠海經濟特區好”,認為“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一方面為特區改革打氣,另一方面肯定了繼續走非均衡漸進對外開放和逐步市場化的路。所以,鄧小平視察特區后不久中央就開放了沿海十四個城市,隨后又將整個海南島設立為經濟特區,再往后,宣布上海浦東的開發開放,以及沿邊開放、沿長江流域開放等。在1992年第二次視察深圳等地后就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中國市場經濟的全面建立作了最后的理論和政治準備,而這些都是基于經濟特區和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
責任編輯張書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