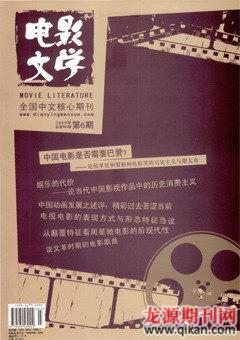電影《梅蘭芳》
楊鵬飛 于 銘
著名導演陳凱歌的大作《梅蘭芳》終于在2008年12月4日公映,可惜,熱熱鬧鬧轟轟烈烈的全球首映禮之后,電影畫面的華麗卻難掩思想和藝術上的蒼涼。這不是一部傳記體的電影,因為現實生活中梅蘭芳的強大后盾并不叫邱如白而是齊如山,這點在導演和演員接受采訪時,都承認是進行了藝術加工的。電影作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對原有的史實材料進行一定的升華和提煉,本無可厚非。藝術本應來自于生活并高于生活。但是關鍵在于為什么要如此加工?為什么把和梅蘭芳共同生活了六年、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糾葛的孟小冬演繹成一個與梅之間不過是有過一段“淺嘗輒止”的露水情緣的過客?又為什么我們從電影來看福芝芳的身份應該是梅蘭芳的原配夫人?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因為電影《梅蘭芳》是代表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道德規范的話語霸權的產物。我們作為受眾從電影《梅蘭芳》中接受的“梅蘭芳”這一文化符號其實是在著名導演陳凱歌和梅派傳人梅葆玖先生這兩位用電影這一形式解讀梅蘭芳的文化權威為我們塑造的符合作為主流文化的儒家道德規范的“梅蘭芳”形象。
我們看到電影在處理福芝芳和孟小冬這兩位梅蘭芳的妻子的時候,是有著刻意的取舍和刪節的。福芝芳在影片中的首次出現是在梅蘭芳與十三燕斗戲之后。喧天的鑼鼓和嗩吶聲里,一對新人歡天喜地地拜天地。影片以此作為少年梅蘭芳一節的結束。然后成年梅蘭芳的一段開始,隨著黎明扮演的成年梅蘭芳柔聲叫道:“芝芳……”陳紅扮演的福芝芳轉過臉來。如此的剪輯手法給觀眾的印象是梅蘭芳第一次結婚的對象就是福芝芳,福是梅的原配夫人,事實上,梅蘭芳的原配夫人叫王明華,本來和梅蘭芳兩人夫妻情深,并為他誕下兩個孩子。王明華為了陪伴梅蘭芳在生下兩個孩子之后就做了絕育手術。不幸的是后來兩個孩子先后夭折,導致梅蘭芳有無后的危險。所以兼祧兩房的梅蘭芳就又娶了后來的福芝芳,因為梅蘭芳自小被過繼給大伯,所以福和王兩人不分大小,都是太太的名分,平起平坐。其實這些封建時代的名分早已灰飛煙滅,筆者在這里本無意去追究這些陳芝麻爛谷子的往事,但就像我剛才說過的,藝術的創作不在于怎樣去改編,而在于為什么如此改編。筆者認為作為電影的特約顧問,梅葆玖先生應該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因為當時已是民國,福芝芳名為夫人,但在婚姻法面前,在活生生的王明華面前卻是不折不扣的妾,我想作為京劇界泰斗的梅葆玖先生是忌諱母親曾有過這樣的身份和地位。因此影片將王明華從梅蘭芳的人生中完全抹去,而且抹得干干凈凈。
如果說對福芝芳的身份和地位的表現還只是利用后期的剪輯和人們的完形心理形成暗示,影片對于另一位梅夫人——孟小冬的塑造更加表明了權力話語的存在。電影中因為鴛夢難成孟小冬與梅蘭芳毅然分手,對梅蘭芳來說,她只不過是一個匆匆過客。那么二人究竟關系如何,不用去道聽途說,只要看看作為當事人的孟小冬當年在和梅蘭芳黯然分手后在《大公報》上連登三天的《重要啟事》就可見分曉:“……經人介紹,與梅蘭芳結婚,冬當時年歲幼稚,事故不熟,一切皆聽介紹人主持。名定兼祧,盡人皆知。乃男方含糊其事,于祧母去世之日,不能實踐前言,致名分頓失保障。雖經友人勸導,本人辯論,蘭芳概置不理,足見毫無情義可言。冬自嘆身世苦惱,復遭打擊,遂毅然與蘭芳脫離家庭關系。是我負人,抑人負我,世間自有公論,不待冬之贅言。”
可見孟小冬認為自己是年輕幼稚,不諳世事,受人蠱惑才嫁了梅蘭芳。以天下第一坤生聞名的“冬皇”是不屑于給梅蘭芳做妾的,她以為自己和當年的福芝芳一樣是平起平坐的夫人。可是梅蘭芳的大伯母去世的時候,由于福芝芳的堅決阻撓,孟小冬不能夠戴孝拜祭,而梅蘭芳的態度卻是“含糊其事……不能實踐前言……”,因此孟小冬的這份聲明雖然說究竟誰負了誰,自有公論,其實字里行間不難看出她對梅蘭芳的失望和怨恨。基本上是在影射梅蘭芳花言巧語騙婚,而后又言而無信。這樣的一段史實,相信無論怎樣涂脂抹粉,只要搬到大銀幕上無疑都會有損梅蘭芳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都會給梅家抹黑。試想一個無法“齊家”的人怎能稱得上“伶界大王”?一個對自己深愛過的女子言而無信的人又怎能配得上“梨園領袖”的頭銜?
可見,在現實生活中作為一代京劇大師、享譽國際的表演藝術家梅蘭芳是人而不是神,而電影《梅蘭芳》在主流文化的話語霸權作用之下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個符合儒家道德規范,恪守“仁義禮智信”的光輝美好的藝術之神、京劇之魂的形象,雖然權力話語在實現其目的的過程中刻意掩蓋了自身的存在,但在對藝術文本的細讀中我們還是不難發現蛛絲馬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