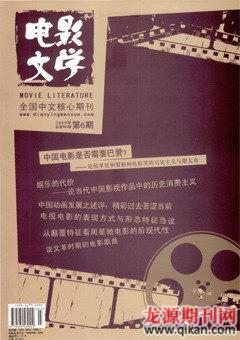論《老人與海》對海明威獨特悲劇觀念的形象再現
王立宏
[摘要]加繆說過,小說歷來都是形象的哲學。《老人與海》用形象化的語言完美再現了海明威獨特的悲劇觀念。小說中海明威一方面通過老人的遭遇重申了人生注定是悲劇的觀念,同時又通過老人“精神的勝利”表達了人決不能在悲劇命運面前低頭的反抗精神,人要在悲劇中顯示出生命的價值和人格的尊嚴,從而使《老人與海》洋溢著一種雄偉壯麗的昂揚奮發的美學意蘊。
[關鍵詞]《老人與海》;海明威;獨特;悲劇觀念
1945年,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Hemingway,1899-1961)因他最后一部力作《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the Sea,1952)“生動地展現出人的命運,謳歌了一種即使一無所獲仍舊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和不畏艱險、不怕失敗的大無畏精神”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海明威這位20世紀最具天才的作家以其獨具匠心的筆觸描繪出現代社會對人精神的深度擠壓和人與環境抗爭而終歸失敗的悲劇,在他短小厚重的(《老人與海》中洋溢著一種雄偉壯麗的悲劇精神和一種昂揚奮發的美學意蘊。
加繆說過,小說歷來都是形象的哲學。《老人與海》用形象化的語言完美再現了海明威獨特的悲劇觀念。在兩希文明熏陶下成長、經歷兩次世界大戰洗禮的海明成在他強悍、充滿陽剛的外在表象下,是他揮之不去、排遣不開的深深的悲傷與絕望。海明威把悲劇看做是人的一種生存方式,一種境界,要成為人,必須沐浴在悲劇的風雨中,這是人的悲劇,是不可避免的。小說一開篇就向讀者展現一幅令人絕望的畫面:“他是獨自在灣流中一條小船上釣魚的老人,至今已去了八十四天,一條魚也沒逮到”,小船的“帆上用面粉袋片打了些補丁,收攏后看來像是一面標志著永遠失敗的旗子”。面臨著嚴重生存困境的老漁夫還必須面對巨大的心靈孤獨,海明威用看似不經意的“獨自”一詞將老人孤獨凄涼的現狀活化出來。老人的妻子早已故去,老人簡陋的窩棚的“墻上一度掛著他妻子的著色照,但他把它取下來了,因為看了覺得自己太孤單了,它如今在屋角隔板上,在他一件干凈襯衫下面”。海明威一向以其“冰山風格”為人們所稱道,在這里就是最好的體現,沒有夸張,沒有渲染,妻子去世之后給老人留下的孤獨和悲傷只這寥寥幾筆,就讓讀者刻骨銘心,而那件干凈的襯衫也絕不是閑筆,須知老人自己是沒有像樣的襯衫可穿的,他用他最好的東西蓋在了他妻子的遺像上,可見老人在其不動聲色的外表下潛藏著對妻子深沉的懷念和依戀,惟其如此,他妻子的亡故對老人的打擊之大,老人內心承受的苦痛之深才會來得更加猛烈,從而形成了巨大的心靈震撼力和深厚的悲劇凝重感。只有小孩曼諾林從五歲起跟老人學習捕魚,與老人一起天天出海,成為老人孤寂生活的惟一安慰和伴侶。但是一連四十天一條魚都沒有釣到,孩子的父母逼迫孩子登上了另一條船,把老人孤零零地留在那條象征失敗的小船里。孩子的離去無疑對老人又是一個重大的打擊。海明威構思出這樣一個孩子作為老人的伙伴和助手,然后又毫不留情地將他從老人身邊帶走,正所謂“欲將取之,必先予之”,這一予一取,老人的處境就越發顯得凄涼了。何況孩子去后,老人獨自一人又是四十四天空手而歸,讓人不由自主地產生一種絕望的感覺。之后,在老人與大魚的生死搏斗中,老人曾九次提到“那孩子在這兒就好了”,更讓讀者感覺到孩子走后給老人留下的巨大孤獨。老人希望孩子在身邊,希望有一個交流的對象,當這個愿望只能成為一種奢望時,他在海上不得不自言自語,時而跟魚說話,時而跟鳥兒說話,時而對自己大聲嚷嚷,這一切都讓我們感受到了老人沉重的孤獨感,也影射了人類的處境,人在這個世界上是孤獨的,是孤立無援的。而事實上,老人身上所承載的悲劇性還遠不止如此,老人在第八十五天再度出海,在好運似乎已經光顧老人時,緊隨而來的卻是更大的厄運。老人在孤獨與絕望中,用生命和意志與之奮戰了兩天兩夜的大馬林魚最終被俘獲時,海明威一再提及老人覺得這“簡直等于是一場夢”,“光景太好了,不可能持久的”。暗示老人的好運是夢一般的不真實,是不可能持久的,老人的悲劇命運才是切實的,是不可改變的。果然,在第三天,饑餓的鯊魚就將老人的戰利品吞噬殆盡,只剩下一幅龐大無比的魚骨架。留給老人的只有對那條與老人同樣悲壯、同樣背運的大馬林魚的無盡的歉疚,老人的一切努力終歸化為烏有,人生注定是悲劇性的。
在悲劇意識不斷濃重的20世紀,對人的認識在現代文學中陷入了根本的危機,在現代作家的眼中,悲劇再次成為人無法逃避的現實。悲劇審美也成為現代作家的普遍的共識,但同時又具有各自獨特的個性。海明威悲劇意識,是在對悲劇的深邃體驗基礎上的強烈反抗精神。雖然悲劇是注定的,但人不能在悲劇的命運面前低頭。這與中國儒家的思想精髓“知其不可而為之”有著殊途同歸的文化內涵。海明威主張勇敢地面對生活,越是環境惡劣,越是困難,越要頑強拼搏,寧可失敗也不可失去尊嚴,海明威筆下的人物都是生活在惡劣環境下的男子漢,具有“精神不敗”的風度,這里滲透著海明威的生命體驗,是海明威悲觀與陽剛氣概的矛盾統一,這正是海明威作品的獨有特征,所以《老人與海》一方面極力渲染桑迪亞哥悲劇性的特征,一方面又淋漓盡致地描繪他的硬漢行為,小說企圖表現人在注定失敗面前如何保持優雅的風度,即海明威所謂的“重壓下的優雅風度”。
老人的人生態度是自信而又達觀的,表現出在困境面前的“優雅風度”。海明威在老人出場時這樣描寫老人:“他身上的一切顯得古老,除了那雙眼睛,它們像海水一般藍,是愉快而不肯認輸的。” “不肯認輸”就是老人的精神不敗的精髓所在。雖然八十四天沒有捕到魚,但“他的希望和信心從沒消失過”。在第八十五天,他仍然如往常一樣叫醒孩子,信心十足地出海去。老人曾對孩子說“我也許不像我自以為的那樣強壯了,可是我懂得不少竅門,而且有決心。”雖然不得不面對自己的蒼老,但老人的自信還在。“我是個不尋常的老頭兒”坦然自在地從老人口中吐出,自信而豁達的老漁夫也就隨之躍然紙上。老人面對自己的對手大馬林魚的態度更是有著“優雅的風度”,在和大魚你死我的活較量中,老人始終對它贊不絕口,甚至稱它為兄弟、朋友,對自己必須殺死它而深感痛心,并表現出對它真誠的認同,“憑它的舉止風度和它的高度的尊嚴來看,誰也不配吃它”。這是真正的男子漢的胸懷。老人身上還展現了海明威的悲劇意識中最重要,最昂揚的部分——決不會向悲劇命運低頭和永不服輸的斗士精神。老人在捕獲大魚時所表現出來的智慧、意志力與承受力,他同鯊魚搏斗到手無寸鐵的風度,無不在向讀者詮釋著什么才是真正的“硬漢”。一向以精煉著稱的海明威在這里不惜筆墨地渲染大魚的龐大與罕見的力量,鯊魚的極端兇悍與殘暴,就是為了凸顯老人在這場殊死搏斗中所綻放的奪目光彩。老人在這搏斗中已經將輸贏置之度外,物質的目的越來越淡化,更多的是為了一個漁夫的尊嚴,一個人的尊嚴而戰斗。“你殺死它(大馬林魚)是為了自尊心,因為你是個漁夫。”“我對那孩子說過來著,我是個不同尋常的老頭兒,現在是證實這話的時候了。”老人用他強大的意志力與自己的強大對手(大馬林魚,鯊魚,鯊魚群)、不斷下降的體力(左手抽筋,頭暈)以及惡劣的條件(工具簡陋,沒有食物,極其少量的水)對抗著,這種對抗讓老人時時感到力不從心,他“身子僵硬、疼痛,在夜晚的寒氣里,他的傷口和所有用力過度的地方都在疼痛”。老人甚至有過放棄的念頭,“我希望不必再斗了,真希望不必再斗了”。但是當兇惡的鯊魚群到來時,堅強的意志和強大的自尊,讓“他又搏斗了”,雖然“這一回他明白搏斗也是徒勞”。老人是一位精神不敗的英雄,是海明威筆下硬漢形象的高度概括和升華,是海明威筆下的一座與悲劇命運抗爭到底的精神豐碑。
至此,海明威獨特的悲劇觀念完成了它最形象的表達:“人無論怎樣都只能是一場悲劇,然而只要有這種精神和風度,人就能在明知會失敗仍要拼搏的悲劇中顯示出生命的價值和人格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