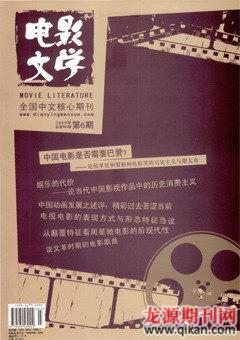董其昌對清代畫壇的影響
張 寵
[摘要]董其昌是明中后期繪畫藝術界的一代宗師,對中國封建社會后期文人畫藝術的發展影響極為巨大和深遠。他使文人畫藝術獲得極大的發展,在明末清初形成熾烈的文入畫風。有清三百余年,凡畫學畫論未有不涉及“南北宗論”的。本文從繪畫理論和繪畫實踐兩大方面對董氏對清代畫壇的影響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和探討,突出了董氏影響之下清代畫壇文入畫藝術的多元化特點。
[關鍵詞]董其昌;文入畫;繪畫理論;繪畫實踐,影響
董其昌是明中后期繪畫藝術界的一代宗師,是明代繪畫藝術的振興者,“松江畫派”的領袖。但董其昌之所以能夠在整個中國畫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更在于他是唐宋以來文人畫藝術的集大成者。他使文人畫藝術獲得極大的發展,在明末清初形成熾烈的文人畫風,這在中國繪畫史上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董其昌在文人畫的實踐和理論兩方面都有著卓越不凡的建樹,本文將就這兩個方面探討和分析其對文人畫藝術的深遠影響。
一、董其昌對繪畫理論的影響
董其昌在晚明享有極高的政治地位和書畫創作及鑒賞上的名望,他的“南北宗論”一出,又經同時代的陳繼儒、莫是龍、沈顥等人的大力宣揚,對明末及有清一朝中國繪畫審美方向的發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并受到近現代繪畫理論界的廣泛關注。
“南北分宗”理論使董其昌享譽當朝、名揚后世,但其影響下的結果卻是十分復雜的。圍繞著這一理論,人們或贊同,或否定,或調和,毀譽參半,爭論不已,成為中國繪畫史和繪畫理論史上的一樁“公案”。
清代繪畫理論界對“南北宗論”持贊同觀點的人很多,他們的見解可以王原祁、唐岱、華琳、沈宗騫、布顏圖等人的言論為代表。一方面,他們在繼承董其昌“南北分宗”理論基本精神的同時,又從各個角度對其進行修補和完善,分別從禪學、藝術風格、藝術形式、藝術技法和地理環境等方面對“南北宗論”作了進一步的分析和論證,從而使“南北宗論”更具系統性和嚴密性。在此基礎上,近現代藝術理論家又從哲學觀念、社會政治條件、時代文化思潮等角度探尋“南北宗論”的內在依據,鄧以蟄、王鈞初、俞劍華、美國學者何惠鑒、高居翰以及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等可為代表,他們的研究為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把握“南北宗論”的美學內涵和歷史意義奠定了理論基礎。
自從董其昌“南北分宗”理論提出之后,對其持批評和否定意見的也不乏其人。如清人李修易批評“南北分宗”理論束縛了藝術家的創造精神,汪士慎認為南北分宗不符合中國繪畫史的本來面目,近現代學者童書業、滕固、啟功等人也從不同的角度對“南北宗論”提出批評,指出其中的疑點和謬誤,還有人認為“南北宗論”完全是董其昌等人根據個人好惡的主觀臆造,中國山水畫史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南北宗,從而對“南北宗論”進行了徹底否定。這種否定和批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未能從“南北宗論”的思想整體上去把握其美學內涵。“南北宗論”固然有著缺陷和不足,但它在明末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提出乃至形成體系,以南宗藝術風格對北宗藝術風格加以排斥和否定,這實質上體現了中國文人畫藝術發展到明末這一特定歷史時期出現的一種新的藝術意向、審美趣味和審美理想。也正因為如此,“南北宗論”才以其強大的生命力主導了有清一代的繪畫理論,其余波至今尚存。
我們知道,董其昌的“南北宗論”含有崇南抑北的傾向,但這種傾向并不過分,董其昌對北宗的核心人物如李思訓、趙伯駒、劉松年、馬遠、夏圭等人的創作,都有過中肯的褒辭。但在董其昌的后學那里,“南北宗論”被發展為所謂的正派與別子,特別是清初的“四王”,動輒以南宗嫡傳自居,將“南北宗論”視為金科玉律,甚至真實的畫史加以宣揚,不遺余力地推崇南宗,北宗遭到極端的排斥。唐岱則大談“正派正傳”之論,將南宗諸家直到自己歸入正派,而妄言北宗“雖得一體,究于古人背馳,非山水中正派”。既有正派與非正派之分,學畫者走何派路徑自然就十分重要,為提倡所謂畫學正道,布顏圖撰寫了《畫家心法問答》一書,以師長的口吻諄諄告誡初學者當認準門戶,以南宗為正宗,不可錯走路頭,迷失正道。
有清三百余年,凡畫學畫論未有不涉及“南北宗論”的,其中少數人從不同角度對“南北宗論”提出了質疑和否定,但這種聲音在鼓吹“南北宗論”的大潮中實在是太微弱了。數不盡的畫者竭力加入到南宗的陣營中,從自身的利益出發闡釋發揮“南北宗論”,以“南北宗論”來抬高自己,喧囂聲譽。這些與“南北宗論”有關的形形色色的言論中,除極少數對“南北分宗”的理論體系加以完善外,絕大多數缺乏真知灼見,不能掙脫董氏的束縛,人云亦云,陳陳相因。更不幸的是,他們牽強附會董其昌的“南北分宗”理論,將其中疏漏、失實、帶有個人感情色彩的一面無限夸大,最終完全偏離了“南北分宗”理論的美學本質,淹沒了其中有價值的東西,這是董其昌始料未及的。現當代的繪畫史家和理論家們站在歷史的高度,對董其昌及其“南北宗論”進行了客觀、系統、深入的研究,基本把握了其美學實質,澄清了歷史上的妄言謬說,指出了“南北宗論”在中國繪畫史上的真正價值和意義。
陳傳席說:“董其昌和陳繼儒是明末極負盛名的大畫家兼大理論家,尤其是以董其昌為代表所提出的山水畫‘南北宗論,向下:影響到繪畫主流的發展;向上:影響到對畫史的把握;當時:反映了一般士人的審美意識;爾后:左右了一般士人的審美心理。影響太大了,直到今日,都無法擺脫它的影響。”這可算是對“南北宗論”深遠影響的客觀、公正、精辟的評價。
二、董其昌對繪畫實踐的影響
在繪畫理論上,董其昌以“南北宗論”彪炳百代,在繪畫實踐上,董其昌以他天才的藝術稟賦,不懈的藝術追求重振了明末畫壇,開創了文人畫藝術的嶄新風貌。與在繪畫理論上的影響比較起來,董其昌在繪畫實踐領域造成的影響也毫不遜色。
董其昌的繪畫藝術首先影響到明末畫壇,他政治地位高,交游廣泛,許多著名畫家都直接或間接出自他的門下,受到他的藝術風格和審美意趣的影響。在畫史上較為著名的有趙左、吳振、沈士充、程正揆、楊文驄、項圣謨、冒辟疆、吳偉業等,他們或在技法上師法董其昌,或在風格上追隨董其昌,成為聲勢浩大的“松江畫派”的主要力量。
有清一代繪畫藝術的發展籠罩在董其昌的影響之下,藝術追求和審美趣味不盡相同的畫家們從不同角度師法董其昌,他強調師法古人的主張,被“四王”等山水畫家所繼承,而他講求筆墨技法,主張“以畫為寄”的看法,則被龔賢、八大等人發揚光大。清書畫評論家方薰說:“書畫自畫禪開堂說法以來,海內翕然從之,沈、唐、文、祝之流遂塞,至今無有過而問津者。”充分肯定了董其昌對清代畫壇的影響。
“四王”是董其昌藝術衣缽的忠實傳人。王時敏自幼受到董其昌的傳授、指點和提攜,其孫王原祁也以“華亭血脈”為榮,王鑒和董其昌同為“畫中九友”,王暈則
出于王時敏門下。清前期的皇帝自順治到乾隆,都接受“南北宗論”,酷愛董其昌的畫跡和藝術風格,把董其昌的藝術作為政治統治的文化代言人,皇帝的積極參與和提倡促成了以“四王”為首的南宗正統派在清初畫壇的優勢地位。董其昌對筆墨程式化語言的追求在“四王”手中發展得更加規范化,他們將董其昌藝術中匯集的古人筆墨形式和技法片面抽取和強調出來,使山水畫藝術成為一種千篇一律的規范化、程式化的存在,這違背了藝術發展的基本規律,違背了藝術創造的基本原則,限制了藝術的活力,導致了清代畫壇的衰落。繼“四王”之后,還有“小四王”、“后四王”承續“四王”余波,他們將“四王”那種規范化和程式化的筆墨形式變得更加僵死和刻板,完全喪失了董其昌山水畫藝術中蘊含的天地造化之靈氣,文人山水畫藝術走上絕境。當然,這些不良后果不應直接歸咎到董其昌身上,但無可否認的是,這是董其昌繪畫藝術和藝術思想中包含的保守因素被后學片面繼承和夸大的結果,這顯示了董其昌在后世文人畫藝術實踐方面的消極影響。正如李修易在評價“四王”及其門徒時所指出的:“蓋耳目為董尚書、王奉常所囿,故筆墨束縛,不能出其藩籬。”這種看法代表了當時有識之士在此問題上的普遍認識。
事物之間因果聯系是多樣而復雜的,同樣是從董其昌出發,八大等人卻發展出了與“四王”完全不同的藝術風格。在八大山人早期的藝術探索中,有大量臨仿董其昌的作品,但他并沒有繼承董其昌的筆墨程式化因素,而是吸取了董其昌在文人畫用筆用墨方面的優勢和“不為物所役”的創作思想,并將之與自己國破家亡后憤世嫉俗、孤高冷傲的性情融會成一體,一掃董氏的溫靜閑雅、秀逸幽淡,開創出只屬于自己的筆勢闊大、簡練雄奇、意趣冷傲的藝術風格,以自己的藝術實踐豐富和發展了文人畫內涵,這代表了董其昌對后世繪畫藝術實踐的積極影響。另外如龔賢等人,也曾受到董其昌藝術思想和藝術實踐的影響,同八大山人一樣,他們沒有滿足于停留在董其昌的層面上止步不前,而是努力沖破了董其昌的藩籬,以各自藝術上的獨創性為文人畫藝術開辟了嶄新的境界。八大山人不是董其昌的正脈嫡傳,但他們才是真正領悟了董其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精髓的清代畫家,他們敢于在揚棄中繼承,富于創新精神,為正統畫派走向衰落的清代畫壇,注入了勃勃生機,開辟了文人畫藝術的新天地,也許,這才是對董其昌及其文人畫藝術最好的繼承和發展。
歷史造就了董其昌,董其昌也以輝煌的成就回報了歷史。董其昌被譽為“藝林百世大宗師”,這是極高的評價,在明清名家輩出的畫壇上,董氏確是影響最為深遠的文人畫藝術大師,17世紀因之成為“董其昌世紀”,余緒至今尚存,其影響力之大是難以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