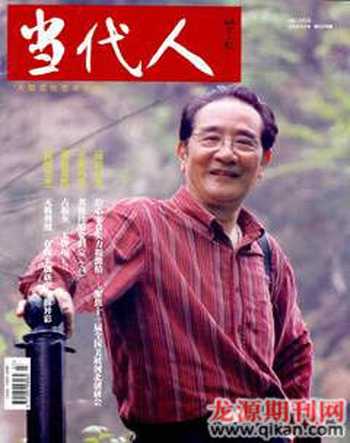耍社火
張新茹
我的老家在太行山下,每逢正月總要耍社火,也總有社火隊來村里表演。耍社火是對前來表演的各種民間藝術形式的統(tǒng)稱,比如:武術、高蹺、旱船、龍舞、獅子舞等.....每當有社火隊到來,等候在村口的接迎者就放三聲禮炮,一是為歡迎表演隊伍的到來;二是通知村里人做好接應的準備。表演隊伍一般是應邀或是互訪,也有主動前來表演。
社火隊的隊伍大小不等,多則百人,少則幾人,每個表演隊都有會旗、有會頭(負責人)。表演者一般畫彩妝、穿彩服,較富裕較大些的村莊,表演人員的著裝就更講究一些,差一點的也會穿燈籠褲或便于動作的服裝。表演時有統(tǒng)一著裝的集體表演,也有分飾不同角色的人物裝扮。上場順序一般由會頭事先安排,有時,性急的表演者會爭先恐后,不等會頭同意,就躥到場地上搶先表演。
耍社火分拉街表演和打場表演兩種形式。拉街表演是在街道上邊走邊表演,無論街道寬窄都不影響表演者的情緒,遇到稍寬處表演者會原地表演,觀眾站在街道兩側觀看,也有觀眾追隨著表演者沿街觀看;打場表演是在固定的場地上表演,觀眾站在周圍觀看。
每每聽到遠處的禮炮聲響,姐姐們就拉著我飛似的來到表演場地,因個子和步子都不及姐姐們大,奔跑時總遭到姐姐們的訓斥。有時姐姐根本拉不到我的手,而是拽著襖袖,我的整個胳膊都被拽出來,但是每次奔跑時我都使勁閉著嘴,從不犟嘴,生怕跳得比步伐還快的心臟從嗓子里滑出來,我知道姐姐們?yōu)榈氖勤s在耍社火的到來之前,占領觀看表演的最佳位置,有時我也和小朋友們做伴兒,早早來到表演場地。社火隊到來之前,樹上、房上都已站滿了等候的人們。
一般的表演的場地上都放著一面碩大的鼓,每個社火隊表演之前都要敲鼓打通,打通時鑼鼓镲鈸一起擊打,交相呼應,震耳欲聾。擊鼓的人都是村里的壯漢,他們輪流上陣,個個敲得滿頭大汗,有的拿著自備鼓錘,把正在敲鼓的人推開,合著節(jié)拍奮勇“參戰(zhàn)”,寒冬臘月天也赤裸著上身擊鼓,情緒激昂時鼓手們雙腳跳起來,腮幫子和上身的肌肉會隨著鼓槌的上下而起伏抖動,肌膚冒著熱氣,連頭發(fā)梢都流露著醉意。隆隆的鑼鼓聲,震動著天,震動著地,也震動著山村里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心。最最讓我興奮的是晚上的社火表演,只要站在觀眾最前排就可以領到一把長長的麻稈,到現(xiàn)在我也不明白為什么耍社火時非得要點燃麻稈,而不是玉米稈、高粱稈或是其它的農(nóng)作物秸稈。我曾反復考慮可能是因為點燃麻稈能照明且燃燒慢的緣故。每次從領到麻稈開始,因占位奔跑累得通紅的臉,因緊張、和羞澀漲得更紅,隨著吱吱的火苗仿佛覺得自己的肢體被烤得晶瑩透亮,紅紅的心臟隨著鑼鼓聲咚咚地上下舞動。
“耍社火”表演開始前,有人揮舞著呼呼作響的“三節(jié)棍”驅趕觀看的人群向后退,好騰出更大的表演空間。三節(jié)棍所到之處,人群中發(fā)出噢噢的叫聲,人們最大限度向后仰著上身,以防被三節(jié)棍擊中,而三節(jié)棍總會有驚無險地從圍觀者的頭頂上方掠過,乘此空檔武術表演者就跳到場地上開始表演。表演形式分雙刀、單刀、長拳、長槍……高蹺表演者更是緊隨其后,有單腿跳、下叉,甚至翻跟頭;旱船表演者如在水上漂來漂去;秧歌表演者有男有女,莊重幽默,扇花飛舞;舞獅者出其不意的高超技藝,令人叫絕。這些表演者既有固定的套路,也有即興的發(fā)揮,他們的激情和觀眾的情緒融匯在一起,互相感染,耍社火的越帶勁,越投入,觀眾們就越開心,越興奮。整個村莊被歡樂、熱烈、幸福、祥和的氣氛包圍著。
我的老家是一個大村莊,耍社火時村里還有一個習俗,就是十里八里的鄰村人都會偕老帶幼前來看熱鬧。來的人無論是不是親戚朋友,只要來到家里,主人都會主動沏茶倒水,熱情地端上飯菜,客人們也大大方方甩開腮幫子,不分彼此,大吃二喝。每逢耍社火的日子,村里每家的門都是敞開的。鄉(xiāng)親們總是剛看完今年耍社火又在盼望明年。
一晃幾十年過去,兒時看耍社火的情景至今不能忘懷,每每想起家鄉(xiāng),自然就想起過年的“耍社火”。兒時耍社火的“印記”隨著年齡的增長無數(shù)次在腦海中重現(xiàn),幸福感也隨著歲月的流逝而無限放大和延伸。(責編:孫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