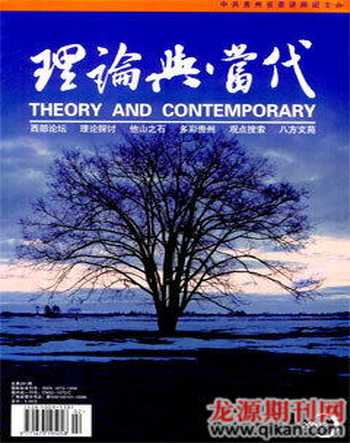新語境下的“偽”寫作與“真”寫作
袁仁琮
轉型期構成了文學創作新的語境,真寫作,偽寫作以及另類寫作同時存在,出現光怪陸離圖景,作一些鑒別,再行消費,或者借鑒吸收,很有必要,
被壓抑、被扼殺幾十年的文學,一旦去掉了壓抑,大有饑不擇食之勢,從本土撿回來現實主義,從國外撈進來形形色色的現代主義以及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于是,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意識流、黑色幽默、魔幻現實主義、中國傳統現實主義以及由現實主義嬗變而來的新寫實主義;受到西方現代主義影響而產生的朦朧詩,展現異彩紛呈圖景。這是觀念大解放,轉型期文學大實驗的結果。一大批新人出現了,一大批老作家跟不上形勢了,另一批人在探索、選擇、小心而穩步地前進。從1980到現在,經歷20多年的比較、選擇,一些作品離文學本質越來越遠,把文學變成實現某種目的的手段。成了偽文學。
有這樣一類作品,它們完全沒有生活依據,純粹出于狹隘感情自我發泄。它們的作者莫名其妙地調侃人生,調侃社會,調侃一切人。漠視最起碼的人的感情。紅極一時的一個作者在他的代表作里充滿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描寫。大學生不上課,打群架,出走;攔住不認識的女生調戲,背10只母雞在身上就是行為藝術家;用“卸腿”黑話嚇唬店老板,修車店強迫人修車,漂亮女生男朋友很多,流產勤,得了盆腔炎;小車被撞,掉進溝里,迎來的不是同情,不是援救,而是“潮水般的掌聲”。整個城市充滿了打架犯、白癡、無賴、二奶、黑店、無聊者……發生火災,作者不是焦急,更不是打119,而是欣賞,說:“這就是火災比水災好的地方。火災能從床上爬起來什么衣服都不用添置就在邊上觀賞,尤其是在冬天,路過火災現場。暖意盎然,真是市民休閑驅寒的理想場所。”救火車來了,作者不是寫群眾的急盼,也不是寫消防官兵的奮不顧身,而是以調侃的筆調寫消防官兵和群眾。群眾自發地統一地散開,大家都直勾勾地看著消防車,想看看究竟是怎么滅火的,眼神中充滿了虔誠,就差涌出一個群眾代表,上前熱淚盈眶地說:“老百姓都盼著你們呢。”
在作者的眼里,消防官兵不是英勇善戰的戰士,不是把人民的生命財產放在第一位的人,而是一群白癡。火也很怪,不滅就自然小了下去。火小了,本來是件好事,作者卻說:“我們的消防官兵必須爭分奪秒,晚一步,火就自己滅了——仿佛都能聽到大家的心跳。”“只剩一堆火苗了,而且火苗有漸微之勢。”作者不是慶幸,而是萬分惋惜,“生怕火苗給吹滅了。因為沒有了天然大火爐,我和王超在樓上看得冷。”
叫人不能忍受的是把群眾也寫成了白癡。出現在火災現場的群眾不但沒有救災的行為;連救災意向也沒有。只剩下一堆火苗了,一個老太婆才端一盆水出來,大喊大叫:“救火啊。救火啊。”消防隊員沒能搶在老太婆的前面,老太婆最后倒了一盆水,火噗的一聲熄了。作者對火的熄滅萬分惋惜,說:“離得最近的人正要阻止,但是已經來不及了,老太婆已經將水潑了出去,真是覆水難收啊,大家都痛苦地閉上眼睛。周圍的一切都好像靜止了。”看了這些描寫,不能不產生疑問:為什么這個城市的人連人的共同感情也沒有了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想去想來,答案只能是:不是作者惡搞,就是胡編亂造。無論屬于哪一種,都己遠離了基本真實,也沒有什么藝術性可言。
和這一類作品類似的是搜集“原始”。搜集“落后”,展覽“本能欲望”的作品。80年以后一批人打出反傳統旗號,借寫人性解放,大寫特寫性欲。性亂。有的著名大型文學刊物刊出的作品,名出版社出版的作品,通書都寫性生活,似乎作品里的那些人,除了亂愛,做愛,就再也無事可做了。另一些作品夸大落后,夸大野蠻,展覽地描寫獸性,淡化人性,鄙棄崇高。這類作品,在80年代,反對傳統文學中不良因素的作用是明顯的。文學自從接受文學是革命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的觀點,納入政治工具軌道,文學創作無視客觀存在著的現實,無視多數人的生存狀態,多數人的感受,多數人的愿望和要求,反話正說,反事正寫,拔高人物形象,粉飾現實,作品中充斥著假大空。這種寫作。年紀大些的作者都是經歷了的。我自己也寫過不少這類作品。那時,作家們生怕說錯話。寫錯文章,惶惶不可終日。一個國家,有它的主體意識形態,有長期形成的集體無意識。作家不要離開這樣的大環境,作犯眾怒的事。但不能禁忌太多。禁忌太多了,扼殺人的主體性,創造性;禁錮人的思想。如果多數人都成了唯唯諾諾的奴隸,這個民族,這個國家是難以興旺發達的。所以,“真”寫作既要反對把現實描得一團糟,糟得連作者自己都不是人了,也不能描得花呀朵似的。沒有陰暗,沒有污濁,沒有男盜女娼,沒有貪官污吏,沒有殺人越貨,沒有絕望和自殺……對這些活生生的現實,如果作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同樣為多數人所不齒。“真”寫作不要離開這個民族,這個國家多數人的愿望,不要違背多數人的感情。只有這樣,才可能在讀者中產生共鳴,建立起碼的信任。對那種“偽”文學的反叛是必要的。但反叛的目的是為了前進,為了發展,而不是相反。如果把文學拉回到記錄野蠻、記錄肉欲的原始地步,就違背了初衷。
有一種作品專門尋求新和怪。文學創作不應因循守舊,不能老用傳統手法敘事,老從情節人手,老是白描,寫外部行為,不探究人的隱秘世界,不會寫人的意識,人的感覺、直覺,自我意識,價值判斷,讀了給人以老面孔的感覺。這樣,哪怕題材新穎,老面孔的表現手法同樣會使讀者生厭。但是,探究新的表現技巧,不等于求怪,讓讀者讀不懂。如果大多數人都讀不懂,作品也就失去存在和傳播意義。朦朧詩漸漸衰微,很值得深思。這種類型的作品,雖不應歸為另有目的的“偽”寫作,卻也不便歸為真寫作。只能歸為另類寫作。
文學寫作的真偽,并非以“新”“舊”為判別標準,并不是新的就是真的,舊的就是偽的。幾千年來的文化史,基本上是由“復古”和“否定傳統”兩種循環構成了發展鏈條。歷史進入春秋戰國時代,孔子提出恢復周禮,倒回去過更為低下、簡樸的生活,是倒退,不可取;唐代、清代都有過聲勢浩大的文學復古運動。這兩次運動,都是當時有識之士不滿意風靡一時的偽文學,或者叫做玩文學發起的。文革以后,又發起一次新語境下的復古一恢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唐代一次復古,出現一大批優秀散文;清代復古,也是如此。80后這一次“復古”,本質是“反正”,是回歸文學本質。否定傳統,時時都在發生。進入20世紀以后,西方文學傳統被否定殆盡。不僅西方如此,中國也是這樣。但不能老跟在別人的屁股后面,必須尋求自己的路。
電影、電視受眾是真誠的,好的影視作品不少,冒充藝術品塞給觀眾的同樣不少。這些編劇,導演不顧受眾的感受,捏造歷史,褻瀆人民英雄,離真藝術已經很遠。圖書讀者也是真誠的,他們花錢,花時間讀作品,總希望得到某些滿足,某些益處,作者塞給他們偽藝術,于心何忍!
文學藝術生產,高層次的目的在于傳播美的信息,美的感情,真誠地為這個世界變得美好一些而寫作。這是為人類心靈付出的高尚勞動,一旦提筆寫作,就是在為人類心靈工作。只有真誠的作家,才可能贏得真誠的讀者。那種偽寫作,不管眼前怎樣的轟轟烈烈,總有一天會被真誠的讀者所拋棄。法國古典主義批評家布瓦洛有一段關于文學作品價值的話是很有意思的,他說:“實際上只有后代的贊許才可以確定作品的真正價值。不管一個作家在生前怎樣轟動一時,受過多少贊揚,我們不能因此就可以很準確地判定他的作品是優秀的。一些假光彩,風格的新奇,一種時髦的耍花槍式的表演方式,都可以使一些作品行時;等到下一個世紀,人們也許要睜開眼睛,鄙視曾經博得贊賞的東西。”(伍蠡甫等編《西方文論選》上冊,第334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出版)
文學創作和文學消費能給人以極高的精神享受,這種境界,任何別的享受都無法達到。這種精神的滿足,能使文學藝術創作內動力長盛不衰。
責任編輯郭漸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