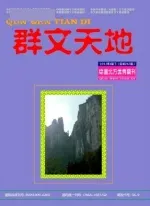對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的幾點思考
秦 懋
田野調查,英文為“fieldwork”,又譯為田野工作、田野作業、田野考察、野外考察、實地考察等。在這里,我們主要探討人類學范疇的田野調查工作。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田野調查”經由人類學家A.C.哈登的強調、博厄斯的倡導、里弗斯的踐行,在馬林諾夫斯基那里上升到人類學方法論的高度。
一、田野調查的特點
田野調查是經過專門訓練的人類學者親自進入某一社區,通過直接觀察、訪談、住居體驗等參與方式獲取第一手研究資料的過程,是人類學家獲取研究資料的基本途徑,也是人類學理論建立的基礎。初次田野調查經歷,通常被視為人類學者的成年禮,是跨越“文野之別”的根本途徑。
田野調查的最大優勢在于它的直觀性和可靠性。調查者親臨調查對象的現場,直接觀察處于自然狀態下的社會現象,可直接感知客觀對象,獲得直接的、具體的、生動的感性認識,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調查者也可在共同活動中與被研究對象中的相關人物建立感情、發展友誼,在此基礎上深入、細致地了解被研究對象表層以下的有關情況及具體表現,這些是其他間接調查方法所不能做到的。
二、系統的人類學訓練是田野調查的關鍵
人類學田野調查是一個與理論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嚴謹的研究體系,有一套嚴格的方法論和具體的操作程序。它不是簡單的資料搜集,也不單純是調查技巧。扎實的人類學理論與方法是調查能否獲得豐富資料,在調查中對民族文化現象做出全面客觀的觀察、描述和分析,撰寫出高質量的調查報告或民族志成果,在理論與方法上做出反思的關鍵所在。若人類學理論儲備不充分,田野調查不規范,調查者下到田野點之后懵懂無知,只是按照提綱搜集材料,那么調查中的觀察視角,關注重點,對現象的記錄和分析都會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不能進行深入細致的描述,更不能在主位與客位的視野下對現象做出闡釋。調查回來之后,發現彎路走了不少,材料是分散的,勉強湊成類似民族志的報告,卻說明不了什么問題,對人類學也遲遲沒什么感覺,甚至會有倦怠的情緒。因此,只有經過規范嚴謹的學術訓練,系統地學習人類學的基礎理論和田野調查方法,才能獲取深入、豐富、細致的民族志資料,提高對材料的把握和駕馭能力,為理論的升華提供基礎。
三、學術感悟力是田野調查的重要因素
一名善于進行田野調查的人類學者應具備旺盛的好奇心,善于捕捉材料、追蹤關聯、整體把握和比較研究。
在實地調查中細致地感受生活,體驗和觀察自己和他人的參與,善于表述和理解當地人的行為所蘊涵的多重文化含義。
對田野資料的敏感度在田野調查中是一個重要內容。調查者不可能預測到所有會發生的情況,對自己所要調查的專題,也許只有一個模糊的意向,甚至會刻意摒棄任何的理論預設。因此在調查中一些寶貴的線索很可能會輕易地被忽略掉,而這些線索,則會被富有學術感悟力的調查者捕捉到,通過觀察和詢問,記錄下大量的細節,這些都是任何訪談提綱無法容納或事先準備的。這種敏銳的觀察,得自于長期田野的浸濡,對當地文化充分尊重的態度和當地文化具體場景的體認。
四、遵循學科基本原則是田野調查過程的核心要素
人類學家的田野調查沒有一個單一的模式可循,調查者針對不同的研究計劃、研究環境會選取不同的調查研究方法,但田野調查都需要遵循學科原則和一些共同的規律。
田野調查的目的主要是認知被調查文化,同時以自身的文化系統作為參照系,在這種參比框架下,不斷深化對異文化的認知和積累資料的過程。在田野調查中,調查者和調查對象總有一定的距離,一是族際差異的距離;二是角色差距的距離,所以收集材料的背景不可能純而又純。顧頡剛在《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一文中說到:研究者在調查中怎樣保持價值中立態度?人類學研究只能在社會之中研究社會現象。為了達到客觀、正確,研究者既要貼近研究對象,又不能和對象合而為一,最好保持若即若離的關系,便于進行整體性的反思。同時,調查者要用文化相對主義的理念,認識到各種文化沒有優劣、高低之分,一切評價標準應放在它所屬的價值體系中進行。田野調查不是簡單地把調查者當成是當地人,而需要調查者和當地人相結合,理解當地文化,從當地人中通過自己的體會來描述當地人的心理和觀念,以“他者”的視角體會當地人的文化和心理。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意識、地區的復雜性、獨特性,不干預、更不要牽涉到當地人的生活中去,努力減少人為的干擾因素。
田野調查作為人類學的基本方法,隨著人類學理論而發展,并影響著人類學理論,也給其他學科以有益的啟示。但無論其形式怎么變,其使命仍在于復原被調查文化的系統結構,其實質在于立足于一種(或多種)文化作為參比系,去反復參比被調查文化,從而達到對被調查文化的認知,最終促使人類的理解與溝通。
參考文獻:
[1]莊孔韶主編.人類學通論[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
[2]汪寧生著.人類學調查——正確認識社會的方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3]宋蜀華,白振聲主編.民族學理論與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
[4]劉海濤.論人類學田野調查中的諸對矛盾與“主客位”研究[J].貴州民族研究,2008(3).
[5]李月英.田野調查:文化人類學的主要研究方法[J].今日民族,2007(9).
[6]余園.田野調查對人類學研究的價值與意義[J].大連民族學院學報,2005,7, 7(4).
[7]鄭欣.田野調查與現場進入——當代中國研究實證方法探討[J].南京大學學報,2003(3).
[8]許傳靜.文化人類學田野調查的發展及實質[J].西藏民族學院學報,2006,9,27(5).
[9]陳興貴.中國民族學田野調查的歷史回顧與反思[J].貴州民族研究,2007(6).
[10]楊清媚.讀書與田野調查——談如何提高對人類學的學術感悟力[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6(6).
(作者簡介:秦懋(1981—)女,藏族,四川小金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碩士,研究方向:民族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