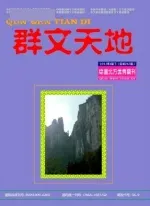“另類”構思的美感
楊 林
“散文的構思,主要是指散文在通過什么線索和結構來組織材料,從什么角度來展開內容的敘寫等環節上,所作的獨到的選擇和安排。”它不僅關系著散文文本類型藝術的成敗,還影響甚至左右文學創作的各個方面,并在不同程度上制約作家的雅趣塑造和思想追求。
散文作為一種文體的特殊性,在于它取材廣泛,表現形式不拘一格,千姿百態。如何將紛繁多樣的材料嵌于自由靈活的形式中,再打磨出一個完整的藝術體,散文的藝術構成就尤為重要了。它充分展現了作家的才識、慧心和獨創性,當然,也關系到文本獨特藝術效果和美感特質的形成。
記得《余光中散文》里寫過這樣一句話:散文要因景生情,隨事起感,自由靈活,活潑天然,得有點詩人的本領;要敘事生動,寫人出神,得有點小說家的才能。由此可見,散文家得有‘雜家的技能,本文擬就《秦牧散文》、《文化苦旅》在敘寫等環節中的個性差異,對各自的“敘述模式”進行一番探討分析,以便更深刻地了解秦牧、余秋雨散文的內涵和風格,并借此思索小說文本解讀的一種方法——“敘事學”,對散文構思的影響。
一、“一事一物”表現不同的敘述主體
“文本的敘述主體是相對敘述客體而言的,敘述客體不完全等同于文本的內容,作品的題材、主題和感情思想等所歸屬的生活背景和客觀世界表現在散文創作便是敘述主體對敘事材料的征服和占有,這種占有決定了敘述主體在敘事活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以此為切入點,我們會發覺《秦牧散文》、《文化苦旅》在敘述主體的表現上有很大差異。
《秦牧散文》中的敘述主體就是秦牧本人,他情感豐富、濃烈、暢達,總能憑借思想的羽翼,將古今中外的逸聞趣事、歷史典籍、社會百態恰到好處地融入散文創作中,使文章妙趣橫生、情思洋溢。作者在‘咀嚼敘事材料的過程中,從不忘記對共產主義、新中國、勞動人民等一切美好事物的贊揚和謳歌。也許《秦牧散文》在現在看來,難免卒讀,因為文中有一定的時代烙印和政治口號。但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秦牧與楊朔是散文界的旗幟,秦牧對于散文創作還提出了“一個中心”說和“一線串珠”論,這后來影響到了肖云儒的“形散而神不散”論。
馬克思說過這樣一句話:“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耀著無窮無盡的色彩。”雖然秦牧在創作中有時代的影子和局限,但他面對“共產主義”這樣一種生氣勃勃的先進思想時,盡可能地挖掘自己的創作靈感和寫作風格。《秦牧散文》中既堅持了政治方向的一致性,又綻放了藝術風格的多樣化,秦牧在政治宣傳與藝術傳承中搭建了一道和諧、多彩的橋梁。《雄奇瑰麗的中國山水》一文中,秦牧以全知視角向讀者敘述了中國大好河山的全景圖,有大川、內海、巨湖、山峰、森林……它們千變萬化、蔚為奇觀。待一一敘述完“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美麗景色后,秦牧沒有忘記將讀者的思想聚中,筆鋒一轉,敘寫的思想焦點便濃縮在文章結尾:“大自然的杰作是值得贊美的,人類雙手創造的奇跡應該說尤其值得謳歌。而真、善、美的東西,將超越時間和空間,打動我們大家的心靈。”秦牧就是這樣一位性格直爽、豪邁、情感充沛的散文家。他的散文中,充盈著人類智慧、社會大愛、自然大美的美好思想。
藝術品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物,它有自己的思想性,這是一個最重要的“根”。這個“根”與其他要素錯綜復雜地交合在一起,能衍變成無窮的情形來。秦牧的“根”在于對“共產主義”及真、善、美事物的敘述與宣傳,而余秋雨對自然山水的“排列組合”,則與秦牧迥然不同。
經典永遠通過重新解釋而獲得更新,《文化苦旅》的敘述主體不單純是作者本人,而是余秋雨對中國文化歷史命運和中國文人人格構成的探索。他的基本路子是,讓自然山水直挺挺地站著,然后把自己貼附上去,于是,他身上的文化感受逗引出它們身上的文化蘊涵。文中的敘述主體“我”,作為一種抽象的存在,早已對中國文化和文人有了密切的關注。自然山水風物作為一種客觀實體,它本身沒什么思想性,“我”作為中國文化、文人情感反思的化身,在與客體相互碰撞之后,則以自然物為依托,宣泄出自身的文化情感和“兩難”的困惑。例如,《道士塔》中敘述主體“我”被支解為三個小個體:真實行走的“我”、與王道士對話的“我”、內心掙扎的“我”。“我”在文中的解構,真實地凸顯了余秋雨“兩難”的心境,他愛佛教圣地、經書文獻,可他又恨,恨自己沒有早出生在那個年代;恨堂堂的佛教圣地居然讓一個道士來看管;恨,諾大的中國竟存不下幾卷經文!最后,他只能讓它停駐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場。這里,我們沒必要去質問作者是否真的會哭,因為“水至清則無魚”,文則“紋”也,適當的渲染,反而有利于提升藝術的真實和美感。
余秋雨是個性情中人,他總是帶著疑問和困惑,走向一片片廣闊無垠的文化空地。他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說:“‘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對歷史的多情總會加重人生的負載,由歷史滄桑感引發出人生滄桑感。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我在山水歷史間跋涉的時候有了越來越多的人生回憶,這種回憶又滲入了筆墨之中。”表象看來,余秋雨是自討沒趣,佯裝出一副老夫子、文化名人的姿態,其實,他筆墨間敘寫的是一些有關文化走向的嚴肅而不失知識性、趣味性的評述。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不敢對我們過去龐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卻希望自己筆下的文字能有一種苦澀后的回味,焦灼后的會心,冥思后的放松,蒼老后的年輕。”
與秦牧單純、質樸、淺易的愛國情感相比,余秋雨在散文中的“情”則更先智性、彈性、知識性。在文學界,雖“余秋雨現象”引來不少爭議,一些批評家沒有遵守西方諺語中“將鏟子說成鏟子”直言不諱的風格。可外界的惡批、指責絲毫沒有摧毀余秋雨對文化的執著體悟,及他與中國文人的傾心交談。對文化、文明、文人的思索和深刻剖析仍舊是他散文“根”的所在。
二、“形散神聚”彰顯不同的敘述模式與創作主題
散文在文學創作里是一種接近天然的文體,“真”“散”“美”是其核心特點。散文家李廣田在他《談散文》一文中,曾把散文的寫作比喻為一個人隨意散步,“散步完了,于是回家去”。借此,我更樂意將散文家喻為“列車長”,那么讀者則如坐上一列目的地明確的火車。這一比喻形象又很在理,因為,散文再散,它總應有一個“聚光點”,也總有一條情感、思想或理路的線索,引導讀者向那“聚光點”推進。
秦牧散文在敘述模式上,“常以理性為指導,把理念(主題)與物象(服務于主題的人、事、物、景等)對應起來,形成‘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的效果。”通讀完《秦牧散文》后,不難發現無論是寫景敘事,還是詠物論理,秦牧文章始終呈現著豐厚的情味韻致——恬靜、閑適、溫和、真摯。
在構思上,秦牧力求標新立異,但其文章在結構、材料的安排上,還是有跡可循的。開篇,作者飽滿的思想情感總是在一景一物或一人一事的刺激下牽引出來;文中,作者則以古今中外的名人軼事,或世間百態的奇聞趣事,加以敘述及引證;結尾,作者靈機一動,便用高度凝練的筆法概括中心思想。
例如,《英雄交響曲》中“從這些殘而不廢的親人們身上,我們想起了……這些事情使我們當日讀報的時候像給火燒到一樣。”《社稷壇抒情》中“這圖案使人沉思,使人懷古……想一想這些肥沃土地的來歷,你不由得涌起一種遙接萬代的感情……”作者的情感暖流并沒有就此停歇,“我在這個土壇上低徊漫步,想起了許許多多的事情……憑著思想和感情的羽翼……”較秦牧的敘述模式而言,其散文的敘述主題更容易概括。秦牧自己曾說過,他的散文是“寓共產主義教育于談天說地之中”。《秦牧散文》的創作主題,較多地體現了社會群體意識,以時代的政治的感情代替了作者個性化的情感,從而匯聚成一條“倡導愛國主義,稱贊好人好事,歌頌新生事物”的思想長廊。
任何文類開始時常是起源于作家的創造性嘗試。秦牧、余秋雨都是學者散文的代表作家,后者保存了學者散文的主因素,但在散文發展的縱軸線上,余秋雨又在敘述模式、創作主題等方面作了創造性的嘗試。秦牧的敘述在平實中見深沉,從容淡定,不夸張高尚的,也不渲染苦難的。余秋雨在敘述中則更顯靈動、冷峻和放逐抒情的意味。用韋勒克的“心理文體學”講就是:背離正常的精神生活引起的精神激動必須有一種背離正常用法的語言來表達。余秋雨用他好動的雙腳和親身經歷詮釋著自己對文化的珍視和對文人的珍重。
余秋雨以“游記”的方式,走走停停、思思索索,用簡勁而冷峻的文筆,敘述自己在游覽中國自然風物、名勝古跡時,對華夏幾千年文化的感慨、反思和評論。在散文創作中他建構了自己的敘寫模式,即以山水風物為依托,尋求文化靈魂和人生秘諦,探索中國文化的歷史命運和中國文人的人格構成。《文化苦旅》中由三個圓點,即詩性語言、故事和文化感嘆,構成一個堅固、嚴密的散文布局,從而形成《文化苦旅》“三足鼎立”的局勢:以詩性化語言敘說為外衣,以小說性敘事形態為肌體,以哲理性文化感慨為脊骨的散文框架。例如《江南小鎮》一文只看題目仿佛已聞到詩的味道了,文中“與顯赫對峙的是常態,與官場對峙的是平民……山林間的隱蔽還保留和標榜著一種孤傲,而孤傲的隱蔽究竟是不誠懇的……”既敘寫著優美的詩性語言,又交融著哲理性思辨的說辭。作者邊不緊不慢地敘述著江南小鎮的風俗人情,邊穿越時空隧道,將“李國香”、“陳逸飛”“沈萬山”“任蘭生”邀請來與他對話,沉思中國文人的歸息之地。
余秋雨就這樣深一腳淺一腳,輕一腳重一腳地行走在西北東南的文化空地上。雖然他踏足在蕭條、寂寞的山水風物間,但文章的敘述焦點從來就沒有脫離讀者的視線。用結構主義敘事學講,便是余秋雨看什么,看誰,說誰,關注什么都有一個立足點或是定點。這個定點便是文章的“根”,余秋雨把對文明、蒙昧和野蠻的思考仍然作為他為人為文不變的主題,并主要集中在文化反思和對傳統文化的理性批判上。
余秋雨的散文,在內容上,包羅萬象,文采斐然;在形式上,自由靈活,結構工巧;在句式上,長短相宜,富節奏感。秦牧,則體現出直截了當的一面,愛憎分明,善即善,惡即惡,單純而質樸,其敘述語言,多以短句見功,結構簡短而有力,活潑自如而明快。
縱觀上述,秦牧散文離不開敘事,余秋雨散文更是以敘事為肌體。“敘事”雖是小說解讀時的常用詞,但倘若作家能在散文中將敘事、寫人、寫景、抒情自由穿插,縱橫捭闔而收放自如,那么散文作為一種天然的藝術就得到了盡美的詮釋。
參考文獻:
[1]王耀輝.文學文本解讀[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2]穆厚琴.解讀余秋雨散文集.千年一嘆的敘事模式[J].淮海工學院學報,2003(6).
[3]曲慧芳.不同時代背景下的散文藝術——秦牧、余秋雨學者散文比較[J].集寧師專學報,2002(6).
[4]楊長勛.余秋雨的背影[M].廣州:花城出版社,2000.
(作者單位:重慶師范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