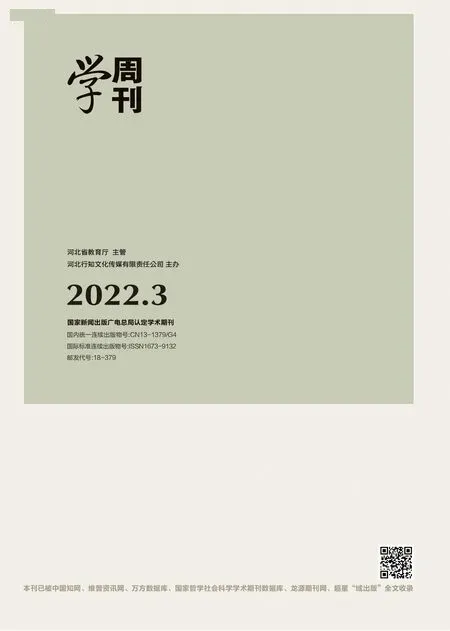于拷問與掙扎中的自慰與解脫
姚麗娜
《歸去來兮辭》是陶淵明歸隱后,在最短的時間內寫的一篇文章,也是除他的《飲酒》、《歸園田居》以外唯一一篇直接表露自己人生觀的詩歌,并將歸隱的情緒上升到樂天安命的哲理層面,即“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因為陶淵明初來田園,所以應把握該詩流露的復雜的交織著痛苦與釋然,并在矛盾中不斷寬慰自己、不斷自責自問的內心世界。劉勰在《文心雕龍?知音》中說:“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人情。”該辭正是抒寫了陶淵明內心的歸隱幽情,表現出他對官場污濁生活的厭倦,對田園愉快生活的贊美以及對勞動人民的歌頌。在整首詩中陶淵明作為一個農民式的詩人或隱士形象,表露幽情,暢談田園生活表決自己的人生選擇。我們可以通過整首詩的構思,把握住該詩感情的主線來引導學生背誦。這首詩一個重要的寫作順序即作者的行跡線索,采用由感到敘,由敘到感的圓和結構,因此鑒賞的關鍵就是陶淵明復雜的隱逸情緒與表現在形式上的詩歌構思。
離開官場是一身的輕松與釋然,但同時伴隨著儒家知識分子仕途受挫的強烈痛苦,所以痛苦是一時難以釋懷的,體現在該詩中就是詩人在不斷的自我拷問中尋找答案,窺視自己的心靈,如“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又有第三段“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詩人在復雜的心理矛盾中自我寬慰,這是陶淵明獨特的思考、解脫方式,即不斷的自我拷問。第三處即第四段“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違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三次發問即是三次心理的掙扎與解脫的過程,尤其是“遑遑”二字集中體現他心神不安的官場失意情緒。
詩人,永遠也不會逃離詩歌的王國,浪漫應該是其骨子里的氣質。所以即使歸隱田園陶淵明也是一個農民式的詩人形象出現,由詩歌的具體詩句中可以看出“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什么都可以沒有,就是不能失去靈魂深處的寄托,松菊是其最愛,松菊即詩人人格的化身。所以詩人在詩中的首選意向為松菊。陶淵明詩歌“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可以看出陶淵明獨愛菊,菊也因此成為高貴的隱士象征。又如第三段“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可見,琴書是充滿詩情畫意的詩人式生活,也是排遣苦悶生活的一種方式。由此可以看出一個知識分子的形象。又如“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詩人的腳步尋幽訪壑,親近自然,熱愛生活,這是他內心萌動的詩情。又如最后一段:“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詩人離不開物質世界,他必須進行田園農耕,忍受“草盛豆苗稀”的尷尬生活,這是詩人兩重身份使然。
又是一年春光好,良辰之際,詩人更加不安分,所以“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在與鄉里鄉親的對話中,詩人珍惜良辰,所以出游,因此他感受到了季節的律動“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斗轉星移,春季最是萬物萌生繁榮的季節,從中詩人感到了生命的律動,敏感的心會因此傷春感懷,生發“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的感嘆,幾許無奈,無限感傷,溢于胸中一吐為快。
在整首詩中,我們看到了一個苦吟的詩人,即使在一間陋室,有一瓢飲,一簞食的艱難物質生活條件下。陶淵明也在努力追逐詩人的夢想,所以才成就為一代山水田園詩的開山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