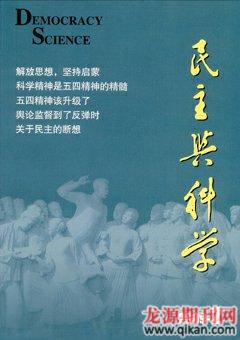期待新醫(yī)改方案推進(jìn)稅收法治
楊 濤
4月7日公布的《醫(yī)藥衛(wèi)生體制改革近期重點(diǎn)實(shí)施方案(2009-2011年)》提出,中國將在三年內(nèi)把基本醫(yī)療保障制度覆蓋城鄉(xiāng)全體居民,參保率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2010年,各級(jí)財(cái)政對(duì)城鎮(zhèn)居民醫(yī)保和新農(nóng)合的補(bǔ)助標(biāo)準(zhǔn)提高到每人每年一百二十元人民幣。
對(duì)于這一新的醫(yī)改方案,許多人從不同角度進(jìn)行了解讀,比如這有助于促進(jìn)民生,有助于拉動(dòng)內(nèi)需,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發(fā)展,但我更愿意從另外一個(gè)角度來解讀這一事件,我希望這一次新醫(yī)改,能成為走向稅收法治的一個(gè)新的起點(diǎn)。
稅收法治是現(xiàn)代國家的一個(gè)基本原則,稅收法治原則上應(yīng)當(dāng)包括兩個(gè)方面,一是程序上的法治化,就是稅收的征收和使用上必須遵循正當(dāng)法律程序,這包括在制定稅收種類、稅率等方面必須由人民授權(quán)的代議機(jī)構(gòu)來決定,這就是所謂的“無代表不納稅”,也包括政府所收取的稅收的使用必須通過代議機(jī)構(gòu)來決定;二是實(shí)體上的稅收法治原則,就是稅收在征收和使用上必須合理化,特別是在稅收的使用上,各項(xiàng)開支所占比例必須合理,為公共福利事業(yè)的支出必須占到稅收收入的大部份,因?yàn)槎愂占热皇菑墓娛种姓魇眨捅仨殲楣姺?wù),而政府本身并不能創(chuàng)造財(cái)富,稅收的收入不能單純?yōu)檎陨硐摹?/p>
程序上的稅收法治化,我們做的并不理想,當(dāng)前除少數(shù)稅種是由全國人大決定外,大部份的稅種與稅率都是由全國人大授權(quán)國務(wù)院或者國家部委自行決定;而對(duì)于征收上來的稅收的使用,同樣在程序上存在問題,每年全國、地方人大都會(huì)對(duì)政府預(yù)算進(jìn)行審議,但由于時(shí)間匆忙、所列入項(xiàng)目簡單,這種監(jiān)督并不到位,以致前不久河北省承德市人大兩次退回政府預(yù)算報(bào)告成為各大媒體的新聞事件。
實(shí)體上的稅收法治化,同樣存在問題。在所有財(cái)政收入的支出,公共福利支出非常欠缺(約占總支出的50%),而政府的自身支出卻相當(dāng)?shù)母撸?006年中國政府的預(yù)算內(nèi)行政支出占財(cái)政總支出的比重為18.73%(如果加上預(yù)算外支出,有學(xué)者估計(jì),中國政府的實(shí)際公務(wù)支出至少占政府全部支出的30%以上),遠(yuǎn)遠(yuǎn)高于日本的2.38%、英國的4.19%、韓國的5.06%、法國的6.5%、加拿大的7.1%以及美國的9.9%。本次全國政協(xié)大會(huì)上,九三學(xué)社中央副主席、浙江大學(xué)教授馮培恩委員列舉了公務(wù)用車消費(fèi)、公款吃喝消費(fèi)、公費(fèi)出國消費(fèi)、政府會(huì)議消費(fèi)、“政績工程”和辦公樓建設(shè)消費(fèi)、能源和資源消費(fèi)等六種政府消費(fèi)行為,例如公務(wù)用車方面,他調(diào)查認(rèn)為我國目前大約有400萬輛公車,每年消耗超過2000多億元,其中真正用于公務(wù)的約占1/3;公費(fèi)出國、公款吃喝每年各不少于2000個(gè)億,至少吃掉一個(gè)三峽工程。
在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方面,同樣在整個(gè)財(cái)政支出所占的比例特別小,而且國家根本就沒有規(guī)定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投入占GDP的百分比。從數(shù)據(jù)上顯示,衛(wèi)生總支出占中國GDP的比重,2000年是4.6%,2003年是4.5%,2005年是4.7%。這遠(yuǎn)低于歐州國家6%到10%的水平,更低于美國,2003年,美國公共醫(yī)療投入占GDP的比重是13.9%,而到了2006年,美國的公共醫(yī)療投入占GDP的15%。而且,就是有限的醫(yī)療投入,也主要用于官員的醫(yī)療。原衛(wèi)生部副部長殷大奎引述中科院的一份調(diào)查報(bào)告的數(shù)字稱:中國投入的醫(yī)療費(fèi)用中,80%是為850萬以上黨政干部為主的群體服務(wù)的。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jí)干部長期請(qǐng)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干部長期占據(jù)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等,一年開支約500億元。為此,醫(yī)學(xué)專家黃建始呼吁政府要加大在衛(wèi)生領(lǐng)域的投入,并且“應(yīng)該在制度上明文規(guī)定下來,對(duì)健康的投入應(yīng)該占GDP的多少”。
此次《實(shí)施方案》提出,到2010年,各級(jí)財(cái)政對(duì)城鎮(zhèn)居民醫(yī)保和新農(nóng)合的補(bǔ)助標(biāo)準(zhǔn)提高到每人每年一百二十元人民幣《實(shí)施方案》還強(qiáng)調(diào),各級(jí)政府要認(rèn)真落實(shí)《意見》提出的各項(xiàng)衛(wèi)生投入政策,切實(shí)保障改革所需資金,提高財(cái)政資金使用效益。為了實(shí)現(xiàn)改革的目標(biāo),經(jīng)初步測算,2009-2011年各級(jí)政府需要投入8500億元,其中中央政府投入3318億元。我希望,以此次新醫(yī)改方案為契機(jī),進(jìn)一步合理分配財(cái)政收入,推進(jìn)稅收法治的貫徹。因?yàn)椋獙?shí)施新醫(yī)改,政府必然要加大對(duì)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的投入,但是,我們公共福利事業(yè)所占總投入的比例本身就小,因此,醫(yī)療衛(wèi)生有加大投入不能占用其他公共福利(例如教育)的投入。醫(yī)療衛(wèi)生中加大了的投入,就必須將行政開支降下來,這樣不僅使得醫(yī)療投入的資金有保障,而且使得公共福利事業(yè)在政府總支出所占的比例趨于合理,使得稅收的支出更合理化。而要做到這一點(diǎn),就必須做到兩點(diǎn):一是通過法律明確規(guī)定醫(yī)療衛(wèi)生的投入要占GDP的比例,以及公共福利事業(yè)占GDP的比例,并且要在現(xiàn)有基礎(chǔ)有比例有較大的提高;二是通過法律明確規(guī)定進(jìn)一步降低行政開支占GDP的比例,使得稅收的收入主要用于公共福利事業(yè),各項(xiàng)支出占GDP的比例趨于合理,真正實(shí)現(xiàn)“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進(jìn)一步推進(jìn)稅收的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