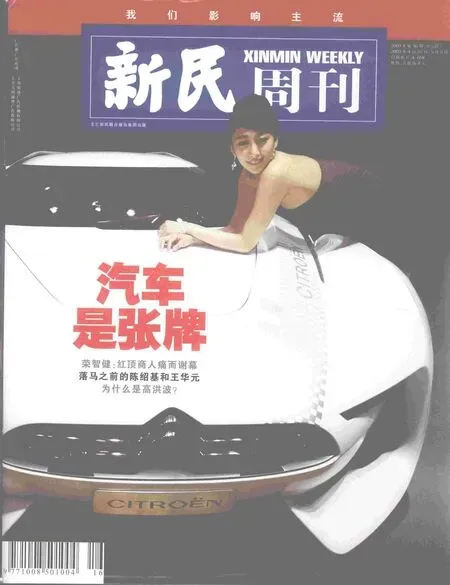高管薪酬:讓人羨慕讓人憂
唐寧玉
當人們還在為金融危機何時見底這個話題疑慮擔憂的時候,一些上市企業高管2008年薪酬的披露,引發又一場爭議和討論:在金融危機時代,那些高管們拿的報酬是否過高了?
高是相對的,當前高管薪酬引發爭議,焦點有兩個:一是高管薪酬和企業經營業績之間的關系,二是高管薪酬和一般員工之間的差距。這兩個問題歸結到一起也就是高管薪酬的合理性問題:多高才算合理,差距多大才能體現激勵。
爭議波及國內外。美國國際集團(AIG)去年下半年獲得美聯儲850億美元緊急貸款后,今年3月份向部分在職或計劃聘用人員發放高達1.65億美元的留任獎金,引來上至總統下至平民的一片聲討。同時,雖然不少華爾街機構去年巨額虧損,部分知名企業倒閉,政府更推出龐大救市方案,但紐約審計處資料顯示,華爾街金融機構職員2008年共獲184億美元花紅,是史上第6多的一年。再看我國內地,已公布的上市公司2008年年報顯示,在金融危機沖擊下,上市公司經營業績普遍下降,截至4月13日,946家披露年報的公司去年共實現凈利潤6841.52億元,同比下降8.89%,這些公司的高管年度薪酬總金額為32.67億元,同比增長16.25%。從收入差距看,1980年,美國主要公司CEO的報酬是一般計時制員工收入的40倍,1990年增長到85倍,到了2000年則變為531倍。而在我國國有企業中,改革開放之前企業高管和一般員工之間收入差距通常不會大于4倍,而去年兩者收入差距懸殊,這改變了以往高管激勵不足的局面,卻導致另一個疑問,是否對高管激勵過度了?
那么,是什么導致高管薪酬一路升高,并和一般員工差距越來越大呢?從學術角度來說,有多個理論如委托代理理論、人力資本價值理論、企業家市場競爭論、風險論等可以作為高管薪酬制定的依據。首先,現代企業中,公司所有者與高層管理人員之間存在著委托代理關系,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想要實現各自的利益目標;其次,作為代理人的高層管理人員經過長期經營管理活動的實踐,積累和培養了一般人所不具備的知識、經驗和才能,使他們的人力資本成為社會生產活動中的稀缺資源,從而在勞動力市場上享有較高價格;再次,根據企業家市場競爭論,高層管理人員之所以能晉升到公司的高級管理職位,是其長期付出大量努力,在層層選拔中脫穎而出的結果。高收入體現了競爭的最終結果,如果和下面員工收入差距加大,能起到激勵中下層管理人員努力工作、爭取提拔的作用;再有,由于高管處在公司領導位置,其行為往往關系到企業的生死存亡,因而他們需要承擔企業盈虧和自身經營聲譽的責任和風險。
這樣看來,高管拿高薪不無道理。但支持高管人員高薪酬的理論背后,是“高薪酬——高人才——高績效”的假設,如果這個假設成立,會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對企業、高管和其他利益共享者來說都是皆大歡喜,但如果只有“高薪酬——高人才”而沒有“高人才——高績效”的實現,則會產生問題。遺憾的是,從現有研究和資料來看,高薪酬和高績效之間關系并不十分確定。問題還在于,如果“為績效付酬”是高管薪酬遵循的主要原則,其核心問題是績效指標的設定、高管薪酬中績效部分所占的比例以及該如何兌現和績效掛鉤的那部分獎勵。與此相關的關鍵是,高管薪酬究竟應由誰來制定,又如何來制定。
高管薪酬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事實上難有完美的方案。筆者認為,針對目前存在的種種不足,可以采取如下一些改進措施:一是在高管薪酬決定機制中,薪酬委員會或其他出資人機構要做更審慎的決策,對高管要更明確績效目標,做到責任和權利、收益和風險共存,體現委托-代理的雙贏關系;對職業經理人的薪酬水平、績效薪酬比例等可以通過市場調查以及和績效之間關系的預測來確定;高管薪酬應該和企業總體經營業績效應緊密關聯,并有一定的長期性和延時性;其二,高管薪酬應更為透明,透明化無形中會通過社會群體壓力和外部市場比較對高管薪酬的合理化起到推動作用;其三,通過建立高效率的市場評價機制,保障合理設計的激勵機制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無論是年薪制還是股票期權制,外部市場評價機制和企業內部監控機制的匱乏會將制度本身的缺陷加以放大,這也正是我國企業所面臨的現實問題。因此,對所有企業而言,讓資本市場成為企業評價的主戰場具有重要意義;其四,提高高管的責任意識、風險意識和其他經營勝任能力。如一些高管主動采取的放棄年薪或將分紅捐給公司的做法,在危機時代或許可以振奮一下人心,相對來說也使得人們對該企業的高管薪酬有更好的接受度。畢竟,對高管薪酬的看法不僅僅是一個客觀現實的問題,更涉及到人們的認知評價和預期。再有,如果高管們真把公司當作自己的事業一樣經營或許也會有所不同,如巴菲特所言,“如果要有更好的公司治理,唯一的途徑是那些非常大的機構投資者中的少部分人開始像真正的公司主人那樣行為并使得經理人員和董事會成員也如此做。”(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