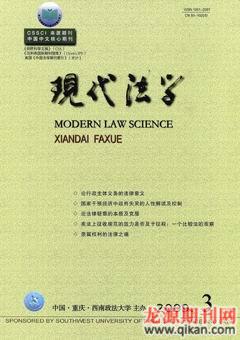國家干預經濟中政府失靈的人性解讀及控制
胡光志 靳文輝
摘要:對政府失靈及其緣由的追尋和考究,是經濟法學人長期以來的不懈追求,也獲得了諸多真知灼見。然而,鮮有人注意到,人性中的“強”、“群”、“樂”等因素,才是政府失靈更為深刻的原因,從干預者人性的角度對政府失靈進行解讀,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可靠的認識論基礎,也可為經濟法克服政府失靈提供有效方向和路徑。
關鍵詞: 國家干預;政府失靈;人性;控制
中圖分類號:DF41
文獻標識碼:A
任何一個現代政治系統都包含一個特定的干預經濟的子系統,其存在的根據,在于其與現實社會之間的功能聯系——由于市場失靈作為市場的內生品格不可避免,通過來自國家的干預以有效消除市場機制的負效應便有了正當的社會基礎。然而,歷史的經驗和現實的情勢都表明,來自政府的干預并非“父愛”般地存在——這種隱含了秩序建構主義邏輯的行為,在實踐中又會因可能出現的政府失靈對市場機制構成威脅和破壞;因此,準確認識政府失靈的內在機理,理應成為經濟法思維的“起點和終點”,也應成為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經濟法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
政府失靈理論是在經濟法學人長期不懈的追求之下,所獲得的頗具真知灼見的理論觀點,是構建經濟法核心理論的支柱之一。目前諸多的文獻對作為經濟法核心理論支柱之一的政府失靈的論述,大致都圍繞干預主體智識有限、利益偏好、能力不足以及由此造成的干預越位、干預錯位、干預缺位等內容進行。這些論述的意義和貢獻固然毋庸置疑,但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政府失靈的內在原因是什么?作為主體的“人”與政府失靈現象是否具有關聯?有什么樣的關聯?導致政府失靈的人性基礎是什么?休謨指出:“一切科學對于人性總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聯系,任何學科不論似乎與人性離得多遠,它們總是會通過這樣或那樣的途徑回到人性”。基于人性在科學中的作用,休謨還認為,如果我們對人性有了透徹的把握,我們的任何學科就有希望輕而易舉地取得勝利,因為一切學科的“首都和心臟”,便是人性本身[1]。在筆者看來,即便是最具工具理性和技術優勢的制度,其產生和運行都不可避免地要與人發生關聯,而人性發展和演化的規律才是政府失靈更為深刻的內因。只有從人的角度對政府失靈進行認知和解讀,通過對隱藏在政府失靈背后的人性問題的探求和關注,才可能為我們正確解析政府失靈提供一個可靠的認識論基礎,也才可能為最終克服政府失靈提供一個有效的路徑和方向。
一、從人性之品格直面政治人的人性真實
“認識你自己”,這是古希臘阿波羅神廟前殿墻壁上雕刻著的箴言。千百年來,古今中外的無數學人圍繞著“人是什么”、“什么是人性”的問題,形成了多種多樣的哲學思潮和哲學流派。作為對人的自我追問,人性問題源于人的自我意識。對于人之所以為人來說,它具有前提的意義[2]。 然而,人的問題卻又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人性到底是什么?不管是傳統“善”、“惡”的基本判斷,還是“政治人”、“經濟人”、“道德人”、“審美人”、“宗教人”、“社會人”的分類,以及人性究竟是人的本質還是人與動物之區別的分歧,似乎都說明人性是什么的問題本身是一個博大艱深、無法統一、難以捉摸的神秘命題。實際上,人性是人基于生存與發展而產生的天然心理傾向,這種傾向既包括人的社會性也包括人的生物性,它決定了人的意志和行為,因而也決定了人的生存方式;也就是說,人性是人作為人的天然本能,是人的一切活動和外部表征的內在根據[3]。也許我們的確無法窮盡描述人性的方方面面,但正如有學者所論述的那樣,“無力真實描述現象的方方面面,并不會使理論無效,相反,一種企圖忠實復制經驗世界全部真實性的理論卻不是真正的理論,它只是一種描述”[4]。“就個體人性而言,生、性、群、強、樂是每一個人在完成自身生命歷程中的必然追求”[5]。基于這樣的理念檢視政治中的人性,筆者認為,政治中的人性主要體現在人性的“強”、“群”、“樂”等3個方面:
(一)人性中的“強”與政治人的權力追求
與自然界中的“物競天擇”一樣,社會中的人具有追求“出類拔萃”、“出人頭地”、追求生存的強大與完美的心理傾向。“當人的活動從社會領域或經濟領域進入以公共權力為載體的公共領域,就由社會人或經濟人轉化為政治人”[6]。事實上,進入政治系統只是人身份的轉化,這種轉化并不改變人與生俱來的求“強”的天然心理傾向。在筆者看來,政治中人性的“強”主要體現在政治參與人對政治權力——即決策、控制、影響、任免和獎懲他人的能力的占有和追求——一種精神上實現自我、成就榮譽的期待。
現實中存在的權力類型多種多樣,但其中最具影響力、最具吸引力、最能對客體予以“合法”的控制和支配的,便是政治權力。毋庸置疑,政治參與人最具有接近這種權力的可能性。“官大一級壓死人”,在政治領域,衡量一個人能力的大小和強弱的標準,是其所處職位的高低和擁有權力的大小。盡管實存的政治生活中大量存在著追逐財富和物質利益的現象,
(注:對物質利益的追求不能一概而論。有時,求“強”的人性因素促使政治參與人會憑借物質利益去獲取更多的政治收益,比如買官、賄賂等,但通過交易獲得權力畢竟不是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現象。故筆者認為,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更多是為了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是政治人人性中“樂”的因素使然。對此將在下文探討。)但財富的數量并不是衡量一個人政治能力強弱的標準,我們從來不用收入的多少來衡量一個人仕途的成功。現代政治哲學奠基人霍布斯早就從權力的概念出發,談到了公共領域中個人的價值或身價的問題。他認為,個人的價值或身價就是一個人的價格或價錢,指的就是一個人的權力使用能夠開什么價,值多少錢的問題。他說:“一個人在公眾中的身價,就是國家給他定的價值,人們通常將其稱作高位。這種國家給他定的價值可以理解為通過擔任軍隊、法庭和公共部門的要職來體現;或者是可通過顯示不同價值的名稱或頭銜來體現。”[7]而職位的高低、頭銜的大小又與其所擁有的權力之間密切關聯,理性的政治參與人在獲得一個職位或頭銜后,人性的因素決定其必然會產生追求另外一個更大權力的欲望。而且“這一欲望是永恒而無休止的,至死方休。究其原因,……不是他不能滿足于適度的權力,而是因為如果他不能獲得更多的權力,他就不能放心現在己經獲得的權力和手段能否保障他生活得很好。”[7]65由此觀之,求“強”的人性基因決定了理性的政治參與人,必然會以對更高的職位以及與之相伴的更大的權力的不懈追求為其政治生涯中的目標指向。政治與權力如影相隨,政治的核心要素是權力;在此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對政治權力的追求體現了政治理性人質的規定性。
(二)人性中的“群”與政治人的政治歸屬感
在人與自然界的斗爭中,群體生活成了人類保存自己走向強大的最佳手段。同時,人只有在群體生活中,才能保存自己、表現自己和發揮自己。事實上,群體生活不僅是人的普遍心理需求,更是人類的基本生存方式。每個人都有天然的對群體的依賴心理,每個人也只有在群體中才被感知是人的存在[3]10。筆者認為,在政治生活中,人同樣渴望一種群體性的存在;尤為重要的是,在現代政治場域,惟有群體性的存在,獲得權力才成為可能。
現代政治是政黨政治。“天下者,黨派之天下也;國家者,黨派之國家也;歐西各國政治,皆操于政黨,……故文明之國,但聞有無國之黨,不聞有無黨之國”[8]。筆者在此無意考究政黨存在的社會基礎和產生的歷史條件,但一個不容爭議的事實是:作為一種具有相同或相似追求和利益的人的“團結和聯合”(“群”的體現),作為一個首先具有工具理性的存在物,政黨存在的根本目的,是借助群體的力量,來達到特定的目的(政黨綱領多有規定)并獲得一定的利益;政黨產生的緣由,首先是對群體力量比單個人力量強大的認知。由此看來,是人性的原因把人分為不同的派別,政黨的產生同樣具有深刻的人性根據。作為單個的政治參與人,他們或基于不同的階層和身份,或基于不同的利益渴望,或基于不同的信仰和追求,勢單力薄的現實和人性中求“群”的基因決定了其必然尋求一種“依憑”和“依托”。“那些野心勃勃、爭權奪利的政治領袖,或者那些擁有巨大財富的人,都會使人們產生依附感”[9],于是加入某個政黨,尋求一種政治歸屬和認同,進而獲得政黨的支持和幫助,便成為現代社會單個人追求政治權力的重要途徑和當然選擇。
不僅如此,在政黨內部,甚至在單個的政府職能部門內部,也會產生相對獨立的派別和團體,現實政治中常有“跟對人”、“站錯隊”的說法。一個政治參與人對派別或團體選擇的正確與否,常能成為其仕途能否順暢的重要因素,有時甚至是決定性因素。其實,“站隊”與“跟人”的最終指向,是所屬群體對某個政治參與人幫助的可能和程度問題,“站隊”和“跟人”行為,也不過是對某一領導人“帶領下”的相對獨立的群體的發展前景和發展潛力的預期,當然這種預期受到個人理性有限的制約,有時也許是一種被動選擇的結果(如某些天然身份,如校友、戰友等等);但人性中“群”的因素決定了很難有政治參與人游離于派別之外獨善其身,這何嘗不是政治中人性尋求歸屬和依憑——“群”的體現?
(三)人性中的“樂”與政治人的享樂追求
不管人的心理欲求何其豐富,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人首先是一個生物,具有“飲食男女”、“食色之欲”等自然屬性的特征,政治參與人也不例外。政治人人性中的“樂”,是指政治參與人通過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期望達到舒適、情感、消遣、快樂等生活狀態的心理渴望。(注:需要說明的是,對非物質的利益的追求,比如前文論述中所謂求“強”的人性因素造成的對作為精神利益的權力的追求,同樣可以讓政治參與人產生快樂、愉悅的心理體味,權力的獲得也可能會讓政治參與人的生活狀況改變、生活質量提高,“強”和“樂”似乎沒有明確的界限。筆者之所以作這種技術性分類,主要是為了論述的方便。此外,筆者認為,人性中的諸多因素,本身是相互關聯、難以拆分的組合,人的各種需要和動機,會相互發生作用,試圖對人性要素進行完美無疑、絕對精確的分類,既不可能,也沒必要。)這種“樂”固然與其他人對“樂”的追求并無不同,但由于求“樂”的心理傾向會影響甚至改變政治參與人理應具有的目標追求和結果導向,影響甚至改變政治參與人的行為屬性和行為方式,其后果可能是政府行為與公共利益的要求、社會的期待相背離,故在此有單獨論述的必要。
不管如何通過教化去尋求精神的超越和救贖,人首先是一個肉體的存在。自利是生命存在的動機,也是生命存在的條件,更是人性的重要內容。從荀子到韓非子;從亞當?斯密到布坎南;從柏拉圖到洛克、霍布斯;以及威廉?配弟、斯賓諾莎、馬基雅維里、馬克思等先哲們,都不否認人性中追求自利的屬性——就是那些最極端的道德論者,在談及人性時都不否認人具有追求“自利”的永恒特征——即使他們認為這種自利是一種“有限的自利”。不僅如此,現代經濟學以人的自利性為基本預設來構建該學科,其中公共選擇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更是將其發揮到了極致,并對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學科產生了廣泛影響,為其他學科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學術增長點”,“經濟學帝國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稱謂,恰恰反映了這種人性假設的擴張態勢和合理之處。對于人性中“自利”、“求樂”的表現,現有文獻已有相當精準的論述,筆者不再贅述。
二、從政治人人性看國家干預經濟中的政府失靈
一如前文所述,任何制度的制定和運行都不可避免地和人發生關聯,任何制度都必須建立在具體的、歷史的人性基礎之上。“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制度的成功與失敗都有著深刻的人性基礎。作為一門政治藝術,作為一項權力委托,國家干預經濟的行為理應以社會公共利益為導向,以對市場缺陷的有效克服為依歸。然而,現實中的國家干預經濟的行為有時卻因干預的錯位、缺位、越位導致干預的功能失調和效用消減,亦即因所謂的政府失靈而偏離人們的期待。事實上,經濟法的產生過程有著必然的經濟動因,其運行過程更有著必然的效益特征和經濟性評判標準。而這種與經濟性密切關聯的事實,在上述“人性”因素的影響下,導致了政府在干預經濟的過程中更容易出現政府失靈。筆者借助上文對政治中人性的揭示,試圖分析國家干預經濟中政府失靈現象產生的人性緣由。
(一)政治權力的追求與政府失靈
一如前文所述,求“強”的人性基因意味著,政治參與人以對權力的占有和追求為基本訴求。筆者認為,干預者在求“強”的心理激勵下,可能導致干預失敗的情形主要有:第一,干預權擴張,引發政治極權主義。首先,對權力的追逐意味著政府的能動和自主——于是盡可能多地擴張國家干預的空間,盡可能多地尋求干預的機會,是這種干預能動性下的當然結果。國家對經濟的全面干預和經濟控制權的高度集中在所難免,旨在消除、預防、克服市場缺陷的國家適度干預異化為國家權力對市場正常機制的干擾、踐踏、扼殺和破壞。其次,對既得經濟職權的不舍和難以放棄,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放權困難”。“在政府中,一種不斷重復的傾向是保住自己的權力范圍,抗拒變革,建立各種獨立王國,擴大自己的控制地盤,不管是否需要都要保住項目和計劃”,[10]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有近20年的歷史,但市場的空間和范圍依然較為有限。國家對過度的干預的慣性依然存在,計劃和干預的力量依然過于龐大,各種市場要素的發育依然不充分,市場仍然處處受掣肘,政府權力對市場的限制仍然過多。據報道,“目前海南的餐飲業有近20個‘婆婆,其中包括衛生、防疫、勞動、社保、消防、動檢、工商、稅務、旅游、質監、公安、物價、環保、環衛、文體、城管和街道辦事處等政府部門,還有自來水、排污、治安聯防等等”[11],這充分說明讓權力既得者放棄所擁有的權力是何等困難。第二,對權力的追逐意味著政治參與人對自己仕途的過分關注,而“我國官員的選拔和晉升標準由過去的純政治指標演變成經濟指標,尤其是地方GDP的增長,導致中國的經濟發展帶有很強的政治激勵性”[12],在這種政績觀的指引下,干預經濟過程中的政績工程、“數字政治”、政府行為短期化等現象禁而不止。當下,提供公共產品的行為變成形象工程;市場監管中長效監管缺位,“運動式”執法成為執法的常態;宏觀調控執行機關對調控決策的不當修正,名義上的“造福一方”變成了實質意義上的“官意表達”;社會保障、社會救濟更多是電視屏幕、報刊媒體上的一時作秀;等等。“‘數字出官、‘一哄而上、‘工程獻禮、‘借貸開發”[13],都是這種心理激勵下的行為表現。
(二)政治人的歸屬感需求與政府失靈
筆者認為,干預規則的制定者和適用者求“群”的心理傾向,可能引發政府失靈的情形主要有:第一,由于眾多干預主體以相對獨立的“群”的形式存在,由此導致干預權行使中政出多門、爭權奪利、機構重復建設等現象難以避免;干預效率低下,內耗嚴重、干預主體之間相互推諉和扯皮、內訌和割據、缺乏協調配合是這種情勢下的必然結果;干預主體合作治理、合作干預的理想狀態無法實現。事實上,當下嚴重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地域封鎖、行業壟斷、行政壟斷、地方保護主義等現象,無不與政府官員“群”的人性基因有關;我國宏觀調控政策執行中的政令不暢、各自為政、短期行為造成的全國整體經濟形勢的失衡和過熱,更是與各地政府的“群”心理激勵密不可分;我國多層次立法體制下,經濟立法中法律與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其實也可從“群”的人性因素中找到原因。第二,經濟職權行使者的自主性缺失,引發政治消極主義。眾所周知,市場缺陷的偶發性、不連貫性、潛伏性等特點,要求現代經濟法應具有回應性、預警性、相機性等特征[14],干預主體應以更加主動、積極、靈活的姿態,以創造性的思維和行動去應對市場機制引發的諸多弊病和問題,但在“群”意識的指導下,干預者為了和所屬群體的思維方式、行為習慣保持一致——為了“遵循通則”、避免脫離所在群體而孤立存在——他們或出于對“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的恐懼,或出于對“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中庸之道的固守,于是導致經濟職權運行中的決策滯后、執行滯后、效用滯后等現象。第三,求“群”心理傾向導致干預機構臃腫、人浮于事。“群”的最本源含義是“人多勢眾”,于是盡可能地擴大自己群體的“勢力范圍”,以追求“人多力量大,人多好辦事”的效果,是求“群”的人性基因關照下的必然選擇。
(三)政治人的享樂追求與政府失靈
“政府及其公務人員在社會上的多重角色和身份使其在追求社會利益最大化和追求部門利益、個人利益之間存在著持久的沖突”[15],而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因此,這種沖突最為可能的結果,是政治參與人在政治決策和執行中將個人利益凌駕于社會公共利益之上。在筆者看來,在政治人“樂”的心理激勵下,政府干預經濟中可能出現的失靈表現,主要包括:第一,干預權創租,干預主體被俘獲,干預決策和運行受個人、集團、地區利益的擺布。“創租指的是那種利用資源通過政治過程獲得特權從而構成對他人利益的損害大于租金獲得者收益的行為”[16]。有學者總結了我國存在的權力創租的幾種形態:無意創租——產生于政府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管制的結果,或者說產生于政府的“良好的主觀愿望”。利率和匯率雙軌制就是典型的政府無意創租行為;被動創租——政府由于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誘使或迫使,利用其職權,創造和維護某些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主動創租——政府部門及其公務人員預期到尋租行為為其帶來的收益,從而通過行政干預主動創造租金[16]64。在筆者看來,這些權力創租形態在我國的經濟干預權運行中“一個都不少”:國家宏觀調控、產業規劃、產業調節中的無意創租;授予某些企業市場開發、市場準入、資源傾斜性分配、產品合格監管、上市許可中的主動創租;保護某些企業避免競爭從而長期保有壟斷高利潤,如專營許可證頒發、壟斷經營許可中的被動創租等。第二,干預權行使過程中的其他腐敗現象,諸如受賄、索賄、吃回扣、貪污、侵吞公款等等,這一切都是求“樂”的心理渴望下的可能結果。當然,這些腐敗類型和其他權力領域中的腐敗類型并無不同,相信讀者早已耳熟能詳,筆者不再展開論述。
三、克服國家干預經濟中政府失靈的人性思考
所有制度都不可能成為自足的運行主體。那種試圖構建“基于可預計性原則而脫離人性,成功地在職務事務中排除愛、憎和一切純粹個人的、從根據上說一切非理性的、不可預計的感覺因素”[17]的最佳干預經濟的制度,以便一勞永逸地實現對市場失靈有效矯正的愿望,只能是一個美好的理想——筆者的論調并不悲觀,其實筆者更愿意認為政治中的人性只是一個客觀存在而沒有“善”、“惡”的倫理區分——事實上,“強”的心理激勵同樣可促使政治參與人為實現公共利益實施公共行為,并由此來滿足“自我實現的需求和榮譽感”[6]55;求“群”的心理傾向也能達致群策群力的合作治理,并避免“拒絕合作、充斥著不信任情緒以及冷漠盛行”[18]。干預者“既可以將自己置換成為一個屠夫式的操刀手,也可以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眾人矚日的道德家”[19]。因此,我們既應拋棄期待和仰賴干預者完美人性的理想和浪漫情懷,也不應失去通過道德和制度弱化干預者人性消極面的信心。“彰善癉惡”、“有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懲干預者人性之惡,揚干預者人性之善”,在避免出現一個“最壞政府”的基礎上尋求“次好政府”以至“最好政府”,才應該是我們“務實中的理想”。在克服政府失靈的過程中,干預者的道德約束、內心自修、干預者選任機制、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的構建等等,毋庸置疑是有效的,而且是必須的。限于文章篇幅,筆者僅僅從道德引導和法律制度構建兩方面予以論述。
(一)道德的引導和激勵
這是一個并不新鮮的話題,也是一個為法治論者所詬病的話題。但不容爭議的是,在人類社會中,道德作為人類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種重要價值規范,它是人類和諧生活的內在依據與外在支撐,它尋求的是人生的幸福和心靈的安頓,它寄意的是真善美的境界,它關注的是人性的提煉與升華。對于著意于“詩意”般地存在的人而言,道德不啻是尋求生活意義的精神家園,其重要性不言而喻[20]。美德不可缺,倫理道德規范深深嵌入整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不管是西方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開創的以“美德”為核心的道德體系的構建和追求,還是中國的儒家對“為政以德”、“仁者愛人”、“內圣外王”等倫理精神的推崇和強調,都說明對社會治理者(理所當然包括經濟干預者)來說,這種倫理規范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道德倡導人性中的正直、廉潔、仁義,譴責沉湎于物的積累、奢侈浪費,這種與善良、仁愛關聯的直覺是一種強大的力量,它在促導干預者充分展現人性積極面以及干預者行為自覺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從來不否認教化的功用和價值,否則一切學校等教育機構和監獄等改造機構就沒有存在的理由。
當然,筆者也并不否認對干預者道德的強調可能導致的“道德”與“人治”合流的潛在危險,但我們同樣也不能因噎廢食,把道德當成洪水猛獸。“唯有法治才是治國之真諦。……然而,承擔這些立法、司法和行政事務的,當然不會是人以外的神。在這里,德治主義又可以被賦予新的意義,即并不希望產生一位圣明天子,而是對分擔三權的‘治者必須有‘德的要求”[21]。在筆者看來,道德和法律等其他正式制度在保證干預權規范、合理行使方面,兩者呈互補態勢,缺一不可。前者是對人性積極面的誘導;后者是對人性消極面的遏制。正如有學者論述的那樣,道德和法律有著不同的作用機理和功能,它們在一定程度上互為優缺點。法律是一種外在性的規范,道德是一種已被內化的規范;法律更多的是抑制人的非理性,而道德則更多的是激發人的理性;法律依靠強制命令運作,道德則依靠內心服從運作;法律的實施存在著被抗拒的可能,而道德則會主動被遵從;法律預期目標的實現是以高額監督成本和執行成本為代價的,而道德對秩序和效率的貢獻是無代價的[22]。也許我們的確無法找到具有高尚道德和高度智慧的智者和賢人來行使國家干預權,但我們必須通過人來實施這種干預。也許“徒善”的確“不足以為政”,但“徒法”更是“不足以自行”。也許道德有引發“人治”的危險,但在法治基礎之上加強干預者職業道德建設的重要性和正當性同樣是一個不言自明、無需論證的常識。
不僅如此,道德在促使干預者充分發揮自主性和能動性,克服干預者因求“群”而產生的被動和保守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只有在道德實踐中,才會反映出人的自主性,或者說,道德實踐是以人的自主性為前提的”[23]。現代政治企圖構建的國家治理和國家干預機制,是一種被動的、機械的、強調過程驅動而不是結果驅動、以控制為導向、注重工具合理性、遵循普遍規則的運用為核心要旨的治理和干預機制,它以嚴格的規范、嚴密的組織、精湛的技術為基本特征。然而,一如上文所述,市場失靈的不確定性、偶發性和階段性,決定了干預行為必須具有回應性、能動性和靈活性等特征,但是這種“高度工具理性化的官僚制政府呈現的是墨守陳規、僵化刻板的景象,使有使命感的政府部門和公務人員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倫理困境”[17]1351。因此,筆者認為,只有在干預中注入道德元素,才能克服干預者在應對市場缺陷時能動性匱乏、回應性不足、自主性缺失的問題,也才能防止國家干預權因僵化而造成的另一種“異化”。
(二)法律制度的規范和約束
筆者認為,法律制度對于國家干預經濟中政府失靈的意義,在于通過運用某些預防性或懲罰性措施,來約束和遏制干預者人性中的消極面,避免干預中的任意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
在認清了計劃經濟時代全能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全面干預導致的弊病后,收縮政府權力、實施“有限干預”,應成為當下中國的主導話語。但在國家干預權“大”“小”的問題上,筆者更認同這樣一種觀點:“現代社會要求現代國家既非全知全能,也不是簡單的國退民進,而是國家的改造,是在重新界定和調整國家、市場、社會關系的基礎上完成的現代國家的構建。”[24]在筆者看來,市場經濟良性運行離不開政府的理性干預,而干預的多少并不是區分“良與不良”的關鍵。將有效干預制度化,才是我們對國家干預的期待。同時,通過制度的約束,有效克服干預者人性中的消極面,又是干預制度構建的核心和關鍵之所在。具體的實現路徑,應包括以下幾方面:
第一,建立科學、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法律規范可以從源頭上控制干預者人性中的消極面。法律是所有正式制度中的核心組成部分,法律的權威性決定了在對國家干預的正當性和規范性的追求中,必須加強對法律的依憑和仰賴。立法是規范干預行為的首要環節,也是法治化運行的前提和起點。因此,制定科學和完備的法律,通過立法和法律解釋,努力尋求有關國家干預的法律與市場需要的契合點,應是立法者的一貫追求。筆者認為,當下有關國家干預的立法完善,應從限定干預邊界、優化干預措施、提升干預效率、建構干預組織、配置干預權力等方面進行。
第二,強化對干預的程序控制和監督。法定化的程序控制和有效的監督能彌補政府中的制度缺陷和人性弱點,是提高干預的效率和準確性的重要手段。筆者認為,建立對干預權的程序控制制度,應從公眾參與政府決策制度、目標實施過程中的方式限制、步驟的確認制度以及干預績效的評價制度等方面進行。同時,監督也是解決干預權越位、錯位和缺位的重要措施。當下構建國家干預行為的監督制度,應從監督權行使的主體范圍的法律認定、行使方式、行使動力、行使激勵以及監督權行使的可近性、可及性、方便性等方面進行。
第三,建立合理的懲罰機制。要加大對干預者人性消極面的震懾和懲罰力度,應完善因干預權的不當行使造成損害的民事救濟程序機制、國家賠償機制、對干預權的合法性審查機制、責任追究機制以及相應的糾錯機制。
參考文獻:
[1] 休謨.人性論[M].關文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6-7.
[2] 何中華.“人性”與“哲學”:一種可能的闡釋[J].文史哲,2000,(1):5.
[3] 胡光志.通向人性的復興與和諧之路——民法與經濟法本質的另一種解讀[J].現代法學,2007,(2):10.
[4] 桑本謙.私人之間的監控與懲罰——一個經濟學的進路[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14
[5] 胡光志.經濟法的人性基礎[J].政法論壇,2007,(3):121.
[6] 汪波.政治學基本人性假設的再探討——論“政治理性人”的基本邏輯[J].浙江社會科學,2007,(6):55.
[7]賈海濤.論霍布斯的權力哲學及其歷史影響[J].哲學研究,2007,(10):65.
[8] 呂雅范.論中國近代政黨產生的基礎[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3):23.
[9] 漢密爾頓,等.聯邦黨人文集[M]. 程逢如,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46.
[10] 戴維?奧斯本.改革政府:企業家精神如何改革著公營部門[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19.
[11] 陳云良.轉軌經濟法學:西方范式與中國現實之抉擇[J].現代法學,2006,(3):176.
[12] 楊充.非理性政府行為與銀行業風險研究[D].成都:西南財經大學,2006: 25.
[13] 佚名.錯誤政績面面觀[EB/OL].(2004-03-06).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3/06/content_1348274.htm.
[14] 朱崇實,賀紹奇.“市場失效”與“政府失效”:經濟法與行政法生存的依據[C]//李昌麒.中國經濟法治的反思與前瞻,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81-82.
[15] 陳奇,星羅峰.“經濟人”和“道德人”并重:行政監督中的人性理論[J].政治與法律,2004,(1):42-43.
[16] 過勇,胡鞍鋼.行政壟斷、尋租與腐敗——轉型經濟的腐敗機理分析[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3,(2):64.
[17]龔會蓮論官僚制度政府倫理困境的突破及我國的經驗[C]// 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研討會暨中國行政管理學會論文集,2006:1350
[18] 克里斯托弗?胡德.國家的藝術[M].彭勃,邵春霞,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9.
[19] 劉澎.論司法之謙抑品格[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7,(4):72.
[20] 佚名.社會轉型時期道德作用的變遷[EB/OL][2008-09-25] http://www.lunwennet.com/thesis/2007/13640.html.
[21]殷嘯虎憲政中的人性預設與制度安排:“以德治國”的憲政分析[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01,(3):91
[22] 應飛虎.需要國家干預說:一種經濟法的認知模式[J].中國法學,2001,(2):137.
[23] 張康之.行政人員的道德自主性及其合作治理[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06,(8):21.
[24] 梁治平.國家、市場、社會:當代中國的法律與發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7.
Unscrambling and Controlling of Government Failure in State Intervention in Economy
HU Guang-zhi,JIN Wen-hui
(School of Law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China)Abstract:
Pondering and analyzing the cause of “government failure” has been an ever lasting task of the scholars in economic law an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ies has become the pillar in establishing economic law theories. However, it is the characters of qiang, quan and le in humanity that are the real reasons that lead to “government failure”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To interpret “government failure” from the angle of the humanity of the interferers, one can readily build up a dependable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and have correct direction and efficient way to study and solve the issues concerning government failure.
Key Words: state interference; government failure; humanity; control
本文責任編輯:盧代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