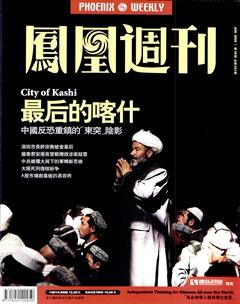利益攸關者應有更大的表達權
鄢烈山
6月5日下午發生的重慶市武隆縣鐵礦鄉雞尾山山體崩塌災害,牽動了舉國民眾的心。當地的救援仍在緊張進行中。但是,天地不仁,沒誰敢擔保下一個小時不會出現類似的環境災難;何況,這樣的山體崩塌并非天災,可以初步肯定是貪婪的礦老板“過度開采”引發的人禍。
有報道說,“至少三次機會可避免悲劇,政府曾兩度要求搬遷,但仍未完全避免險情”。2000年左右由于開采地出現危崖、地陷等情況,當地政府曾發出停產通知書,但停產持續時間不過一年便恢復。“如果2005年發生坍塌的時候就把礦停了,這次也不會出現這個慘劇。”這種狀態的出現,有礦主的責任,有政府監管不力的責任,也有不愿搬遷或遷了又回來的村民留戀故園、心存僥幸的緣故。
然而,當危險迫在眉睫時,為什么錯過了避免災難的“第三次機會”呢?幾乎所有接受采訪的村民都回憶,今年特別是農歷五月初一以來,礦井附近已經發生過多次碎石進裂掉落的情況……幾乎每天晚上都會掉石頭,越掉越多”,“在事發前兩天和事發當天上午,石頭棹落的情況已經非常危急”。“村民說,他們就這些問題向政府反映過,但一直沒有得到重視。”一直到悲劇終于發生了!當地政府的責任不用我提,村民們自己為什么這么被動呢?在生死存亡的大問題上為什么不能督促政府部門斷然采取措施呢?除了心存僥幸,我認為還有重要的一條就是:他們養成了依賴政府盼陛格,不知道如何監督政府,如何主動地維權。其實,僅礦山占用和破壞土地,濫砍樹木,污染空氣,對他們世代居住的家園的無情摧殘,村民就該出面維護自身權益的,至少可以要求礦主或政府給予合理的環境權益補償。
雖然不排除當地有官員被礦主收買的腐敗可能,但官員個人不腐敗又如何呢?據5月26日新華社電,為了關停轄區內的兩家污染企業,江蘇省儀征市環保局黨組書記侯宜中向上級舉報,奔走呼吁4年多,報送調研材料累計數十萬字。他不僅個人通過信訪向各級環保機關反映問題,而且組織了203人聯名舉報,簽名者包括“他的前任,原局長、黨組書記趙有寬,前前任,原局長、黨組書記夏永根,以及財政局、衛生局前任局長等”。那又怎么樣呢?據新京報6月7日追蹤報道,至今“已舉報9次,收效甚微”。因為兩家污染企業揚州農藥集團的優士化學、瑞祥化工是上市公司,是上級政府揚州市的納稅大戶。
顯然有無權錢勾結的個體腐敗不是這類環境問題的癥結。盡管可以說是更高層面的權錢(官商)勾結,但有關領導者個人沒有揣腰包,就可以理直氣壯地繼續生產,不到暴發太湖藍藻、吉林化纖廠千人“心因性集體中毒”那樣的大事件,就不會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和高層重視。
不難看出,這里缺乏環境權益攸關者有力的集體維權行動。試想,儀征的侯宜中們如果與當地群眾一起上訪,估計就不會迄今“感慨‘拳頭遇上棉花”了。集體維權之所以缺乏,我分析主要有三條原因:一是不少國人信奉“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著”,只愿“搭便車”,或者忍慣了,像作家高曉聲筆下的的農民陳奐生想的是“只要不是欺負我一個人,就不算欺負我”。二是多年的教育使他們不待見維權者。上月我在廈門市,聽朋友談為PX工程“散步”的事件,他頗為不屑地說,那些人就是工程選址處的居民和房地產開發商,他們怕他們的房子因有污染和危險而不值錢了唄。可見他并不認為,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表達訴求,雖然不“高尚”卻是天經地義的!還存一點就是,人們(包括官員與群眾)對于集體性的表達心懷忌憚。其實,憲法確認了公民有游行、示威、請愿等表達自由。公民合法運用這些權利的國家和地區也未見天下大亂。相反,將這些合法的表達渠道棄權不用,到了利益受損者琶無可忍時,就會發生堵企業的大門、斷路,企業員工與居民打群架,乃至沖擊政府機關的群體泄憤事件。這樣的案例并不少。
《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有一節是專門講“環境權利”的。其中講到創造有益于人類生存和持續發展的環境,落實《國家環境與健康行動計劃(2007-2015)》,強化環境法治,維護公眾環境權益,深入開展整治違法排污企業,防范環境風險,拓寬和暢通群眾舉報投訴渠道,等等。同時,在“監督權”這一節講到“加強人民群眾對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等的監督”。
我深信,普通民眾對如何防范全球氣候變化造成的災難可能不敏感,甚至對亂扔垃圾一類也視而不見,但對于嚴重危害其生命和生活安全的環境危害,他們肯定有相當的關切和愿望,希望維護自己合法權益。因此,應該讓他們實際擁有足夠的表達權,以反制那些不以人為本的基層政府權力和資本貧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