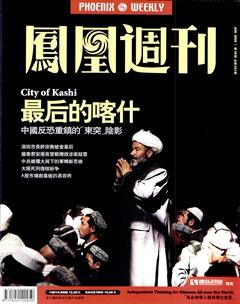“鄧玉嬌”背后的法治走向之爭
沈彬
上個月一則法治新聞,打開了潘多拉的麾盒:5月10日,湖北巴東縣某鎮政府3名工作人員,在休閑中心被女服務員鄧玉嬌刺成一死一傷。死者的“官家”身份,加上弱女子以刀捍衛貞潔,引爆了網絡輿論。事件情節波瀾起伏:鄧玉嬌被送進精神病院,律師當眾痛哭,鄧母更聘官方背景的律師……直到近日檢察院審查起訴。案情發展的每個節點,都引發了草根與官方話語的“白刃戰”。本案已不是一起單純的刑事案件,而成了中國法治的橫截面。加上幾位專業法學家披掛上陣,形成涇渭分明的陣營,背后是中國司法專業化Vs,司法民主化,全民法官Vs,精英法治,是對中國法治之路的話語權爭奪。
專業判斷和民眾的正義直覺
案件本身并不復雜。即便按律師控訴書里的說法、3位官人中的一位黃德志企圖在浴室里“強奸”鄧玉嬌,后鄧逃至外間,當著多人的面,死者鄧貴大用錢扇打她,羞辱她,并兩次“摁倒”她,鄧不堪羞辱拔刀自衛。
對相同事實的定性,草根民眾的判斷和專業司法截然相反。從民眾的正義直覺看,民女有捍衛自己貞操的絕對權利,特別是面對官家淫威時,她被冠以俠女、貞女等名號——無數人對現實的無奈,轉化成激情投射在這個女孩子身上。
鄧玉嬌也契合中國傳統的文學想象——民女反抗胥吏欺凌的經典題材,比如膾炙人口的詩篇《羽林郎》、《陌上桑》。這種文學想象中的“合法性”,和現代法治有著話語權上的緊張。
現代法治社會不是宗法社會,并沒有把“貞潔”放在與人身安全同等重要位置,即只有針對危害人身安全的侵害,才有無限防衛權。雖然億萬中國人認可保衛名節有充分的理由殺人,但這并不為中國現行的刑法所接受。這是現代法治理念和億萬人認可的傳統沖撞。
《刑法》規定:“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于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學理上對此有著不同理解——“無限防衛權”是針對“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強奸,還是只要是強奸都適用?但司法實踐中一般傾向前者,即“無限防衛權”應與犯罪危害性相匹配。本案中,死者的污辱行為很難說構成強奸,也不能說“嚴重危及人身安全”。在現代法治的語境下,鄧無疑是防衛過當,構成犯罪。這幾乎是司法專業判斷的共識。
貌似強大的民意,如果脫離了專業的知識支持,很容易被“愚弄”。此案輿論沸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鄧玉嬌竟以“故意殺人罪”被立案,輿情無法接受。后警方確認鄧玉嬌“防衛過當”,不少人欣喜若狂,以為警方糾正了“故意殺人”冤案。事實上,“防衛過當”并不是一個獨立罪名,只是犯罪構成的一個方面;按刑法理論,防衛過當即構成故意犯罪,而不是過失犯罪,即鄧只能定故意殺人罪或故意傷害罪。從她連刺4刀,其中兩刀致命的角度看,依司法實踐她還是會定“故意殺人罪”,也就是說警方根本沒有改變本案定性!由是反推,若當初警方在通報中回避“故意殺人”罪名,代之以“防衛過當”,就可避免觸發輿論的地雷。
又如在此前的杭州飆車案中,激憤者主張以“過失殺人罪”追責,以為那是一個嚴重得多的罪名。事實是,在小區里發生的交通事故,就是按“過失致人死亡罪”論罪的,它的刑罰并不比交通肇事更嚴重。政府如果掌握“公關技巧”,就很容易“疏導”、操縱民意。
“全民陪審團”能帶來正義嗎?
基于上述話語緊張,以及現實法治讓普通百姓的失望,從許霆案以來,輿論空間中有著一種天真、固執、集體無意識的預設——現行司法體系是靠不住的,法律專業人士早已投靠既得利益集團,出賣良心,只有“全民陪審團”代表人民執行公正。甚至有人直言:如果一個法律跟中國大多數人的意見相左,那就是一個錯誤的判決。
這是把陪審團想象成了全民公決,錯誤地把“民主訴求”強加到司法頭上,是民主饑渴癥和對現實司法失望下的“司法民主臆癥”。世界上審案子沒有靠全民公決的!事實上,執此主張者也未把自己定位在法官的客觀第三方立場,而是沉浸在“受害者角色扮演”中,動輒對別人發出“如果受害的是你的親人,你會怎么樣?”的道德責難,已經偏離起碼的“自己不做自己法官”的程序公正。
即使英美式的陪審團制度,也不可能是某些中國人想象的“多數人的正義”,更不是“群眾公審大會”。在法官的專業主持下,對控辯雙方的舉證、質證,代表一般人的普通理性作出判斷。美國著名的辛普森案件,陪審團的意見就跟最廣大人民的意見相反。“陪審團”代表民意一說,只是中國人從此岸現實需要出發對彼岸的幻想。
在中國民主化還是一個漫長議題的背景下提“司法民主化”本身就是一種奢侈,乃至破壞。中國法治之路一直在震蕩,在前任肖揚法官任期內,強調了司法專業化,但最近最高法提出“三個至上”,把人民滿意和遵守法律提到相同的“至上”位置,可看作是法治改革面對合法性危機,尋求民意資源。
沒有政治民主作為前提的這種所謂“司法民主”,只會破壞近年來中國法治專業化的積累,讓民意浪費在個案的自相矛盾的干涉當中。任何人在未被依法判決之前都是“無罪的”,但在判決前之所以要把一些嫌犯“抓起萊”,目的不是對其預先處罰,而是嫌犯可能繼續為非作歹,銷毀證據,乃至遠走天涯,所以刑拘的目的是為了保障司法程序的順利進行。若嫌犯不存在阻礙司法程序的可能,就沒有必要抓人,而是可采取取保候審。這個人道的法治理念,很多人是接受的。比如云南省“躲貓貓”案件中,農民李喬明因為盜伐林木被刑拘,蹊蹺地死在看守所里。當時有論者指出:依現代法治精神,此嫌犯完全沒存必要刑拘。但在杭州飆車案中,在事故當天責任尚未查明,是否涉及刑事犯罪都沒有弄清的情況下依法并不能對肇事者刑拘,而這種合法行為卻成了杭州警方的罪狀。大家似乎忘了“無罪推定”,沉浸在對“富二代”的階級仇恨當中了。
兩大法學派斗法
鄧玉嬌案論戰的最精彩之處在于,幾位法學教授同室操戈,體現了走何種法治之路的學理沖突。論戰中引起公憤的“反面人物”,是西南政法大學的高一飛。他撰文指責鄧玉嬌的律師有違職業道德,企圖利用輿論干涉司法,并援引了美國這種法治較成熟國家關于司法和輿論的規定。
中國政法大學蕭翰副教授指責高一飛作為法律人士喪失對“弱女子安危”的關心,“討好官方、助紂為虐”。并指出,當代中國的法律體系,受階級斗爭意識形態的影響,大量條文是基于敵我思路,而不是基于保障公民權;中國的法律學者弄不懂這個,就是“不懂法的精神”。
很自然,高一飛被民眾唾罵,蕭翰受到民眾推捧。如果說高一飛教授還有要求律師協會處分鄧玉嬌原律師的“告密者”之“道德污點”的話,那么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喬新生,僅從法律角度談鄧玉嬌的行為構成防衛過當,即遭到無數人的謾罵,這說明了什么?
其實,以上幾位都受過專門的刑法教育,不可能不知道:在現行法律下,鄧的確構成犯罪;同時雙方也非常清楚,這個專業判斷民眾絕不會滿意,而且民眾憤怒并不是針對此案,而是長期受到公權侵害積累下來的,這只是一個發泄渠道。如果可以安一個帽子的話,那蕭翰就是代表“自然法學派”,要求“超越法律”,按實質正義、自然法的原則判定鄧無罪,而不是依照“惡法”:而高一飛則代表實證主義法學,即便個案中有種種不公,也必須按既定法制運行,而不是為了迎合大眾,推倒重來,更不應歌頌“以暴治暴”,否則“中國就得成為水泊梁山”。前者的思想是民粹的,后者是精英的:前者是激進的,后者是保守的。這兩種思想的對立,并不能“政治站隊”分為反政府、投靠政府,在狂飆激進的時代,社會不僅需要踩油門的人,更需要踩剎車的人。從對中國歷史的考察看,中國現在似乎更缺少踩剎車的保守力量。
貴州甕安事件、林嘉祥猥褻門、躲貓貓事件、杭州飆車案、鄧玉嬌案……這些大規模全民參與的個案監督,促使政府認真傾聽民意,進一步試探了輿論的底線,已形成一種中國政治的新生態——個案公眾監督,這將是中國民主進步,公眾輿論空間形成的平臺。但司法作為一種保守力量,還是應保守既有的穩定和可預測性,不能在個案中聽憑民意干涉。否則、未來就不得不不斷向輿論低頭,不斷走法治的回頭路。中國百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