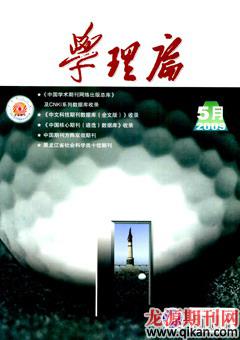地域文化觀照下的陜西當代文學創作
王小剛
摘要:文學具有地域色彩,早在南朝梁時期,劉勰就在其思想巨著《文心雕龍》中反映出這樣的思想來。《文心雕龍》稱北方早出的《詩經》為“辭約而旨豐”,“事信而不誕”,是質樸的“訓深稽古”之作;稱南方后起的《楚辭》則為“瑰詭而慧巧”,“耀艷而深化”,并將此“奇文郁起”的原因歸于“楚人之多才”,多少接觸到地域與文學的關系。在當代文學創作中,陜西作家群的作品明顯地表現出三秦文化的影響。本文將著重從陳忠實入手,以他的《白鹿原》為文本,簡要探討三秦對他的文學創作的影響。
關鍵詞:地域文化;陳忠實;秦地小說
中圖分類號:I207.425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09)11—0139—02
《白鹿原》這部扛鼎之作以它那“囊括宇宙,貫通古今”的敘事藝術為我們展現了渭河平原50年變遷的雄奇史詩,將白鹿原的風土人情、民俗文化推向了世界。陳忠實并沒有刻意求新去追求小說創作主題范式,而是理所當然地繼續秦地小說家大力推崇的文化主題,盡情地闡釋著自己對關中文化的理解,為我們呈現了一部瑰麗的民族史詩畫卷。
一、創業主題
在人類的歷史進程中,如何生存一直是考慮的首要問題。秦人把這個問題和創業放在了一起去考慮。處于農業文明的關中平原,眾生的創業自然離不開農業的首要生產資料—土地。《白鹿原》中,白嘉軒從創業起初到成為白鹿原屈指可數的大家族,都一直對土地有著獨特的情感。就是在和鹿子霖的爭斗中也時常是為了土地。可見土地在農業社會中是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的。為了得到那塊長著鹿樣樣奇草的慢坡地,他對鹿家機關算盡;為了把父親的墳遷到那塊他認為蘊藏著白鹿精魂的地里去,他謊說自己做了夢,夢中的父親鬼魂告訴他棺里進了水;為了李家寡婦的那六分好地,他和鹿子霖鬧得沸沸揚揚…等等都是很好的憑證。在創業的社會關系方面,白鹿原完全采用的是農業社會所特有的家族式結構。“對于白嘉軒來說,他最重要的關系在于家庭。他首要的觀念是家庭觀念。他的進取就是家庭的進取,他的哀樂就是家庭的興衰,他的人生完全融化在家庭里了。離開家庭作為小說人物他則不復存在。”[1]作為創業的主體—人來說,對其性格特征,我們可以引用吳宓先生對陜西楞娃的解釋:憨厚,耿直,倔強…但我們也可以從作品中發現關中人特有的一種狡黠。白嘉軒是一個追求仁義的“正面人物”。他一生居仁思義,心懷大志,為家庭和鄉人殫精竭慮奔波不息。作為一個農人,他敬恭桑梓、服田力穡,用血汗一步步建立了自己的家業;作為族長,他博施公濟,逐漸樹立起了在鄉民們的威望。他一生的奮斗目標是:治好家業,振興家族,同時使白鹿原的鄉人們家家溫暖,個個仁義。其實,他一生中的每一次仁義之舉幾乎都是出于立身揚名的功利目的。就像修祠堂時的愿望一樣,他“想出面把蒼老的祠堂徹底翻修一新,然后在這創辦起本村的學堂來,而他的名字將與祠堂和學堂一樣不朽”。就創業的進程和結果來說,農業社會以兼并土地為手段的創業,在起初,創業者往往是要付出大量艱辛的體力勞動的,等到自己的土地達到一定程度時,土地所有者就可以不用自己勞動而獲得大量的收入。然而,由于種種原因的限制,農業社會中的地主,并不是每個人都會擁有大量土地。許多所謂的“地主”只是十幾畝甚至幾十畝地的“主”。白嘉軒在今人的眼中也只不過是一個多承包了幾畝地的“專職農民”而已。
如果說上述在中國的農業生產中具有普遍性的話,那么在秦人的創業中,我們更應該看到主客觀方面的限制,這兩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很強的地域性。客觀方面:惡劣的自然環境的影響;主觀方面:守成有余,開拓不足的自然經濟觀念的制約。因此,對世代的秦人創業者來說,“苦”一直是伴隨他們創業左右的。在秦地小說中,秦地小說家們對苦難的人生進行了集中的關注,使他們既不淡化對天災人禍的冷峻審視,又不忽視對苦難降臨時人的堅忍所凝聚的精神品格的稱揚。我想這一點應該是作為農業文明中的關中平原和他者地域農業文明的區別。秦地作家對這一點的關注,也應該是作為區別于他者的地域特色。
二、性·情主題
“臨近世紀末的秦地文學似乎給廣大讀者留下了這樣的印象:那伙老陜老土,特別愛寫男男女女的事,寫得有滋有味,寫得驚世駭俗,寫得不倫不類,寫得別有用心,寫得讓人感動又讓人反感,寫得令人厭惡又忍不住看…”[2]秦地小說家對形形色色的性戀與愛情的描寫,與作家的生命體驗生活積累和觀念意識有關。探討秦地性文化,有三個層面值得注意。“一是原始的本能層面。秦地小說突破了種種認為禁錮,尤其是在壓抑人們甚久的律條崩潰之后,秦地作家更真切地看到了生命的本相:貧瘠的土地上強化著更為旺盛的生殖文化—生命基因復制成了一種集體無意識的頑強沖動。《白鹿原》開篇便切入這一性文化的層面,寫白嘉軒為了生殖目的而頑強地、豪壯地連娶了七個老婆,終于達到了生殖的目的。這種描寫極富文化人類學的意味:他很古老,也很時髦…二是性的審美化層面。在20世紀的秦地,文化娛樂的條件仍普遍匱乏,尤其像陜北的窮鄉僻壤,‘在沒有點電燈,沒有電視,沒有收音機的夜晚,在這閉塞的一村一戶被遠遠隔開的荒山上,夫妻間的溫柔,成了他們夜晚主要的文化活動。(《最后一個匈奴》)在這種情形下,性愛活動涉入精神需求領域,既是一種‘體育活動,又是一種‘美育活動…三是性的社會化層面。在人們熟知的描寫性愛的文學教訓中,總強調怒能為寫性愛而寫性愛,要在性愛的描寫中去觀照社會人生。這是將性愛置入社會人生的大系統中去考察勢必會引出的結論。的確,性、性愛及性描寫與社會人生莫不有著十分親密的關系…”。[3]《白鹿原》中,陳忠實反映了在宗族社會中,關中平原人們的性·情觀。他所反映的性·情觀極相似第三點。在陳忠實所營造的《白鹿原》的世界里,女性是作為男權社會的“他者”出現的,她們也不應該有自我存在的意識與權利,否則便萬劫不復。“30位女性中明確提到死去的有14位,約占50%。‘死籠罩了白鹿原的上空,這些人的死是必然的”,“越是遵循這種害人的制度越可長壽,越是和宗法制度相敵對越是短命。女性在封建宗法制度面前沒有任何價值,愛情、事業、人生的追求都如同一張白紙”。[4]這是典型的男性文學主流敘事對女性形象的書寫,其歌頌和贊美的筆調遮蓋了事實的殘忍。“客觀地講,女人作為配角在白鹿原上生活的”,“男人成為中流砥柱,而女人如同男人的附屬品”。[5]在以男性為尊的時代和社會里,女性完全被籠罩在男權的陰影之下,男權的中心統治地位無情地對女性從肉體到靈魂構成雙重壓迫和摧殘,女性的命運是悲慘的。即使書中把握了自己命運的惟一女性白靈,她的死亡,仍暗合了傳統儒家信徒的人生觀,逃不出白嘉軒們的預料,逃不出封建道德欺詐的目光,男權社會對女性的蔑視顯而易見。這是一個彰顯男性優勢的社會,顯示了傳統倫理道德對于男性的絕對寬容和對于女性的絕對嚴苛。女性僅僅作為傳宗接代和男人成家立業的工具而存在,女人沒有獨立的地位,用白趙氏的話說,“女人不過是糊窗戶的紙,破了爛了揭掉了再糊一層新的”。固然,造成女性悲劇命運的原因是當時社會與文化雙重壓迫的結果,陳忠實也以歷史真實的筆調再現了女性的“生”之艱難,然而作品中女性悲劇命運的描寫卻透露出陳忠實的文本抒寫,依然是典型的男性文學主流敘事對女性形象的書寫。“白鹿原是一個典型的男權社會,在這個以男性為尊的社會里,女性的世界黯然失色。”[6]在《白鹿原》中最值得我們關注的女性非小娥莫屬。在白鹿原的人看來,小娥就是禍水,更重要的是她失去了女人所應有的貞潔。在中國傳統的倫理文化觀念中,貞潔是衡量女性的一把標尺。以男權為中心的關中文化,自然而然地遵循著這一標準。但是我們要問,是誰讓她成為萬人唾罵的“婊子”呢?她自由地追求屬于自己的幸福難道有錯嗎?也許在貞潔這一點上我們不應刻意地去責備古人。但是對女性進行戕害的貞潔觀我們則要責問:所有的不貞潔還不是由那些操縱話語權的男性所造就的嗎?明顯的是:在關中貞潔婦道是對女性人性的一種戕害。
結語
文學作品是作家對特定時期特定環境下特定人生的理解與表現。陳忠實對傳統文化有著獨特的感悟和更為自覺的文化意識。陳忠實立足于農耕文明,并對在此之上形成的中原文化尤其是關中文化進行著反思。深刻地剖析了關中傳統在時代變遷下所面臨的尷尬處境。關中文化的接受者和傳播者們也經受著時代的磨練。恰似陳忠實一樣,在對自己故土那種迷戀的感情之外,更有一種對傳統文化衰落的失落和擔憂。但同時,他仍舊詮釋和解構那種深入骨髓的文化傳統并把它盡意地展現出來。地域文化構成了陳忠實的整個創作世界,也只有在這種地域環境的影響下,他們的作品才具思想性。地域文化影響了作家,作家同樣接受和傳播著地域文化。
參考文獻:
[1]鄭萬鵬.《白鹿原》與家族文化[J].東疆學刊,1997,(1).
[2][3]李繼凱.秦地小說與秦地文化[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4]孫艷平.從筆下流出的眼淚[J].太原教育學院學報,2001,(3).
[5]龍葉.《白鹿原》中幾位女性人物之我見[J].渭南師范學院學報,2003,(2).
[6]張愛榮.黯然失色的女性世界[J].云南經貿大學學報,2002,(3).
(責任編輯/彭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