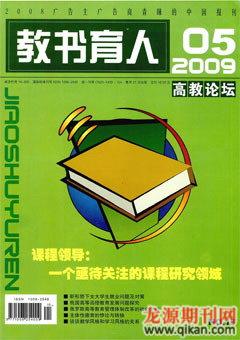走出去,女人想要什么?
王 卓
“女性解放”作為一種特殊的解放運動,首先要解除的就是性的束縛,這是女性尋求自由發展的基礎,而真正的自由發展恰恰是以人格獨立作為保障的,人格的自由與發展才是女性解放的價值所在。19世紀末托爾斯泰、易卜生借助他們筆下的安娜、娜拉為女人呼喊出心中的渴望,讓更多的人開始關注女人的世界。
一、簡析安娜、娜拉的藝術形象
1安娜
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創作于19世紀70年代,主人公安娜出身于一個貴族家庭,從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7歲時,姑母做主把她嫁給了大她20歲的省長卡列寧。這時的安娜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愛情,只是盡著別人告訴她的應盡的妻子職責,維持著夫妻名分。表面上看這個家庭是彼得堡上流社會的楷模,實際上卡列寧壓抑著她身上一切有生氣的東西。安娜履行了教育兒子、愛護丈夫、參加必要的家庭社交的義務,但是從來沒有享受過一個妻子應該得到的愛與溫馨。在這個表面上高貴體面的家庭里,安娜長期忍受著無愛的苦痛和精神上的壓抑。在這種無愛婚姻中,女性只是以男人的物件身份生存于世,不具有和男性一樣的自由、平等。
不甘心永遠被這種無愛婚姻束縛的安娜,走出了家庭,也與此同時她舍棄了自己的家庭、自己在上流社會的地位、自己的人格尊嚴。然而,與安娜毫無保留地付出不同的是,渥倫斯基對待安娜的態度卻沒有那么堅決。他對安娜是有所保留的,他可以忍受與社會一時的對立,但為了自身的利益絕對不可能維持長久。因而,當上流社會讓他在地位和安娜之間選擇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自己的名譽。安娜搏盡人生所有換來的愛情竟成了取她性命的“劊子手”。她企圖用生命的代價來懲罰渥倫斯基,但實際上,她懲罰的只有她自己。
2娜拉
娜拉是易卜生劇作《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愛他的丈夫,她婚后的最大目標就是想盡辦法讓丈夫和孩子們高興。她心里一直希望有一天自己身陷險境,丈夫能夠奮不顧身地把自己從險境中救出,這樣就可以完美地證明他們之間的愛是完美的了。然而,先接受這樣挑戰的竟是她自己,為了把丈夫從病魔中救出來,她毫不考慮自己會承受什么樣的法律制裁而冒名簽字。丈夫病好之后,這件事也被別人發現,這也恰恰到了娜拉認為丈夫該不顧一切救贖自己的時候了,結果海爾茂首先想到的卻是他自己的危險。他認為娜拉給他惹了大禍,毀壞了他的名譽。他罵娜拉是“偽君子”,是“撒謊的人”,是“下賤的女人”,甚至剝奪了娜拉對三個孩子教育的權利。但當危險過去,身份和名譽保住的時候,他又開始親昵地稱呼娜拉“小鳥兒”“小寶貝”。
海爾茂為自己所作的事情辯解道:“男人不能為他所愛的女人犧牲自己的名譽。”正是這一瞬間,娜拉忽然醒悟:在丈夫的心中,重要的不是自己、不是家庭,而是名譽、地位、金錢,表面上所看到的愛情,在一切考驗之下都那么的不堪一擊。他們的這個家庭只能存在于風平浪靜的時候,一旦有了波瀾,無論大小都將變得不再完整。所以,娜拉覺得這樣的家庭讓人覺得可怕,當她的丈夫提出婦女最神圣的責任是對于丈夫、孩子的責任時,娜拉堅決地回答說:她還有一個責任,就是對自己的責任。按照娜拉的說法,如果一個女人都不對自己負責任的話,就不會有人愿意為其負責任。她不甘心永遠成為丈夫的玩偶,過沒有自我的生活,她毅然走出了家。
覺醒了的娜拉立志要做一個獨立的女人,開始闖蕩一條新的人生之路。不再人云亦云,對一切事情“都要用自己的腦子想一想”。其實在那個年代里,大家并不知道娜拉的結局到底會是怎樣。但作品的意義在于通過娜拉的出走,“否定了那種籠罩著一層溫情的資產階級家庭,因為那種家庭溫情、家庭幸福,是婦女在她那個小天地里,為之甘心犧牲自己的獨立的人格作為代價的”。
二、走出去。女人到底想要什么
安娜走出了家庭,她想要的是平等的愛情,是有愛的家庭,但她沒有看清楚,在那樣龐大的罪惡面前,她太微不足道,所以,女人抗爭想得到相應的地位的首要條件,是讓自己變得強大,也就是要靠更多個脆弱的個體來組成強大的群體。由個體抗爭,發展到群體抗爭,才能為女人爭取到屬于自己的一切,有愛的婚姻,有愛的家庭。但是,可悲的是,很多女人已經把自己所受的不合理待遇看作理所當然,甚至有些女人很迷惑地問:“我們取得了地位后,要做什么呢?除了做家務,侍候丈夫,我還有什么可以做的呢?”可見自我的不覺醒,也是女性個體解放運動向群體解放運動發展過程中的阻力。
娜拉走出家庭,她說:“首先我是一個人,跟你一樣的一個人——至少我要學做一個人。”1879年《玩偶之家》首演之后,娜拉離家出走的摔門聲驚動了整個歐洲,后來也驚醒了“五四”之后積極探索的中國知識分子,由此成為世界婦女解放的宣言書。女性要擺脫生活中固定地發揮妻子、母親的社交功能,要能夠說出自己的意愿,走到社會中,積極爭取自己的尊嚴,而不是男人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玩偶。女性不再是愛情生活的奴仆,而應該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者。正如舒婷《致橡樹》中所說:“我必須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為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相握在地下;葉,相觸在云里。”娜拉的出走不是為了尋找愛情,而是要尋找作為一個女人的獨立性。她告訴人們,婦女的人格高于婦女所珍惜的愛情。她所否定的已經不是建立在浮華上面的無愛家庭,而是對傳統的夫權思想的否定。
三、走出去,女人為何如此艱難
1根深蒂固的男權思想對女性造成了強大的社會壓力
無論對于安娜、娜拉,還是其他女人來說,走出家庭也許不難,但是,真正想要走出固有的思想的束縛得到自己理想的生活卻十分艱難。把女性視為男人的一部分或男性的點綴品,這種思想在各種文化中一直都存在。例如:《圣經》記載,上帝是從作為男性的亞當身上取下了一條肋骨造成的女人,所以女人只不過是功能性的,從屬于男性的客體,她只擁有軀體、性、生殖的物質特征。而古希臘文化中的觀念認為:女人只是男人種子的消極孵化器。在中國的儒家文化中為女人設計的主要“功用”是生兒育女,傳宗接代。娶妻的目的不是用來組建溫暖的家庭,而是用來生子。班昭在《女誡》中云:“事夫如事天,與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
可見無論是哪一種文化中,女人都不可以享受真正的婚姻生活。羅素說:“無論是文明人的本能還是野蠻人的本能,都不會僅僅滿足于性交。如果要使那種導致性交的沖動得到滿足,就必須有求愛、愛情和伴侶生活。否則,肉體的欲望雖然暫時平息,但精神的欲望卻依然如故。因為它沒能得到深切的滿足。尤其是對女人來說,女人更加渴望在性關系中,沒有壓抑,沒有約束,充滿著愛與關懷,獲得情感和
性的雙重滿足。但這樣想享受到性愛的美好的女人是不被世人所容的。”
2薄弱的經濟根基限制了女性走向社會
馬克思認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陛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只有經濟獨立,才可能不完全依賴男人,也只有這樣才可以擺脫男人的控制,有自己的生活,也只有這樣男人才會真正的把女人當作人來看待,而不是發泄欲望的工具。所以女性應該走出去,參與社會勞動來獲取經濟收入。但實際上第三世界的女性根本不存在拘束在家庭中的煩惱,為了生活她們早就不得不和男性同樣承擔繁重的體力勞動。當我們看到經濟主導一切的時代的時候,不難發現,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為了謀取最大限度的利潤,帝國主義國家往往選擇第三世界國家、地區,而這些國家、地區中,廉價勞動力更成為他們壓榨的對象,這是民族性的,而不單單屬于女性。另外,種族歧視、民族壓迫,使很多男人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法律上處于無權和弱者的地位,更何況于原本就沒有地位的女性。所以,對于第三世界的婦女來說,她們擔負著反對種族、民族壓迫和性別壓迫的雙重任務,她們身體和心靈被剝削更甚。所以,女性真正的解放又伴隨在國家、民族解放、階級解放的過程之中,個體解放伴隨在群體解放之中。
四、結論
多年以來,女性解放論者一直在宣揚“男女平等”的理念。盧賓說:“僅僅強調女性走出家庭,參加社會生產是不夠的,首要問題是解放人類再生產領域的分工,即:男女雙方能夠真正分擔養育兒童,照料家庭,完成家務的工作。”在現代社會中,這樣真正的再分工是很難完整實現的。性別平等說到底是一種價值判斷,而并不意味著女人可以和男人做同樣的事。女性解放重要的是修正性別差異,修正將男性和社會、家庭中的統治、權力中心地位聯系在一起,將女性和服從、邊緣聯系在一起的價值判斷。女性要通過進入社會改變自己的身份、地位,從而改變自己的價值。
隨著女權運動的發展,人們已經逐漸認識到,外部社會條件是可以改變的,但是這種改變還必須和婦女自身的真正覺醒相連。隨著婦女解放的程度的提高,婦女在自身價值的實現過程中,不再困于個人狹窄的天地,而是與男子一樣面對著整個社會生活,這就使得女性的眼光和思維方式從自身內部世界不斷向外拓展,從而使女性的世界成為一個開放的世界。回顧走過的歷程,女性問題從與男性面對現實權力時的斤斤計較、爭來奪去,到更多地對自身人性完善的關注,這是女性發展史上的巨大進步。
現代職業女性比傳統女性承擔的壓力更大,除了要像傳統女性那樣“相夫教子”,還要投身于社會工作之中。所以,時至今日,女性解放的話題還在繼續。存在主義文學家西蒙·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有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希望更多的女人能實現自己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