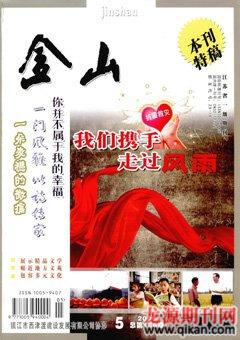文化老人又遭揭底?!黃苗子陷“告密門”
夜子 輯

自從文懷沙事件后,又一位文化老人再度被推上輿論的風(fēng)口浪尖。近日,南方周末刊發(fā)了章詒和(章伯鈞的女兒)的文章《誰把聶紺弩送進(jìn)了監(jiān)獄?》(下簡稱《誰》),指出著名畫家黃苗子正是當(dāng)年的“告密者”。此文一發(fā),馬上在各大媒體與網(wǎng)絡(luò)引發(fā)關(guān)于歷史與道義的爭論。
《誰》的作者指出,她在2009年2月刊紀(jì)實(shí)版《中國作家》雜志上,看到資深政法工作者寓真所寫的《聶紺弩刑事檔案》(下簡稱《聶檔》),該文長達(dá)十萬字,以解密了的檔案材料為憑,系統(tǒng)又完整地揭示出聶紺弩冤案的真相:“長期監(jiān)視、告發(fā)聶紺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寓真將告密者分成兩類,第一類為限于人身自由而被迫告密的,有些則是“積極配合公安機(jī)關(guān)”的。雖然《聶檔》中沒有明確列出讓聶紺弩深陷“言論之罪”、“寫反動詩之罪”的罪魁禍?zhǔn)资钦l,但《誰》的作者卻明確指出他們是王次青、黃苗子等人。而“聶紺弩贈詩較多的是給黃苗子,但送給黃的詩稿,不知為何也都進(jìn)入了司法機(jī)關(guān)。”(《聶檔》文)黃苗子也因此成為《誰》的作者集中火力揭發(fā)的“告密者”。
此文一出,媒體和網(wǎng)絡(luò)一片嘩然。黃苗子,一位近百歲、在中國美術(shù)界德高望重的老人,一下成為眾矢之的,甚至有網(wǎng)站拋出“黃苗子和文懷沙誰更壞”的話題,引發(fā)網(wǎng)友熱議。
“倒黃派”:對黃苗子的“行為”感到失望
“如果這樣的人都能‘變節(jié)、告密,我們的家長、學(xué)校和社會還如何有信心能教育影響以后的一代代年輕人?賣友求榮的人注定被唾棄。”
“關(guān)于近日的黃苗子告密事件,我們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是非分明。不管是誰,不管他多么有名,也不管歷史多么久遠(yuǎn),做了壞事就一定要承擔(dān)責(zé)任。如果我們姑息養(yǎng)奸,那以后人們做了壞事就不會再有顧慮了。那樣發(fā)展下去我們會是一個什么樣的民族?!我們的國家又會變成一個什么樣的國家?!黃老苗子必須站出來回應(yīng)!他也還有機(jī)會,如果沒做那事他可以通過媒體或法院辯誣,如果真做了那他就應(yīng)該公開向聶紺弩的亡靈致歉!除此以外,黃苗子沒有別的選擇!”
“真相究竟如何我不清楚,但是從整個事情里我聞到了一股血腥氣!這使我感到害怕,在那個年代,任何人都不可能獨(dú)善其身。我只想大聲疾呼:做人要厚道!”
“挺黃派”:對《誰》作者提出質(zhì)疑
“作為那個時代‘落難的貴族,她所寫的文章只是滿足了人們對那個時代看似真實(shí)的臆想。她寫的東西都有一個特點(diǎn):死無對證。而且都是道聽途說,不見任何文字資料可以佐證。”
“文革的事情已經(jīng)模糊了,僅從一些文章中的只言片語中判斷或斷定一些事情,跟猜測沒有兩樣,結(jié)論下得有點(diǎn)太肯定了,章詒和在當(dāng)事人和主要見證人都不會說話了時,站出來寫這寫那,目的不會太正!其實(shí)她現(xiàn)在這種情況和告密的行為沒什么兩樣。”
“告密檢舉是當(dāng)時的社會生活常態(tài),雖父子夫妻兄弟概莫能外,人人自危,幾乎人人皆有罪感,皆需自證自保,組織叫你檢舉揭發(fā)某人,那是看得起你,你可能覺得還有點(diǎn)救,絕對會積極的。絕無虛言,情理之中的事。”
“時代的果實(shí),既是苦果,沒必要再回味。誰人背后不說人,誰人背后無人說。何苦只和讀書人過不去?”

旁白:
也有不少專家學(xué)者冷靜地分析該事件背后的意義。北京學(xué)者雨父發(fā)表《黃苗子事件:首先是世道敗了人心》,指出“苗子先生身處那個時代,世道如斯,人心不古,進(jìn)退寧不失據(jù)?我們現(xiàn)在覺得黃苗子先生‘不堪,正表明現(xiàn)在的人心似乎在慢慢變好。”而媒體從業(yè)人于德清的《要不要揭文化老人的歷史傷疤》則指出,從那段歷史的泥濘中走出來的人,更需要直面靈魂的真誠。所有的罪惡和過錯可以得到寬恕,但是,事實(shí)無法回避,對歷史采取鴕鳥政策,是肯定不行的。這不是又一場無限上綱上線的道德審判,而是一場遲來的真相還原,是真正地負(fù)責(zé)任地面對歷史。“這對后來的告密者以及未來的告密者都足以是一種警示。”
目前,黃苗子方面沒有就此事做出任何回應(yīng)。
質(zhì)疑
有人找來了寓真的《聶紺弩刑事檔案》,那是章詒和拿來“說事”的憑據(jù),他細(xì)讀之下,疑竇從生。
質(zhì)疑一,寓真的《聶紺弩刑事檔案》無疑是一篇很好的報(bào)告文學(xué)作品,能讀出作者對聶紺弩先生深深的同情和尊重,很平和,很客觀。但這里面實(shí)在找不到關(guān)于黃苗子是告密者的論述。
質(zhì)疑二,章詒和在文章中大量引用的1962年9月12日有人遞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顯然不是黃苗子的手筆。章詒和在行文中卻交待得極為模糊,使一般讀者幾乎看不明白這封密告材料的真實(shí)作者。《聶紺弩刑事檔案》中有這么一句:“王次青寫的檢舉材料,主要是關(guān)于聶的言論。”章文雖然也引用了這句話,但文章開頭的處理,卻容易給人一種先入為主的印象,目前有不少讀者已經(jīng)把這封信的作者安在了黃苗子的名下,甚至就把黃苗子當(dāng)作了告密人。該人特地找到了《中國作家》雜志編輯部,詢問了《聶紺弩刑事檔案》的編輯,從那里,他更加明確地得知那封信的作者,本與黃苗子毫無干系。
質(zhì)疑三,《聶紺弩刑事檔案》有寫給黃苗子的詩,這些詩怎么到了專政機(jī)關(guān),寓真在書中都搞不清楚。他寫道:“當(dāng)我以偶然機(jī)會接觸到聶紺弩檔案的時候,聶公本人早已作古,就連戴浩、向思賡諸位可以作證的人,也都各自安息而去。黃苗子雖然健在,已是90以上的耄耋之年,我曾有意登門拜訪,解開聶詩入彀被禍的疑團(tuán),但又怕驚擾老人的晚景安寧,所以打消了此念。”
那么,章詒和有什么憑據(jù)可以說這些詩是黃苗子主動交上去的呢?黃苗子從1957年即與“二流堂”成員一起被劃為右派,成為專政的對象。1958年被發(fā)配到北大荒伐木,1967年春被關(guān)進(jìn)牛棚,1968年9月4日便被抓進(jìn)了監(jiān)獄(聶紺弩是1967年1月被捕的)。“文革”后被多次抄家,他的大量書信、文稿、資料、照片等被抄得干干凈凈,直到“文革”后才返還了一部分。在監(jiān)獄里,專政的對象失去了自由,被要求交代、檢舉,本是正常的事,退一步說,即使檔案里有黃苗子在特定的情況下被要求解釋聶紺弩詩詞的情況,但從解詩的內(nèi)容上看,似乎并沒有“深挖”、“陷害”,反而是避重就輕、蒙混過關(guān),章詒和憑什么說是黃苗子“一筆一劃把聶紺弩寫進(jìn)了監(jiān)獄”?

質(zhì)疑四,檢閱近期的網(wǎng)絡(luò)評論,關(guān)于黃苗子告密事件,已經(jīng)有王容芬等人對章詒和提出了質(zhì)疑,而章詒和似乎也信誓旦旦。是不是章詒和還掌握了其他有關(guān)黃苗子主動告密的材料,只是還沒有公布出來?該人認(rèn)為,章詒和已經(jīng)是一位著名的公眾人物,有較高的知名度,具有學(xué)者、作家、博士生導(dǎo)師等頭銜,千萬不要在善良的讀者面前賣關(guān)子了,有什么猛料盡快公布,免得讀者不明就里和過于期待。人人都有說話的權(quán)利,但說話要有真憑實(shí)據(jù)。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guī)定了“誰主張,誰舉證”原則,即當(dāng)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zé)任提供證據(jù)。絕不能采用猜測臆斷編故事寫小說甚至“道聽途說”、“移花接木”、“莫須有”等樣的手段,來面對“黃苗子是否告密”這樣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
鏈接:
黃苗子,曾用名:黃祖耀,出生于1913年,籍貫:廣東中山。1949年后任政務(wù)院秘書廳秘書,《新民報(bào)》副總經(jīng)理,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編輯,民革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常委。20世紀(jì)80年代后任全國文學(xué)藝術(shù)界聯(lián)合會委員、全國書法家協(xié)會常務(wù)委員、全國美術(shù)家協(xié)會委員等。第七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1992年后,任澳大利亞格里非斯大學(xué)客座教授、名譽(yù)教授。
主要論著有《美術(shù)欣賞》《吳道子事輯》《畫家徐悲鴻》《八大山人傳》《畫壇師友錄》《藝林一枝》等。 聶紺弩,筆名:耳耶、二鴉、簫今度等。生卒:1903—1986,籍貫:湖北京山。1949年后,歷任中南區(qū)文教委員會委員,香港《文匯報(bào)》總主筆,中國作協(xié)古典文學(xué)研究部副部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副總編輯兼古典部主任。是中國文聯(lián)第四屆委員,中國作協(xié)第一至第三屆理事、第四屆顧問,第五、六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 論著有《紺弩小說集》《紺弩散文》《聶紺弩雜文集》及《中國古典文學(xué)論集》。■
(夜子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