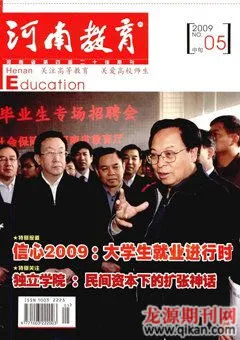遙遠的精神絕響
被魯迅稱為“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的馮至,在他的文章《昆明往事》中有這樣一段令人深思的感慨:“如果有人問我,‘你一生中最懷念的是什么地方?我會毫不遲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繼續問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來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覺得更健康?在什么地方書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讀書更認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書,又寫作,又忙于油鹽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連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昆明。”馮至1939年暑假應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葉公超的邀請,辭去同濟大學的工作,到位于昆明的西南聯大擔任外文系教授。《昆明往事》是馮至后來所寫的一篇回憶文章,被認為是最能反映西南聯大人心聲的文字之一。
從上海到昆明,馮至的選擇代表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精神取向。抗日戰爭開始之后,中國知識分子基本上處于兩種狀態之中:一是繼續留守在淪陷區,這包括在上海租界里的孤島文人,也包括在北平和南京偽政府統治下的文人群落;一是絕大多數文人的選擇,他們集體遷移到大后方,這種遷移又主要分成了兩個方向:一部分是到位于西南的昆明或重慶,一部分則是到位于西北的解放區延安。西南聯大所在的昆明集中了當時中國最杰出文化精英的半壁江山。從1937年開始到1946年結束,在民族危亡、家國破碎的危難時期,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所組建的西南聯合大學開始了一場為中國學術文化延續血脈與保留火種的艱苦戰爭。相比上海租界里的孤島文化、解放區里的革命文化、日偽統治下的淪陷區文化,以及國統區里的黨國文化,遠在西南邊陲的昆明,則代表了一種比較純粹的學術文化。因此,它能夠在民族危亡、偏居一隅和物質極度匱乏的情況下,依然生機勃勃,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跡,也因此更值得今人進行一番研究。
抗日戰爭勝利之后,北大、清華和南開3所大學北上復校,西南聯大由此解散,隨后就是國共內戰,再隨后是新中國的成立,而這些歷盡磨難的中國文人等來的卻是近30年的精神煎熬。之前諸多文化形態的共存,最終以延安為代表的革命文化成為歷史主流,曾為西南聯大外文系教授的馮至,則伴隨著時代潮流的幾度起伏,卻無法超越他在民族危亡之際旺盛噴涌的創作態勢。兩相比較,作為馮至,竟也有撫今追昔之感,這或許也是他懷念那段歲月的重要原因。而讓后人為之感慨的,也正是以馮至等人為代表的諸多文化學術精英們,曾在如此困厄的環境之中,顛沛流離,殫精竭慮,卻集體性地書寫了我們這個民族的驕傲。
讀劉宜慶的著作《絕代風流:西南聯大生活錄》,就頗有如上之感。此書采用文學筆記的手法,以西南聯大這一獨特的文人群落為切口,生動風趣地描述了西南聯大師生日常生活的種種情形,來試圖重新勾勒和描繪他們極為豐富的精神面貌,追念那逝去已久的精神絕響。
劉君的這部《絕代風流:西南聯大生活錄》分為兩部分,上編是對西南聯大部分教授和3位校長的記述,下編則是對西南聯大人生活狀態的描述:前者是談論個案的精神狀態,后者則是群體性的日常生活實錄;前者展現了中國文人精神中不黨不官、人格獨立和敢于批判的風骨,后者則代表了中國文人處于危難而雍容瀟灑的風流氣派。讀完劉君的這部著作,乃有西南聯大之后已成絕響的嘆息:偌大中國,再無這風骨,也再無這風流了,而這閱讀也便成了溫習這種遙遠精神絕響的功課。隨后的歷史歲月中,盡管也有梁漱溟、馬寅初、陳寅恪等為數頗少的文人還保持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尊嚴,但大多數人都在歷史的風浪中隨波逐流,或者永遠保持了思想的緘默。因而我讀他們在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就頗為感慨,前后差距之大不由讓人感到一種歷史的荒謬。諸如作者所提及的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吳晗,在當時寫成了一部關于朱元璋的著作《由僧缽到皇權》,因為朱元璋的軍隊起義時扎了紅頭巾,所以就叫紅巾軍,簡稱紅軍。國民黨政府審查的時候,認為吳晗的這部書寫得很好,但需要改一個字,就是不能叫紅軍,應叫農民軍。當時的吳晗家境貧困,妻子臥床害病,吃飯只能買農民晚上賣剩下的蔬菜,如果他的這部書能夠出版,就可以拿到很高的稿費,但吳晗卻表示:寧可不出,也堅決不改。而就是這個吳晗,在后來他所出版的另一部著作《朱元璋傳》中,卻根據時代與政治的需要不斷進行內容修改,直到最后整部著作幾乎面目全非。同樣一個人,在西南聯大時期,他保持了文人的精神風骨,但在后來擔任重要職務的時期,卻違心地對著作進行多次修改。那么,究竟這種風骨是有歷史局限的伸縮性,還是只因政治的力量太過于強大?
像吳晗這種前后形成巨大反差的文人,其實并非僅為一二。在中國文化遭受到重創的時刻,另一個不能讓人明晰的問題是,在西南聯大所處的抗日戰爭民族危亡時期,這些中國的文化巨人不惜以種種代價作出極大的犧牲,但到了后來當文化在不斷遭受到內在精神戕害的時刻,為什么那么多文人又選擇了沉默和啞然失聲,甚至有的竟然成為歷史的跳梁小丑,這不能不讓人沉思。諸如同樣是作者在書中所提及的西南聯大教授馮友蘭,時任哲學心理系主任,為人師表,一代碩儒,頗有風度。1942年6月,陳立夫以教育部部長的身份三度訓令西南聯大務必遵守教育部核定的應設課程,統一全國教材、統一考試等新規定。聯大教務會議以致函聯大常委會的方式,駁斥教育部的三度訓令。此函由馮友蘭執筆,上呈后,西南聯大沒有遵照教育部的要求統一教材,仍是秉承學術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則治校。這樣參與公共事務的事件在馮友蘭也還有不少,在這部著作中就有《馮友蘭的風度》等短章予以稱贊。但讓我感到十分疑惑的是,就是這個很有學人風度、能夠秉承自由獨立精神風范的學者,為何在后來面對比這更為嚴重的情況時,卻沒有挺身而出,而是選擇了緘默與回避,甚至是令人非常難堪地參與了歷史丑劇的演出?這又究竟是文人天性上的局限,還是中國的文人太懂得識時務者為俊杰之道呢?
因此,等我讀完劉君的這部《絕代風流:西南聯大生活錄》,在不斷溫習那些已經成為絕響的文人風骨與風流的時候,頗為疑惑這些美麗如童話一樣的故事為何竟然只會成為歷史的一聲絕響呢?我想,這一方面在提示我們需要重新去深入認識中國的歷史和文人;而另一方面則是時下歷史著作的寫作問題,這或許也是造成我們理解問題出現諸多疑問和偏差的一個重要環節。在這部著作中,劉君對于西南聯大的學人常以一種溢美和欣賞的方式來表達,這些文字在我讀來預示著,作者在進入之前就已經基本形成了寫作的基調,這或許正是其研究的一個陷阱。還是以馮友蘭為例,此書中的《馮友蘭的風度》一節中,劉君也注意到何兆武在《上學記》中對于馮的批評,也注意到當時的西南聯大學生在民主墻上張貼漫畫諷刺馮,但在作者看來這些或者是“有偏頗之處”,或者只代表了“一些學者的看法”,然后筆觸一轉,變成了對馮氏的另一番描述,最后很快以這樣的論調結束:“在抗日戰爭這段艱難的時期,有論者認為,馮友蘭在西南聯大論道德有古賢風,著文章乃大手筆,立功求其實,立德求其善,立言求其優,這就叫至真至誠。這正是馮友蘭作為中國學者的中國氣派。”讀完這樣的評價,我總感覺這評價來得太容易,短短千余字就得出如此結論,似乎難以讓人信服,而對那些異見的言論也缺乏應有的辨析和深入的探討,如此造成的就是歷史人物形象的單一與單薄。其實,歷史與人物遠非我們想象得如此簡單,其復雜性、矛盾性和深刻性都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這或許是當下歷史寫作者所必須重視的。
(《絕代風流:西南聯大生活錄》,劉宜慶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責編:曉 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