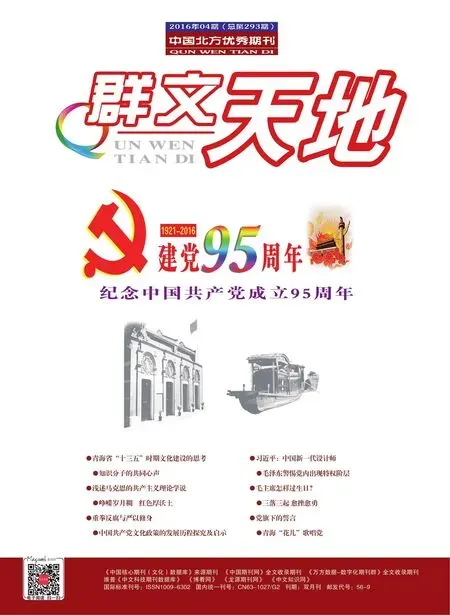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的原因淺析
齊志賢
冷戰結束以來,聯合國安理會在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方面發揮著越來越不可忽視的作用。然而,新的時代形勢也同樣凸顯出這一集體安全機制的局限。有關安理會改革的呼聲因此逐漸高漲。在筆者看來,安理會改革主要
基于以下原因:
一、新時代、新挑戰
冷戰后的國際形勢雖總體趨向緩和,世界的安全形勢卻陷入更加復雜化與碎裂化之中。作為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最重要、最具權威的機構,安理會在冷戰后面臨著更多的外在挑戰。主要體現在:1、傳統安全概念遭到顛覆。世界多元一體式的發展導致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非傳統安全威脅不斷涌現。同時經濟、社會、人道主義與生態等非軍事資源領域的不穩定也成為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新威脅,如由貧富差距、環境污染等引發的大規模騷亂、恐慌等,這種威脅雖較隱蔽、沖突烈度小但影響范圍廣泛①。此外,世界性戰爭雖未爆發,但因民族、種族、宗教、意識形態、領土爭端等引發的地區沖突、國內沖突不斷,局部戰爭熱點反而呈現不斷增加的趨勢。這些安全威脅的存在不斷挑戰著安理會的傳統維和機制。2、美國的單邊恣肆。隨著第三世界實力與美伙伴國離心傾向的雙重增大,安理會這一美國合法稱霸的有力工具變得越來越不得心應手。單邊主義的恣肆由此而生。其存在破壞了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國際法體系及其運作機制,并向安理會這一傳統的多邊維和機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最為嚴重的是美國單邊主義政策與實踐為超級權力的恣肆開了先例,如果得不到有效約束,安理會將形同虛設。3、其他集體安全機制的邊緣化挑戰。國際社會的無政府性決定了安理會不完整的權威性,使其不可避免地會與其他集體安全機制發生摩擦。北約即是典例。1994年《北約戰略新概念》將干涉行為列入其主要戰略目標,不啻于褫奪了國際社會賦予安理會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特權,這種超越區域地理概念的角色自我膨脹行為,使安理會“時常處于一種被輕視、被蔑視的尷尬境地中”②,安理會被邊緣化而形同虛設的危險進一步增大。
二、舊體制、舊運行
作為時代的產物,聯合國建立在懲罰與管制戰敗國的基礎之上,同時也是大國斗爭與妥協的結果。安理會這一核心機構的體制結構與運行機制自然也被打上了這種烙印。冷戰終結所帶來的多元化趨勢將世界引入一個前所未有的紛繁復雜時代,安理會的傳統體制結構與運行機制逐漸陷入困境。主要表現:1、四兩撥千斤的尷尬。改過自新的德、日等戰敗國對躋身國際主流社會的努力,實力不斷增長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對國際社會發言權的迫切要求,聯合國全球代表性的不斷提升,使僅15個成員國的安理會難以再反映聯合國的代表性與廣泛訴求。擴大安理會、增加安理會的代表性勢在必行。2、議而不決的尷尬。安理會決策能力低下、工作效率差已成不爭事實。究其原因在于安理會決議的權威性與強制性,使安理會充滿國際權力的斗爭與妥協。冷戰后國際社會一超多強的多極化格局導致了國際權力斗爭的進一步復雜化,造成協調與平衡各方利益的難度不斷加大,安理會的多邊協調機制也因此面臨更加嚴峻的考驗。3、傳統維和機制的尷尬。這種尷尬因不同的安全威脅而異:對于傳統安全威脅,局部戰爭熱點的“繁榮”,使安理會傳統維和機制面臨前所未有的高需求;而大國權力斗爭的復雜化與協調難度的加大,使安理會傳統維和行動更是舉步維艱,盧旺達大屠殺即為典例;對于非傳統安全威脅,非傳統安全問題的不斷蔓延與惡化顛覆著傳統維和理念,安理會傳統維和機制捉襟見肘。更為嚴重的是對于此類新問題,安理會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應對機制,充分暴露出其傳統維和機制的滯后性。因此,只有改革安理會傳統的體制結構與運行機制,才能使其適應新時代的深刻變化并重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三、重建的代價
安理會在應對世界新安全形勢的不力,引發了人們對此傳統維和機制的失望與質疑,國際社會中也因此出現了不少廢棄安理會、重建集體安全機制的聲音。讓我們來考量一下重新構建一集體安全機制的可能:首先,在是否有必要廢棄安理會的問題上,我們有必要客觀地判斷安理會是否的確不再有存在的價值。顯然,安理會通過其多邊協調性、核心性與剛柔并濟的實踐性,為穩定國際關系所做貢獻是遠大于其不足的;其次,即使我們真的廢棄安理會,重建一新的集體安全機制,我們能否承擔其中的代價呢?如果重建的是區域性集體安全機制,如美國提出的“民主同盟”,那么人類構建全球治理達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將毀于一旦,世界將重新陷入碎裂化的競爭與對抗之中。顯然這與多元一體的世界發展趨勢背道而馳。如果是全球性的,那么我們有必要掂量一下:在設計新的集體安全機制上我們已經走出多遠、在國際社會的認同與接受上我們有多大把握、鑒于集體安全機制的權威性與強制性,誰能保證新機制的構建不會陷入權力紛爭的中斷?退一步講,假設我們“成功地”設計出新的集體安全機制,那新機制又會和安理會相去多遠,又有誰能保證這一新機制不會重蹈安理會的覆轍呢?對于這些疑問,我們并沒有多少肯定的答案可以給。因此,既然我們選擇了借助全球性集體安全機制的手段來尋求最終的世界和平與安全,既然我們已經這樣走出了這么遠并且走得看起來并不那么令人沮喪,既然我們有必要繼續這樣走下去,那么改進現有的集體安全機制要比推倒了重來的代價小得多,更何況安理會并非乏善可陳。事實上,即便是
安理會這一稱得上傳統的全球性集體安全機制我們都尚未駕馭好,更何況一個新的集體安全機制?
注釋:
①俞正梁等著:《全球化時代的國際關系》,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174頁.
②喬衛兵:北約組織與八國集團左右夾擊聯合國,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年第3期.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