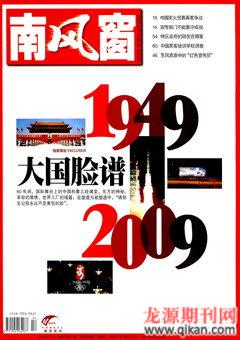中印邁向和諧的漫長征程
李因才
不僅中印雙方很容易受制于競爭思維框架,區域外大國和區域內的小國也在一定程度上趨向強化兩國間的競爭態勢。比如,東南亞國家特別希望新德里發揮更大作用以抵消中國影響,而南亞諸國則期待與中國更多合作以制衡印度霸權,華盛頓更是竭力在中美印間維持等距離三角外交以保持獨大、中心地位。
6月的中印關系“冰火兩重天”。—方面,兩國在邊境地區緊張對峙,印度空軍司令梅杰聲言“中國是最大威脅”,之后印度又開始在“阿魯納恰爾邦”增兵近6萬并部署先進武器。與此同時,辛格總理在9日的國會講話中也聲稱領土問題“絕不妥協”,盡管中國外交部采取柔性姿態低調回應試圖消火,但民間的反應依然熱火朝天。當6月下旬中國未能阻止亞洲開發銀行向“阿魯納恰爾邦”項目貸款6000萬美元之后,這一反印情緒再次得到宣泄。
另一方面,中國國家主席15日晚在葉卡捷琳堡承諾“爭取早日妥善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印度總理則承諾“不會允許任何人在印度領土上從事反華政治活動”。翌日金磚四國峰會上,四國元首手手環握,樂意融融,會后以“我們”的大家庭式言語表達了共同推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決心。這兩種有強烈差異的畫面正說明當前中印關系的復雜:既在改革現存國際政治經濟權力格局方面合作,又深陷相互猜忌的戰略泥潭之中,始終難以邁開大步伐。
馬拉松式談判的有限進展
中印關系進展艱難,在兩國的邊界談判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尼赫魯時代,印度堅持“邊界已定,無須談判”,結果喪失良機,導致1962年邊界戰爭。70年代末兩國關系開始走向正常化,時任外長的瓦杰帕伊和黃華實現互訪后,兩國隨即在1981年12月展開副外長級別官員談判。在前后8輪副外長級談判中,新德里改變了先前的“不談判”政策及“不解決邊界問題不發展關系”的“平行”政策,對中方提出的三段爭議區域“一攬子解決”而非“分段解決”的方案做出讓步。之后,談判工作被新成立的邊界問題“聯合工作小組”接管。

從1989年7月到2003年8月,“聯合工作小組”接連發起了15輪談判。2003年瓦杰帕伊總理來訪,邊界談判遂升級為“特別代表”規格,中方由戴秉國副部長(后任國務委員)主持,印方則先后由國家安全顧問米什拉、迪克西特和納拉亞南領銜,在北京和新德里又輪番對陣了12場。而1994年成立的由兩國外交家和軍事家組成的“專家小組”。迄今召開的會議也有15次之多。可以說,最近20年來,由“聯合工作小組”、“特別代表”、“專家小組”構成的這三層次政治談判機制,各司其職,在中印邊界劃分問題上進行了馬拉松式談判。
經過努力,兩國在1993年、1996年、2005年元首互訪期間,就緩解軍事對峙與沖突、建立軍事互信達成系列協議。與此同時,邊界談判也取得一些突破性進展。在2001年“聯合工作小組”的談判中,雙方就爭議最小的中段區域取得了共識并于次年11月交換地圖。而“特別代表”之間經過5輪連續磋商后,最終于2005年4月溫家寶總理訪印期間。確定了解決邊界問題的11項政治指導原則,為下一階段的細節磋商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此外,與邊界談判密切相關的西藏地位問題也最終塵埃落定。2003年瓦杰帕伊訪華時,印度正式承認“西藏自治區(而非西藏地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放棄了此前的“宗主權”或其他對“西藏自治區”作另類解釋的立場。作為回應,北京也逐步歇認了新德里對錫金的主權現實,例如從中國外交部網站上的亞洲國家和地區名單中拿掉錫金。
由于上述一系列措施和進展,1987年“桑多洛河谷”沖突事件后,兩國邊境基本相安無事。考慮到兩國各陳兵數十萬虎視眈眈,中間又歷經冷戰終結、1998年印度核爆、1999年印巴沖突和2002年印巴危機等事件,中印邊境能一直保持和平安寧,實在是個奇跡。不僅如此,1990年代以來兩國還陸續開放了幾對邊境貿易口岸,其中最重要的是2006年7月開放的位于亞東縣與錫金段的乃堆拉山口,該山口在1962年之后就—直處于封閉狀態。
東段爭議邁不出大步
不過,和外界的期待相比,中印邊界談判進展還是太慢。2007年“特別代表”會晤了3次,2008年只有一次,從2007年9月的第11輪會晤到即將于今年8月初上演的第13輪,中間連續出現了兩個長達一年的談判間歇。2000年從“聯合工作小組”中分離的兩國安全對話在進行兩輪后無疾而終,戰略對話機制從2005年到2007年接連進行三輪之后也慢慢沉寂下來。
東段的所謂“阿魯納恰爾邦”是談判最大難點。該區域涉及面積9萬多平方公里,占三塊爭議區域面積總和的70%以上。由于1962年中國軍隊戰勝印軍后旋即撤出,該地一直由印方實際控制。40多年間,新德里不斷往這里移民并加大資金投入和政策同化力度,軍事布防更被視為重中之重。隨著時間的推移,印度人越來越心安理得地將該區域視為印方獨有資產,對中方所謂的“覬覦企圖”嚴加斥責、強硬以對。
2006年11月胡主席訪印前,孫玉璽大使在電視采訪中稱“阿魯納恰爾全邦屬中國領土”,此言引起印度強烈反應,新德里甚至要求中方召回孫大使。2007年5月,中國不給一位來自該區域的官員發簽證,再次成為印度報章攻擊的焦點。而對華姿態強硬的《印度時報》甚至連年無聊地搞起所謂中國軍隊入侵次數的統計。2006年隨著青藏鐵路的通車,尤其中國經濟、軍事現代化進程加快,新德里的危機感急劇攀升,對該區域的主權宣示日趨頻繁,經濟、軍事投入也更加不惜血本。
由于牽涉主權尊嚴和領土完整,兩國在此一區域都很難做出太大讓步。其中,接壤不丹的達旺地區更是爭奪焦點。這個2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不僅富產資源、氣候溫潤、風景秀麗,更是藏南地區的政治、宗教中心,六世達賴倉央嘉措的出生地。有著300多年歷史的達旺寺,是西藏的第二大寺院。由于達旺地區被藏人視為宗教、文化圣地,中國萬難舍棄。中國部分南亞問題專家甚至提議,北京應將歸還達旺視為兩國繼續邊界談判的前提。
不過,印度軍方聲稱,一旦新德里將這個連接雅魯藏布江河谷和拉薩的走廊地帶拱手相讓,中國軍隊就可以長驅直入,對印度東北安全構成直接威脅。1962年,達旺是當時的主戰場。1987年,由于印方堅持在該地設立哨所并謀求將之并入“阿魯納恰爾邦”,這一地區再次出現嚴重的軍事對峙事件。
可以說,在兩國邊界談判過程中,需要的不僅是實力和技巧,更要有政治智慧和勇氣。在強大民意壓力和民族情緒的顛簸里,雙方都必須謹小慎微,掌握好航向和速度,防止傾覆。而新德里由于向來缺乏政治共識,大選后上臺的又多是聯合政府,使得其在邊界談判中角色更顯艱難,也更難以邁出大步。
實際上,為了迎合民意,脆弱的聯合政府往往會在進入談判前顯示自己的強硬姿態。而印度媒體更是出了名的攪局者,通過大打“悲情牌”,號召領導人“勇敢抵抗中國欺凌”,從而潛移默化地改變了民眾對談判的心理預期。反過來,新德里不斷挑釁的強硬姿態特別是坐守1962年邊界戰爭大部分成果卻將自己塑造為戰爭受害者的可惡嘴臉,又激起了中國民眾的極大憤慨。兩國民族主義情緒的發酵無疑給需要理性務實空間的邊界談判投下了長長的陰影。
超越競爭性思維
很顯然,由于談判進展緩慢,邊界問題已經嚴重制約了兩國的關系發展,對雙方在其他領域的合作產生了極大的負面效應。12.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爭議如鯁在喉,使得他們在國際舞臺上的牽手既顯得勉強又動作遲緩。無論是在金磚四國、中俄印多邊框架下,還是在諸如溫室氣體排放、多哈議程的談判過程中,兩國的象征性宣示都遠遠高于真心合作。盡管在所有這些領域,中印都存在大量的共同利益。而在南亞、中亞、東南亞、非洲等地區性事務中,雙方更是如同死敵,難見合作的場合。其中。身處弱勢地位的新德里對華心態不僅封閉保守,而且缺乏自信,尤其是在南亞次大陸事務上。
比如,中國早在1990年代就開始逐步調整南亞政策,在印巴沖突中保持中立,視克什米爾問題為印巴之間用非武力方式解決的“雙邊問題”,更強調在印巴關系中的平衡角色。但新德里仍舊喋喋不休,一如既往地指責中國和巴基斯坦“正在推進相似的目標,在戰略上‘擠壓印度”。對中國和斯里蘭卡、緬甸、孟加拉、不丹、尼泊爾等國的雙邊合作,盡管印度戰略界也注意到,北京著眼于經濟交往而非戰略企圖,不過依然憂慮重重,認為中印在南亞的競爭是導致雙邊關系緊張和地區不穩定的重要原因。
由于競爭對手的思維限制,兩個共同生活了數千年的文明大國,彼此對對方的了懈卻近乎無知。印度尼赫魯大學教授巴騰度·辛格在《印度教徒報》撰文,哀嘆印度社會對遠在萬里之外的西方國家的了解程度要遠遠高于對近鄰中國的了解。其實,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彼此不了解,自然談不上相互接近乃至接受,這不能不說是—種悲哀。
有意思的是,不僅中印雙方很容易受制于競爭思維框架,區域外大國和區域內的小國也在一定程度上趨向強化兩國間的競爭態勢。比如,東南亞國家特別希望新德里發揮更大作用以抵消中國影響,而南亞諸國則期待與中國更多合作以制衡印度霸權,華盛頓更是竭力在中美印間維持等距離三角外交以保持獨大、中心地位。現實主義均勢思維的流行,讓兩國都成了受害者。也許,雙方都應該聽印度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教授一句話,他說:“人們應該問的一個問題是,中國和印度可以相互學到什么,而不是誰將超越誰。”